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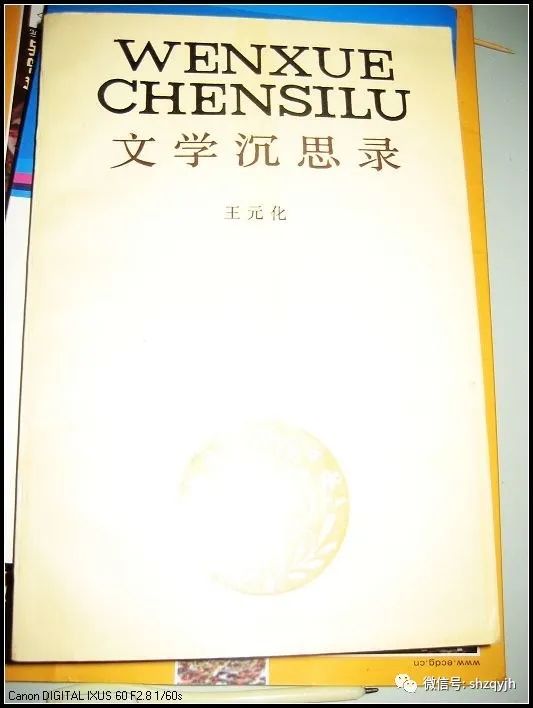 东方的名著《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褒述,比如说夸父就是一个探索自然奥秘的巨人,也许夸父的伟大并不在于他跨越三山五岳如走泥丸,而在于他最后倒在探索的路上后,仍不忘记泽被造福后人,弃手杖化桃林,以资后来者有了一块歇息和继续前进的基地。 时光飞快,转眼间,我国文化思想界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逝世已多年了。然而,作为一代著名的思想者,他留给我们的那种独立思考、善于反思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也早已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长河流月去无声,很多时候在夜阑人静时,随手翻看着王元化先生赠送的《文学沉思录》、《思辨随笔》等书,想起曾经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以及相处并不算多的日子,不禁感慨良多。王元化先生的音容笑貌甚至一些看似细小实则难忘的往事,一一浮上心头。 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爱的老头 2000年我调上海市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征集社会名人的档案资料。 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那是在2000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到了位于徐家汇附近的一家小宾馆内,叩门之后走出一位老者,正是王元化先生。他微笑着说:“贺飞同志,欢迎!因为你来和我谈档案征集事情,我已经谢绝了几个电话来访的客人,我们就可以安心谈工作了。”说着他顺势将手搭在我肩上走进客厅。原本我担心,这样一位海内外闻名的学者且又做过大官,我会不会拘束?哪里知道初次见面竟是这样的宽松随和。 没有拘泥感,这话题就自然多了。趁他说话时,我一边注意倾听,一边仔细关注地看他。王元化先生神态和蔼,语气平缓。我发现老人的眼睛非常特别,有时目光亲切慈祥,有时会突然地亮了一下,好象有一种特别的光芒,非常深邃!我很奇怪这种现象。以前我只是从书本上读到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是重瞳,后来武侠小说中描写有些武林高手因为内功深厚会目射精光。王元化先生逝世后,曾有人写文章说王元化的眼睛像尼采或茨威格。但是李煜也好,武林高手抑或尼采茨威格也罢,反正我都没见过。我只看到过王元化的眼睛真的有些特别,特别在哪里,我一时说不清楚。 交谈中,王元化先生偶尔会说些上海话,但一般他都用略带方言的普通话交谈。也许是没有了拘谨,我突然冒出一句:“王老,听您说话,我才知道什么是《汉宫之楚声》了”。他问我:“哦,你读过《汉文学史纲要》?”我回答:“是的,但不知道荆楚语言,因为我没有去过楚地。不过告诉您王老,我是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王元化先生一听哈哈大笑:“原来如此”。我又告诉他,知道您的书法很好,我也喜欢书法,有时还练篆刻。他一听忙说,有人送他一方印,上有“仆本恨人”四字,能解释一下吗?我回答:“晚清会稽赵之谦刻过这四字,是‘恨’字”,王元化先生笑着解释他方言读音不标准,听起来像“狠”了。正在这时有客来访,我赶紧起身告辞。谁知王元化先生悄悄说:“你可暂到另一间屋看看书报,等客人走后,你给我把这方印四字解释清楚再走”。客人走后,我告诉王元化先生,赵之谦这四字是与一方“穷鸟”印同时刻治,根据边款理解,大概是恨人不如鸟自由意思。王元化先生闻之欣然。 与王元化先生的初次见面就是这样生动有趣,像我这样的无名后生小辈,有时还有不知轻重时候,他竟毫不为意,如此平易近人,让我顿生惊喜感慨。 接触多了,愈觉得老人毫无架子亲切可爱。有一次我带了一位叫韩凌的青年学子同去看望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随口问他在哪里念书,爱看什么书等。韩凌同学告诉老人,在复旦大学网络学院读书,平时爱看南怀谨的书。王元化先生一听惊奇,:“你这个年龄能看南怀谨的书,很好啊!”谁知这个韩凌同学掏出两本书说:“我现在也爱看您老的书了,请您帮我签个名吧”,王元化先生爽快答应了。这个韩凌得陇望蜀,又恳求王元化先生赠送几本书,最后又出一招拿出照相机希望和王老合影留念。王元化先生一看呵呵直乐:“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我是防不胜防了,怎能不答应呢”。 从王元化先生那里出来,青年学子兴奋的有点迷糊甚至困惑:“原来这就是王元化先生啊!”我说:“是啊,有什么奇怪吗?”“怎么我要求什么他都答应啊?他可是闻名天下的大学者啊!”青年自言自语道。 “噢,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我有点答非所问却意味深长地说。 后来这个韩凌告诉我,在一次回学校参加聚会时,和老师同学们谈起拜访王元化先生的事,并且还拿出了照片给大家看。众人都非常吃惊,连连问他,你怎么会认识王元化先生的?那种神情和语气中的成份非常复杂,弄不清楚究竟是疑惑、妒忌、还是羡慕。 “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我问。“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青年学子如此说。 博学精湛、幽默诙谐的智者 众所周知,王元化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一生著作等身,是一位秉性异常记忆力超群的人。谁能想象一个毕生读了那么多书而且已是耄耋的老人,记性仍然是这样惊人,思路仍是如此清晰。 2007年,此时的王元化先生已经87岁,癌细胞渐渐感染到他的肺部,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访欧美讲学,赴东瀛论道;再也不能去西湖吟赏烟霞,也不能登华山谈笑论剑;最严重的是手已不能写字,眼亦无法看书,那一刻,他定然感受到岁月的无情,再也不能行动自如了,垂垂老矣。然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元化先生特地叫人请了一位女大学生为他朗读古典名著,期望再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曾侯编钟的黄钟大吕、大泽云梦的龙吟马啸、赤壁鏖战的鼙鼓铮鸣以及从故乡荆楚大地吹来的烈烈长风。 有一天,接到王元化先生的电话,要我和本部门的孙慧同志去他处取近期的一大批书信。见我们进来,他示意秘书带我们在客厅稍候,此刻他正在聚神地听着女大学生朗读《史记·项羽本纪》,我们静候在外权当陪听。忽听王元化先生叫了声:“停,你这里读错了,‘距关,毋内诸侯’,这个字不读‘内’,读‘纳’,是通假字。全句意思为依据或占据着关隘,不要接纳诸侯。” 如此高龄,这般记忆,真是不可思议,若非亲眼目睹,实在无法相信;先生博学,令人叹服。 除了博学精湛,王元化先生还是一个非常幽默诙谐的老人。他每有新书出版,就会送我一本签名本,所以我每次去看他时总要问一下近期是否有新书出版。记得有一次,我一下子“搜”出了三四本新出版的著作,王元化先生不禁哈哈大笑:“贺飞,你土匪啊!这哪里是来看我,分明是来抢东西的。我说你干脆改名‘胡作非为’算了”(他这是用上海话讲的)。多年来,王元化先生先后赠送给我的书近二十多部,计有《思辨随笔》、《文学沉思录》、《清园近思录》、《思辨录》、《清园文稿类编》等等。如今这些珍贵的签名书都已成为我对王元化先生的深深怀念和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最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以来,王元化先生共计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近万件的信函、照片、读书笔记、九十年代反思日记、墨迹、书稿等,是直至目前为止单个捐赠数量最多的社会名人,为上海市档案馆增添了一笔非常可观的历史文化财富,为国家的档案资源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元化先生患有较严重的皮肤过敏病,尤其是每当夏季闷热潮湿时,更是奇痒难受,所以大凡一到夏天时分,他就下穿一条宽大老头短裤,上身索性光膀赤膊。有一天我约了负责美编的一位女同志去他处商谈工作,因为事先没告诉他有女同志。门开后,只见王元化先生仅穿着一条老人短裤和拖鞋,光着上身出来。一看到我身后那位女同志,啊呀了一声:“有女同志啊!失礼了”,慌忙缩了回去。赶紧入内找了件老头汗衫,手忙脚乱地套上穿好走出。谁知忙乱中出汗更多,湿的汗衫又粘在身上。无奈之下,只好再换了条大浴巾披着出来,一本正经地自嘲道:“这下可好,书房变成了澡堂”。惹得我们忍俊不禁,我们赶紧说:“王老,您是我们的父辈长者,您老尽可随意的”。王元化先生摆摆手说:“这不太好,我老头子一副又老又丑的皮囊,让年轻的姑娘看见实在不雅,披件东西也是对女同志的尊重”。 王元化先生曾经对我谈起,他常常怀疑我们居住的城市空气有问题,因为他到其他国家去交流访问时,如果也在夏天季节,他说自己的皮肤就没有瘙痒问题,因为那些国家的空气质量环境状况都非常好。当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概念。2004年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为他送去捐赠档案的目录清单。那是一场瘟疫横扫神州大地后的第一年,不知怎么的我们聊到了中医。王元化先生突然问我,有一位国宝级的国医大师,他的档案资料的档案馆收不收?我说:“既然是国宝级的抢都抢不到啊”!王元化先生问我:“听说过颜德馨吗?”我一听猛省:“难道是那位孟河学派抗衰老的中华名医?”王元化先生说:“正是此人!你还不知道吧,去年上海共8例非典的病例档案就在他手里,我这就帮你打电话问问”。电话接通后,只听王元化先生在电话这头说:“颜老啊,近来忙吗?要是忙的话,我就来帮你采药、煎药、背背药箱,你看怎么样?还有,我这里有个叫贺飞的,档案馆的,你那里一些宝贝资料就捐赠给了他吧”。电话那头很清晰地传来颜德馨的声音,也是妙语连珠:“王老啊!东西捐给档案馆,行啊。但你这枝有思想的笔是不能搁下的,你要是忙不过来,我正琢磨着来帮你磨墨捧砚脱靴呐”。 这两位中国最崇高职业的德高望重老人在电话里互侃,听得我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哑然失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作智者乐,仁者寿。 两情愈是久长时,愈期在朝朝暮暮 宋人秦淮海有一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假如这一名句用在王元化、张可夫妇身上,便成为无病呻吟的多余。 早就听说张可先生的美,在王元化先生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的照片中,有部分是与家人的合影。看照片上的张可先生确实美丽端庄,虽然我多次去过王元化先生处,但一直没有见到过张可先生本人。曾经试探着问过王元化先生,他告诉我张可先生身体不太好,大部分时间都在治疗。 所幸我终于看到了张可先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张可先生。 具体时间记不得了,总之是在一个天气很好的下午,我正和同事孙慧同志在庆余别墅王元化先生的住处。孙慧说起照片上的张可老师很漂亮,我说,看照片上的张可先生,那种美的清纯一如秋水长天。王元化先生听了,点了点头,说道:“是吗?那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把她扶出来,你们看看是不是所说的那样”。一会儿,王元化先生轻轻扶着张可先生走了出来,又轻轻地扶着张可先生坐下,并向张可先生介绍我们。只见张可先生向我们微笑着点头,没有说话。虽然早已看过照片上的张可先生,但我还是被眼前的那种美惊呆了,这是怎样美丽的一位女性啊!是那种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和温婉、纯净和沉静,那种美,才美得不可方物。与照片相比,眼前的张可先生虽韶华已去,白发清瘦,但那种微笑善良,那种高雅气质,岁月不仅没有减少她往昔的美丽,反而更增添了她一种生命的风度、宽度与厚度。王元化先生轻轻地告诉我,张可先生因大脑受损,已无法用语言交流和阅读了。又过了一会,王元化先生就轻轻地扶着张可先生进去了,临别时依然是张可先生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看着八十多岁的老翁对八十多岁的老妻那种轻柔、那种温情、那种呵护,我看得出,王元化先生手势是轻缓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呆呆伫立着,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张可先生,从王元化先生口中得知,张可先生已经住院多时了。后来打过几次电话给王元化先生,都是秘书接的电话,告知王元化先生到医院去陪张可先生了。记得还有两次在王元化先生那里,没坐多久,他就非常歉意地说,要去医院了,因为每天都是这个时候要去陪伴张可先生的。六十年的相濡以沫,王元化先生是不能没有张可的。 两情愈是久长时,愈期在朝朝暮暮。 2006年,张可先生去世了。我去看望过王元化先生,发现他老了许多,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的幽默风趣话少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张可先生可以说是王元化先生生命中的重量天枰,一旦离去,便成为王元化先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知道此时王元化先生已患重病,本想试着说上几句宽慰保重的话,谁知话到嘴边又不知如何说才好。我觉得即使搜遍人间任何的劝慰话语,此时可能也是尽显苍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明白,王元化先生如此状况,恐不能久矣,他念兹在兹的,是彼岸的天国,那边有他六十年来家国中相濡以沫、魂牵梦绕的妻子张可。 此情可待成追忆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先生走了---从荆楚大地到吴越山水,走进江南五月令人沉醉的春风里。那是一个草薰风暖、莺飞草长、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随着如同潮水般的吊唁人群,小心地轻轻地捧着一束白色的花,走入吊唁大厅,大厅里播放的竟是一曲《彼岸花开成海》的乐声。我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佛教纯清乐曲,非常的柔美动听感动心灵。询问之下,原来正是王元化先生生前之意。不由得心头一热,联想起王元化先生平生为人处事:安然,坦然、淡然乃至超然,倘若真有来世,想必人生的下一站依然也会是从容。如此一想多少减去几份伤感。跟着次第的人流,我走近 走近王元化先生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献上象征自己一瓣心香的花束。泪眼朦胧中,怎么看都觉得王元化先生仿佛仍然在静静地思考、在沉思、在探索着哲学与人生永恒的真谛…… 思想者孤独远行,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 三千多年前,当思想家老子骑着青牛从东方逶迤而来,皓首白发的背影渐行渐远地消失在西去的漫漫黄尘古道时,华夏民族不知过了多少年才突然意识到:中原大地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位先行的思想家走得如此匆匆乃至无影无踪?这位睿智的思想家为什么要离去?他是否隐隐意识到中原故国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无论怎样的原因,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件!幸亏那位关尹还算清醒,硬是索贿般地让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权做买路钱后才放行。 同样如此,当王元化先生在世时,他治学论道,待人接物,或思维慎密而敏捷,或语言幽默而诙谐,润物细无声,意味却隽永。今天一旦王元化先生远去,熟悉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地平线,猛然间,感觉到心中崩塌了很大的一块。一直以来,中国学界常常比喻北李(慎之)南王(元化),恰如现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对双璧。李慎之以后,犹存王元化半壁江山。而今王元化先生也走了,中国思想界的长空顿显寥落,个中残缺,虽女娲又何补? 斯人往矣,杨柳依依。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智者、思想家若群星璀璨。我没想到,近现代中国历经内忧外患、饱受磨难坎坷之后,在现实生活世界里还能有幸见到如此美好的人生: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孤独的思想者,他一直都在思考,他一生都像夸父那样在追逐着真理的太阳。他把独立、自由、不懈的探索精神和人间至爱展示给我们。与这样一位仁者、智者、思想者同世,并且还能有幸走近他与他相识,真是上帝赐予我的格外恩典。 此情可待成追忆。岁在癸巳,又近清明,谨以此文怀念尊敬的王元化先生。是的,虽然他已离开了我们,但他却走入了永恒。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