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北大、清华共计6000余教职员在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据说当时不叫“北大五七干校”而是“试验农场”。 这块位于江西省,地处鄱阳湖畔,距离南昌市区43公里的冲积平原带,地图上难以找到名字的地方,叫“鲤鱼洲”。父亲厉以宁与第一批抵达这里的“五七战士”们,经历了几个月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迎来了新的一年 -- 1970年。 1《空余明月照芦花》 这年春耕开始前,连里给大家放了来到鲤鱼洲后的第一次假,全体休整一天,准许到外面的商店买些日用品。父亲和连里的几个教师听说附近有个天子庙,据说还是古迹(当年为纪念朱元璋战败陈友谅而修建),便决定趁此机会去看看。 从连队出发顺着大堤走了大约10公里,看到残破不堪的一座庙,但仍有乡民烧香祭拜。为了纪念在鲤鱼洲的第一次“旅行”,父亲写下七绝。 2《七绝 鲤鱼洲头天子庙》 (一九七零年) 楼船烧尽炮声消, 败寇成王一步遥, 遗址几经荒草没, 烟云过后雨潇潇。 回程,从天子庙向鲤鱼洲北大干校走,路边有一农舍,室空无人,周围荒凉不堪,想必是外出逃荒去了。农村的荒芜和破败,父亲不会是第一次看到(之前屡次下放农村),但依然被触动,心情沉重地写下了途中所见。 3《七绝,天子庙途中所见》 一九七零年 塘边小屋是谁家, 蛛网掩门窗满沙, 一片蛙声人未见, 空余明月照芦花。 正是每一次这样的经历,使父亲,一位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之感受,开始了对现有体制的怀疑和深层思考:国家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计划经济之模式行得通吗?  鲤鱼洲上所见》 一九七零年 荒村春夜人皆睡, 忽见堤坡有影来。 衣衫破旧不遮体, 扶老携妻带幼孩。 自称家舍在市外, 山地无雨已成灾。 逃荒只为保残命, 母病儿小饥难挨。 但求两碗热面糊, 草草喝完再赶路。 原来还有更穷人, 今日深知百姓苦。 这是父亲在值夜班时遇到的乡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备受煎熬。鲤鱼洲各连都有值夜制度,每天晚上有两人共同值夜。主要任务是阻止干校外不明身份的人前来偷窃,以及防火、防堤岸坍塌等情况发生。 父亲自1969年起就参加轮班值夜。后来,母亲到鲤鱼洲后,也轮到值夜。也遇到过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乡民跑到这里来。 5《值夜用具》 秋早逝,冬将尽,又暖风 鲤鱼洲的春耕开始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如沐春风”,是我曾经“认识”的春天。但是,江西鄱阳湖畔的冬末初春,却是格外地冷冽,寒风袭人,水凉刺骨。 二月末,稻田开始放水,“五七战士”们卷起裤腿下田翻地,这时稻田表层还有碎冰。 水波粼粼,一头壮硕的水牛,拉着一副木犁,犁后面跟着两个人,用铁锹把木犁翻开的泥土梳理一下,把犁开的地沟抹平,人跟着牛走。活似是不累,但人蹚着冰水,不多久已是嘴唇发青,瑟瑟发抖。 好在劳动力多,来回走个三几趟,就换班。田里的人到田埂上随地而坐,脚不再泡在冰霄的水里,再喝一碗厨房送来的热姜汤,算是除寒取暖,周而复始。 去江西前,我只在电影和书本上见过老牛拉犁,人跟在后面撒种、播种,大地一片阳光,是农耕社会的一幅画面,甚至以为很“经典”,“很浪漫”。到了鲤鱼洲,切身体会了春寒刺骨,看着大人们要下到满是冰渣的田里,简直不寒而栗。 后来,我自己也到农村插队,同样干过跟在老牛后面犁地的活,再也不觉得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有何“浪漫”可言。 灌水、犁田、平沟、育秧工作完成后,这时已是清明前后,天气开始暖和。 6《巫山一段云》 鲤鱼洲上清明节 一九七零年 细雨秧田去, 挑砖总盼晴。 愁思忘却一身轻, 天外有繁星。 祖墓知何处? 新坟草已青。 谁家记得是清明, 茅屋似兵营。 清明,不免引人伤感。但是,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们”却没有时间和心力悲春伤秋,父亲也只能在诗词里聊发感叹。 插秧的时候到了。 父亲在插秧组,有些教师被分配在起秧组或挑秧组。起秧,是把秧田的秧苗拔出来,用稻田的水洗去泥土,用稻草把秧苗捆成一把一把的,供挑秧组运走。 挑秧组把捆好的秧苗装在箩筐或大簸箕里,挑到准备插秧的田边,把秧苗一把一把地扔在插秧者的身后,以便他们插完手上的,身后就有秧苗可用。 父亲成为连队的“插秧能手”,插秧速度快。他归结为自己身体瘦,转身灵活,以及挑秧组的老师力气大,供应及时并到位。 原始的劳动工具(片源:鲤鱼洲陈列室) 我当了“小五七战士”后,和小伙伴们干过运秧苗和插秧的活。运秧苗,最大挑战是挑着秧苗在田埂上歪歪扭扭地走,保持平衡,防止连人带筐掉到田里去。 插秧,弯腰倒着走,怎么走出一条直线?怎么把秧苗插住,不浮在水面?都是技术活。 后来,我母亲(因为工科背景)被调去和其它连队的人研制成功了“插秧机”,真是对生产力之极大解放,也算是“知识分子”种田发挥出了自身优势吧。, 但当时鲤鱼洲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手劳作 其实,如果不计以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之政治目的,仅从“种田”而言,鲤鱼洲的生产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因为鄱阳湖四周都是血吸虫疫区,为了预防血吸虫病,连里有严格规定:不能下河游泳、也不要到河边洗衣服。 下水稻田干活时,需要在腿脚、手臂皮肤上搽一层药油(二丁酯),作为防止血吸虫感染的药水。据说当时这种油很贵,且大量使用,故而鲤鱼洲生产的每斤大米之成本是市场价的25倍以上(当时大米每斤不到两角,这里生产的大米每斤成本则是5元以上)。有人开玩笑:“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水稻”,“知识分子种稻田,一斤米五块钱”。 如果再加上在鲤鱼洲劳动过的北大教职员中,有人不幸患上了血吸虫病,甚至病重医治无效最终去世,该是多么大的社会成本? 后来听北大校医院的医生说:血吸虫在身体内的潜伏期可达15年,甚至更长。在疫区生活过的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我才知道那么多年,我也一直是一位潜在带“虫”者。 这一年(1970),父亲自北大经济系毕业已经整整15年。回顾15年坎坷经历,他填了一首《江城子》。  一九七零年 宫墙深院画楼前, 雨涟涟,不成眠, 把酒问君、何处是桃源。 伴我秋灯多少梦, 添白发,已中年。 新来移住赣江边, 月牙镰,放牛鞭, 百里芳洲、好个艳阳天。 莫谓青春再难到, 光脚去,下秧田。 每一次,读父亲在鲤鱼洲的诗词,脑海中都会浮现一幅幅当时的画面。在体力、精神和心理几重压力和磨难下,他用填词赋诗如此文艺之形式,消磨无眠的夜晚,记录内心之苦闷与无奈,又在字里行间展现出精神的不屈与期盼。 不久,清除稻田的杂草劳动开始了。一块稻田要先后除三遍杂草,和插秧时一样,都得弯下腰在泥水里移动。十连指挥部居然下了一道命令,要大家在稻田里除草时,“50米不许抬头”。 当时稻田大约有50米间宽,不分男女,统统下水,每人负责两到三行,一字排开。 “开始”,一声令下,几十个人蹲在稻田里,倒退着行走。指挥部领导站在田埂上监视,只准弯腰除草,不许抬头换气。抬头表示偷懒、磨洋工,轻则批判重则加倍惩罚。 8《粒粒皆辛苦》(2019年,小伙伴重返鲤鱼洲所见, 好不容易等到收工回宿舍,人人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全是烂泥,洗干净后才能到食堂去打饭。晚上,大家都喊腰疼。几天之后,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此外,这时天气渐热,水温亦暖和了不少,牛虻、蚂蝗又活跃了起来。弯腰除草时,除了不让抬头,还得忍受牛虻在背上叮一口之刺痛,蚂蝗在腿上肆意横行,鲜血流淌。 难怪后来,北大经济系教职员在谈论“鲤鱼洲干什么活最累”时,众人首选“稻田里除草最累”,次之“双抢”,至于父亲刚去时干的砍柴、挑柴等又重又累的活,由于只是少数人参与,未作计算。 只道湖边雨后凉 被鲤鱼洲“五七战士”排在第二位“累死人”的劳动是“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连在一起,前前后后计20天。 抢收早稻有四个环节。第一,用原始的工具--镰刀,把成熟的早稻割倒,放在地里; 第二,把割下的早稻捆好,用扁担把它们运到打谷场; 第三,把早稻送到打谷机上打谷,再把谷子装进麻袋,码在打谷场旁边; 第四,把装在麻袋里的稻谷用手推车运到大仓库门外,再用人力把它们扛进仓库,码成一层一层。有时还要扛麻袋走跳板,走到高处才卸下来。把早稻从田里运往打谷场时,中途不准休息,因为扁担在中途一停,捆好的稻子一放在地上,会掉粒,这就是浪费粮食,是要受批评的。 四道工序全靠人力,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尚未提上日程。 抢收早稻之所以累,与天气变化有密切关系。因为夏天时有暴雨,必须抢在暴雨来临之前把早稻割倒、运回、打谷完毕,再装进麻袋,码在大仓库里。否则遇到暴雨,将损失惨重。 所有这些,必须在短短几天内完成,叫做与老天爷抢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机连轴转,谁也不能停。 食堂把饭送到地头,轮班吃饭,不休息、不睡觉、连续干活。  夜间挑稻谷走田埂,漆黑一片,每人头顶上绑紧一个手电筒,远看好似一条火龙。打谷场上,黑夜里,借着灯光,女教师抱着稻捆供应打谷机,男教师站在打谷机前紧张地脱粒,24小时打谷机连轴转。 还得有人站在打谷机旁装麻袋,老弱病号,就用扫帚把落在地面的稻谷集中起来,再用簸箕把稻谷装进麻袋。无论哪个工种,都会有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 10《卜算子 鲤鱼洲之夜》 一九七零 苇影月明中, 渔火江村里。 挑谷穿梭去又来, 汗湿黄花地。 休叹世情凉, 劫后皆余悸, 今日河东转眼西, 谁敢违天意? 紧张的水稻脱粒, 父亲记得最累的一次,连续劳动48个小时,两天两夜都在地里。 今天写下这段文字,不由想起我后来当知识青年插队时的“双抢”,亦是不分昼夜地在地头或打谷场上干活,又困又累,什么人间烦恼、七情六欲统统随着打谷机的轰鸣抛到九霄云外,只想在稻草堆里小睡一会。 我曾因“双抢”连续无法睡眠,“美尼尔氏症”发作,天昏地旋呕吐不止,被准许到草墩旁休息一阵。现在想起,都心有余悸。 鲤鱼洲的早稻还没有装袋入库房,抢种晚稻的活就开始了。过程与种早稻一样,平犁土地,育秧,挑秧,甩秧,插秧。这时如果有暴雨来临,只要早稻已入库,对晚稻的损害并不大。 “双抢”结束,终于有了暂短的休整时间。 这时母亲请了探亲假带上厉伟(他还没上小学)到了鲤鱼洲。十连在草棚内空出一个房间,同样是用草帘子编成的“围墙”,门和窗也是草帘编的。他们与连队的人一起在食堂吃饭,开始了临时“五七战士”的生活。 设立鲤鱼洲干校的目的是对“人”进行改造,“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是疾风暴雨地革命让他们脱胎换骨,故,施加各种苦与累之磨难便是再自然不过。 但是,对一些从城市里来到乡下的孩童,在这里的感官刺激和天然喜好与成人之世界定有天壤之别。 到了鲤鱼洲,厉伟整天在田埂上玩,捉青蛙、抓鳝鱼、捞小虾,去喂鸭子,或者跟着赶牛人在大堤上溜步。于是,他成了养鸭老师、放牛老师的小帮手。 还有一次“杰作”,他想把进了厨房的一只鸡赶出去,结果“鸡”急,飞上了灶台,一失足,掉进一大锅粥里。鸡被烫着了,带着一身的粥满厨房扑腾(画面自行脑补)。 很快,我在北京就知道了这起“事件”,后来到了鲤鱼洲,在厨房工作的老师还津津乐道地和我提起“你弟弟赶鸡大闹厨房”之事。因大伙都知道他是好心办成了“添乱”,便没有责怪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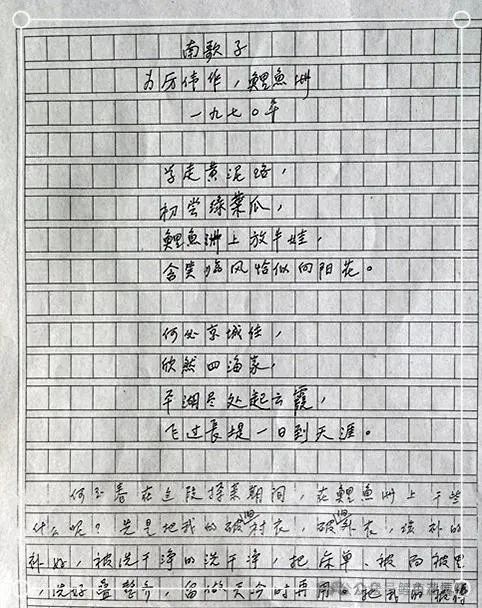 《南歌子》 (厉伟作)鲤鱼洲 一九七零年 学走黄泥路, 初尝绿菜瓜, 鲤鱼洲上放牛娃, 含笑临风恰似向阳花。 何必京城住, 欣然四海家, 平湖尽处起云霞, 飞过长堤一日到天涯。 母亲这期间,为父亲拆洗被褥、缝补衣服。自家人的忙完,开始替几位家属未来的经济系老师清洗被褥、床单。因她老在洗东西,被军宣队发现了,对她说:“他们都是来改造思想的,让他们自己洗,你别替他们洗”。母亲表面上答应下来,变成悄悄地帮他们。 没多久,母亲的探亲假到期了,父亲请了假送他们去南昌。那天他们坐上一艘从鲤鱼洲北大干校开往南昌的小火轮,正值狂风暴雨。 船一离岸,就在风雨中飘摇。船小风急,风狂浪大,同舟20几位北大教员,无不胆颤心惊,命悬一线。终于到了南昌,雨小了一些。 父亲用一根扁担一头挑起铺盖卷,一头挑起一口小箱子,沿街打听南昌火车站怎么走。 竹扁担 --小伙伴保存的纪念品 送走了妻儿,父亲搭上一艘运建筑材料到鲤鱼洲的船,回到连队。归途中,想起狂风暴雨中远送妻儿的惊险一幕,写了一首词。 11、<归自> 狂风暴雨中由鲤鱼洲乘船赴南昌 一九七零年 江上雾, 恶浪滔滔天已怒, 倾盆大雨空中注。 世途艰险如舟渡, 朝谁诉, 忙人总被闲人妒。 虽是“险情”记录,也不禁道出世道沧桑,世途艰险。白云苍狗,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父亲说“回忆我们在鲤鱼洲农场的往事时,好像没有隔多久,因为那段历史让北京大学每一个亲历者都毕生难忘”。 孤洲耕地人 父亲送走了妻儿后没几天,农田的活又忙了起来,晚稻田里的除草劳动又开始了。 正在此时,指挥部下达紧急命令,全体动员,连夜扛着铁锹,带上扁担和箩筐,上堤防洪。大家颇感意外,因为鲤鱼洲一带天气晴朗,怎么突然防洪呢? 上了大堤才知道赣江上游下暴雨,赣江发大水。同时,四川大雨不止,洪峰已达湖北湖南,正逼近九江,长江,洪水可能向鄱阳湖倒灌。 1970年代的赣江南昌码头 鲤鱼洲本来就是用大堤围起来的洼地,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从下面能看鄱阳湖上的点点鱼帆。北大和清华所在地,又是鲤鱼洲洼地之最低处,故极为潮湿,田埂、水渠、堤坝、道路都难以牢固。 由于地面低于湖面,完全不漏水是不可能的,如果排灌站能力不够这片地方就会被淹没。所以鲤鱼洲干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排灌站,加固大堤。 排灌站便是沿大堤最显眼之建筑,在十连的东边,是控制鲤鱼洲内河水位的装置。许多年后,有小伙伴重返鲤鱼洲,寻找的标志物就是排灌站。 12、《故地新颜》(2019年,片源:孙刚) 如果鄱阳湖水上涨到漫过大堤或大堤决开了口,即使有排灌站也无法应对,整个鲤鱼洲将是泽国一片,几千条生命“如在水盆中”,将是“人或为鱼鳖”。 十连最靠近大堤,距十连10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块叫做“豆腐腰”的堤岸。那里堤不高,湖水正在逼近堤岸。 十连除了几位病号留守在营地,全部出动,在堤岸下铲土、装麻袋,两人一组,逐级向堤上搬运麻袋。一麻袋泥土,可比粮食重多了,独自扛麻袋上堤,路难走,常摔倒。于是,排成一列一列,向上运送。 在大堤上的人紧张万分,眼看着湖面一点一点地升高,大家的命运都系在一袋一袋的麻袋上。堤上、堤下每一个人,拼命干了一整夜。 天亮时,听到堤上的人大喊“湖水不往上涨了”。又过了几个小时,传来“湖水开始下降了”,大家才敢松口气。 傍晚时分,堤上堤下奋战了近20个小时的十连教职员个个精疲力竭,撤回到干校宿舍,换成其它连队接防。 十连则在宿舍休息,就地待命,准备再战。父亲将这段经历写进了给马雍的回信中。  致马雍 一九七零年 孤洲耕地人, 多谢勤相问。 千里赐佳音, 路远心声近。 忽闻奔大堤, 八月长江汛。 草草复君函, 纸短言难尽。 除了双抢,“抢修大堤”亦是北大鲤鱼洲人之共同记忆。“那时,大家都是以命相搏呀。万一决堤,就全完了”。 六连的小伙伴告诉我,她父亲和六连老师扛着“重如千斤”的大麻袋(实际重量过百斤)踏着木板上大堤,亦是生死不顾了。后来她父亲发觉胸口疼痛难忍,被准许去南昌看病,一拍片,两条肋骨已压断。她瘦弱的母亲,同样和人扛着麻袋往堤上送。 我虽未亲历,但从父亲的文字和小伙伴的讲述中,依旧感到当时惊险万分之情景,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和悲哀。 我到了鲤鱼洲后,那年的夏秋之际,忽然又传出准备防洪,告诉我们(小学生)紧急集合令一响,只可带一个小包,立刻要跑到外面去集合。那一阵,即使是小孩,神经都是紧张兮兮,似乎紧急集合令随时将到来。小伙伴们互相交流,小包里装些什么? 忽然一天夜里,集合令真的响起了,黑灯瞎火地找衣服,惊吓的我浑身发抖。忽然,我妈喊了一声,是“演习”(她是否提前听到消息了?)我才从慌乱中缓过神来。 那次是“演习”。后来听说北大干校撤离后,鲤鱼洲数度遭洪水淹没。我们听到,无比唏嘘,父亲更是沉思良久,终究意难平,当晚记录于笔端。 14、<鹧鸪天 忆鲤鱼洲> (一九八零) 初到孤洲似梦中, 丛丛野草浪涛汹, 五更挑土泥泞路, 三月秧田冷雨风。 经酷暑,忍寒冬, 辛劳两载转头空, 不知当初谁圈定, 百万书生去务农。 稻色金黄又是秋 这年(1970年)十月,第一批下放鲤鱼洲劳动的北大教职员届满一年了,每个系都换走了一小部分人回到北大,父亲依然是继续留在鲤鱼洲的劳动力之一,当时他感觉“教书是无缘的”。 留下来的人,在鲤鱼洲过了中秋。军宣队从北京运来了月饼,下放劳动人员每人发两块。月饼名叫“自来红”,是当时北京最流行、不是唯一也是排列第一的月饼(我真想不起来,那时北京还有其它月饼吗?)。 月饼很硬,但是大家都吃了。月饼馅是红绿丝和冰糖块,大家吃出了百般滋味,五味杂陈。 15《浣溪沙》(中秋节,于鲤鱼洲) 一九七零 巍巍庐山枕碧流, 时光飞驰过中秋, 风摇芦苇自飕飕。 日落西堤牛进舍 云开东岸数归舟, 争看明月照荒洲。 我后来去农村插队,中秋前就听说队里派人去城里买月饼了,中秋晚上知青发月饼。那一整天,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村头的土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拉月饼的驴车进村。 在知青期待的眼神下、老乡们羡慕的目光中,那晚我们吃了北京的“自来红”月饼。依然是那么硬,馅里依旧是红绿白,同样,我们亦吃出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鲤鱼洲一年,父亲感概万千。写下一首《鹧鸪天》聊表心情。 16《鹧鸪天 来鲤鱼洲一周年有感》 一九七零年 稻色金黄又是秋, 文思未绝复何求, 闷雷有意常惊梦, 破帽无情也恋头。 诗易写,信难投 赣江北去却东流, 潮声仿佛春蚕曲 吐尽愁丝再不愁。 鲤鱼洲人之共同遭遇,共同经历的种种精神与肉体之磨难,使“闷雷有意常惊梦,破帽无情也恋头”两句,在鲤鱼洲北大一些老师中暗自流传开来。 父亲的生日快到了,这是他只身一人在鲤鱼洲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17、《木兰花》 已到三十九岁的最后几天,有感而作 一九七零年 悠悠江水长堤树, 漂泊十年茅屋住。 逢人不再问家乡, 只说荒洲新去处。 外村来往渔舟渡, 最怕天寒风雨路。 凋零黄叶落无声, 几座滩头无主墓。 如果说孤寂、回京无望、教书无缘,还是个人之感伤,亲睹民间疾苦,旧墓新坟青草黄叶,对一个有良知、富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则是更大、更深切之悲哀,更痛切、更沉重之煎熬。 18《相见欢 四十自述》 (一九七零年) 几经风雨悲欢, 志未残, 试问人间行路有何难。 时如箭, 心不变 莫待他年空叹鬓毛斑。 不屈、不甘,自我激励,不负时光,父亲为40岁及今后之人生定了调,亦正是他勤奋终身,笔耕不辍,诲人不倦之人生写照。 鸣谢:本文得到鲤鱼洲小伙伴的鼓励和支持,文中多幅照片由他们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杏花春晓》文章精选)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