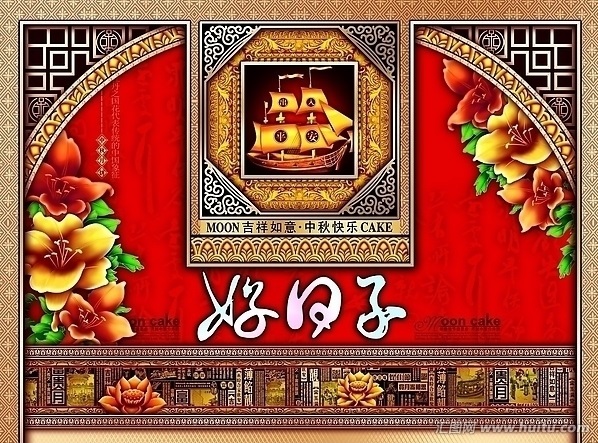 若说这四十年什么改变令我印象最深,我想,恐怕是吃这件事。 从记事起,我们庄子上的人,虽然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一年四季,只有麦收过后可以吃上两三月的细粮,其他时间都是以玉米、山芋及杂豆、高粱为主食。玉米面做饼,口感很粗糙,要是有点油、拌些葱花,做成锅盔饼,倒也好吃些。 但是油从哪来呢?邻里们常用三钱大的酒盅互相借油。母亲把油滴在用玉米衣做成的油絮子上,在铁锅里抹一圈儿,油锅便滋滋地冒出油香味。山芋面做饼,趁热吃还可以,一旦冷了就像铁疙瘩,根本咬不动。好在住在我们家一个院子的三大娘,会用小苏打和面,做出的山芋面饼松软可口,还带着点香味。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吃饭开始实行桌餐制。女同学饭量小,又时常碍于面子不好多吃,剩余的饭菜往往让同桌的男同学沾了大光。每天早上两个二两馒头,一大碗稀饭加咸菜,中午和晚上四两米饭加一毛五分钱左右的熟菜。饭吃完了,剩下点菜用开水一冲,就是一个汤。那时油珍贵,汤喝完,饭盒几乎干净得用不着洗。偶尔星期天,到校外小吃部买几根油条,或者一毛三分钱一碗的辣油面,算是开一次荤。然而即便几根油条一碗面,还是有同学花费不起。 因为吃的重要,那个年代很多的生活交流往往都与这个话题有关。亲人朋友见面问候,时常是关于吃:吃过啦?吃过啦。吃了没?吃好啦。高中毕业后,我被抽调到公社的工作队,任务就是怎样让社员多打粮食吃饱饭。时逢1977年麦收,开镰收麦的头天晚上,为了动员社员们出工,我和生产队指导员、队长、会计四人倚靠在队里油坊的磨盘上,没有油灯,借着月光开会分配任务。早上队长从庄子东头往西喊人,指导员从西往东喊,会计在庄子中间两边呼应,我负责敲打挂在树杈上的一块破铁铧犁。 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到上塘”的文章,其中报道了我的家乡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举措。这年暑假回家,听庄子上的人议论,大队里的田分了,牛分了,手扶拖拉机也分了,有些人一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来,多少有几分担心。但到了春节放假回家,陡然觉得庄子上人的脸色大不一样了。原来是新举措施行后的第一季,粮食及花生等农副产品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人民日报》中写道:“我们走村串户,只见地里场头,到处晒着山芋干、玉米、豆子。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垛。有些社员家里,连堂屋、睡房的地上都堆满了粮食。”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人还是那些人,田还是那块田,粮食却一下子多得像泉眼里冒出来一般。年关期间,正好那年工作队的指导员来拜年。我说起那年四人催社员下田收麦子的事,问他现在社员下田还要人催吗?他笑而带着几分严肃说,那是啥时的事啦,你家的粮食你不去收,你指望谁呀?现在人们的能动性都大得很呀。 生活一天天实实在在地变化着。生产队的粮仓不见了,家家户户的粮垛子堆得高高的。公社干部再也不到田里来估产,再也不说粮食被麻雀吃掉多少,再也不催交公粮。人们不仅吃得饱而且是吃得好。老家庄子东边有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邻居,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迅速胖起来,方方的脸膛有了油光。村民们餐桌的菜肴丰富了,主食多样了,平时无事还能喝些小酒。再到后来,各类外来快餐、饮料、水果的引进,让乡里乡亲也尝到外国人的口味是啥样。 现如今,人们见面吃没吃的问候少了,却把“瘦了、苗条了”作为欣赏的语言。一度养活千万人性命的山芋、玉米等粗杂粮,在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被渐渐“疏远”,而随着健康饮食、健康生活的理念的兴起,这些粗杂粮又成了人们的“香饽饽”,重新回到饭桌上。 由饿肚子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从将就吃到有选择的吃,一个“吃”字的背后是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发展脚步。它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缩影,是我们日子变好变甜的重要标志。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