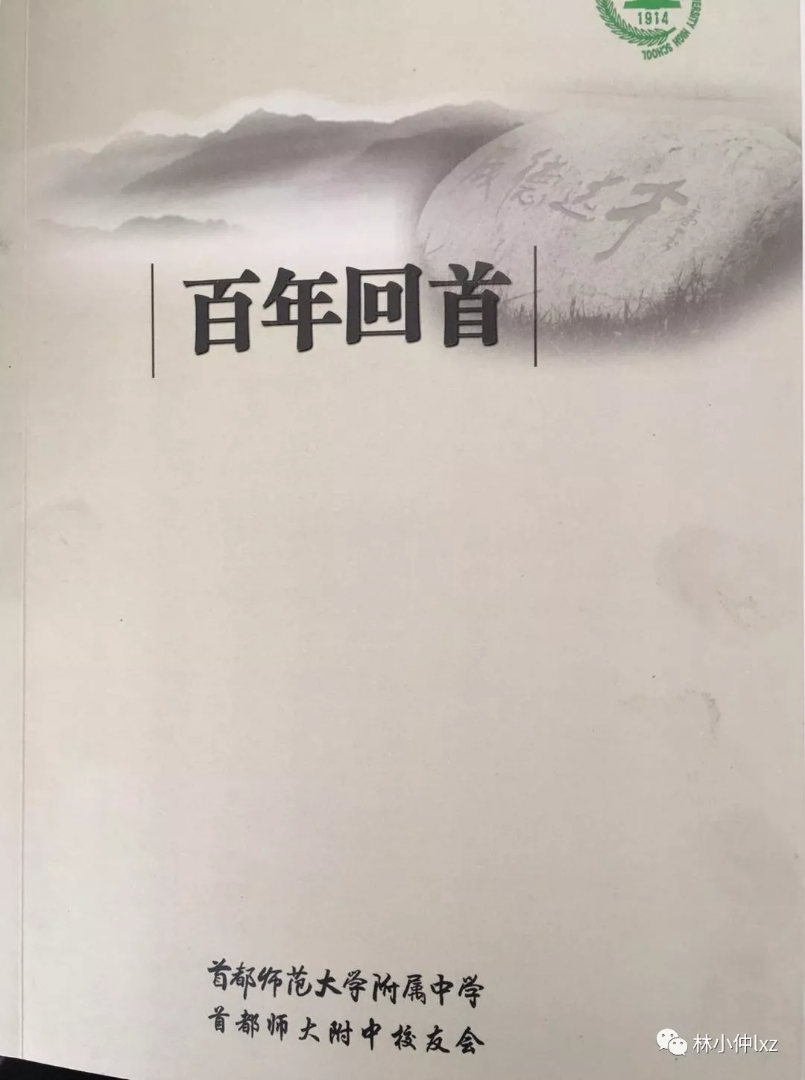 北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大附中)是我中学的母校,也是我少年时代的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父母相继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年仅23岁的妈妈,千里迢迢将襁褓中的我送回四川老家,我在外公外婆居住的自贡沱江边度过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 我妈妈胡文鸾1954年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附中任教,先教中文,后教英文,并先后在这两个教研组任组长,三十余年,直到离休。 1955年在43军的三姨将我从四川接回北京,五岁的我立刻被附中绿树成荫的校园所吸引:飞机式的建筑格局,三层的教学主楼如同飞机的双翅,大礼堂则如同机舱;紧随其后的是东西对称的两座宿舍楼如飞机的后翼,再后面是宽大的操场。现代化楼房与枝叶繁茂的乔木相衬,中西合璧,给校园凭添了几分优雅和温馨。我家住在紧邻后操场的一排平房,曾经是当年建校盖楼时民工的工棚,稍加修缮成了教师宿舍,那里曾住过十户人家。夏天的晚上,大人和孩子们围坐在葡萄架旁,能看到北京夜空中满天的星斗。  对于我这个重返都市的孩子来说,校园内的楼房、自来水、电 灯、抽水马桶,乃至校园的花坛,教师休息室的麻将桌、留声机都使我好奇,成为淘气的对象,不免惹出闯祸的故事,当然这大都发生在我上小学之前。师院附中多年来都是北京市重点中学,我中学时的同学有许多来自复兴路沿线部队大院,也有知识分子和工农子弟。1963年,上初一时,我们还都戴着红领巾。 我的两个班主任使我一生难忘。林淑珍老师教生物,她是我在初一(6)班时的班主任,那时候刚刚步入而立之年,落落大方,白皙的脸庞,端庄的神态,一位有过很好学养的大家闺秀。她待我和同学们既像大姐姐,也像妈妈。我上课经常涂鸦画小人书,招致科任老师到我的班主任林老师处告状。记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到生物实验室谈话,她批评了我几句,我还没怎么样,她倒掉起眼泪。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埋怨我不争气,从学习说到了我的着装,她数落道,你的衣服弄得这么脏,哪一点像老师的孩子!我姓林,你也姓林,你就不能为我争争气?接着她让我把打球时扯破的上衣脱下来,一针针帮我补好。她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好好念书,更多的是要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2018年春天,我与同班同学于子夜、林小涛、苟洪斌、任国华千里驱车,五位年近七旬的学生到河南平顶山探望年过八旬的林淑珍老师,附中师生情同母子。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是我在初二(4)班的数学老师李纯熙。他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数学老师。现在我们同学聚会时,还能回忆起李老师的执教精神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让同学们倾倒。李老师年轻时身体不是很好,脸色有些苍白,给人贫血的感觉。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年代,使得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给他造成精神压力,但并未阻挡住他尽职尽责地教书育人。  我敬重我的语文老师赵芝力,一位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才子。他的中文功底很深,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谈笑举止无不透着文人的潇洒。一些常见的词句,一段在我们看来平淡的文章,被他从文学殿堂到市井习俗娓娓道来。我后来上大学,听过不少教授讲课,像师院附中语文老师那种水平的真不多见。他从文学作品分析中,为我们讲述对社会和生活的观察方法,点评分析审美的独特视角。 我的英语老师杨时谦讲课时,双手伏在讲台上,重复着某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面部表情颇具喜剧演员特色。我喜欢优雅气质的张惠钰老师的历史课,她有闽南人的娴雅文静,讲课引人入胜。郑旦华曾是我的政治老师,避及那些枯燥和程式化的政治教育,学生们却被她口若悬河的热情吸引。刘子厚是一位有学养的语文老师,他没有教过我,却与我很亲,新中国十年大庆时,他将九岁的我扛在肩上,参加天安门的国庆游行。 我们尊敬的艾友兰校长15岁就成为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出生入死颇具传奇,他的家曾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站。艾校长对事业投入,对学生们关爱,他为附中的建设、发展辛劳了一辈子。艾校长,洒脱的儒雅气质,谦和博学的大家风范,才思敏捷的精神状态,都对师院附中教师团队和学生们有着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革”给艾校长和他的同事们的灾难和屈辱,是那样的残酷和深重。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艾校长在学校被长期关押,除了因为是校长外,他曾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解放前领导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艾校长的姐夫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张大中。这样一个红色的家庭背景,一夜间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他遭受了后人很难想象的非人待遇。艾校长的女儿艾亚平是69届的学生,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只有15岁。在兵团她遇到一位师院附中的女生,当那位女生知道她是艾校长的小女儿时,眼泪夺眶而出。这位部队大院出来的“老三届”女孩,曾和班里另外几个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过艾校长。她还记得艾校长脊背上被抽得伤痕累累,她不停地向艾校长的女儿道歉。事后艾亚平曾将此事告诉父亲,艾校长却宽厚地说,那时她们还都是孩子,责任不在她们。 我和“老三届”的师院附中校友们经历过浩劫年代前后截然不同的校园。“文革”前的校园靓丽和美,校园内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篮球场外常常围满观看的师生。在李明忠老师的调教下,师院附中的男篮身手不凡,名列京城中学前三名,从这支队伍中走出过日后国家篮球队队长黄频捷。女篮队员们也可圈可点,她们大都成为校内瞩目的明星人物。清晨操场上活跃着热忱亢奋的晨练人群,白天各班课堂呈现着认真生动授课场面,中午学生食堂热闹欢快,晚自习教学楼日光灯下坐满勤奋苦读的学子。那时同学间相互友好,即便是开国将军、部长的子女们也大都为人朴实低调,很少用门第作为炫耀的资本。 “文革”使这一切发生了逆转。1966年陷入空前浩劫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北京的中学,师院附中同其它学校一样卷入了政治漩涡。6月7日以后,红卫兵的军用皮带抡向慈爱的师长。工作组进校后,许多教师被打进了劳改队,“红色恐怖”使善良的人们无一能够幸免于难。教导主任赵幼侠是一位执着敬业、清丽柔弱的女老师,她受到非人的摧残和凌辱,带去终生难以平复的创伤。被冤屈戴过右派帽子的喻瑞芬老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我目睹了她那衣不遮体的惨状。校园里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嚣,从校门口一直到食堂内外贴满骇人听闻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同学反目,师生对立,而斗争的主力却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部分中学生们为何一夜之间变成草菅人命的打手,中央关于那段历史的决议给了明确的答案。 1966年9月,我随学校近百名同学,到群山环抱的门头沟清水涧帮助秋收,与老乡同吃住一个多月,同行大多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谁也不知道家中已被“文革”划成异己的父母是否会祸从天降。10月6日至10月28日,师院附中老红卫兵也组织了180多名师生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劳动,他们在当地受到好评。1966年11月,我们二十多位同学结伴而行,跨越河北、山西、陕西,在寒风中,历时一个月徒步长征到延安。1967年1月,北展剧场多次举办声势浩大的辩论会,对立的中学生们在争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5月29日,北京各中学的老红卫兵近300人在天安门广场演出《红卫兵组歌》。6 月2日,700多各中学“四三”派红卫兵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展剧场公演。两派中学红卫兵的演出都有师院附中学生参加。在各自梦回吹角连营的悲壮之余,抗争居然成为中学生们的生存需要。从8月到9月,我们也有冒着全国武斗的枪林弹雨,扒火车南下,在郑州、武汉、长沙等地串联受困的经历。而后,北京夜幕下的长安街和烽火硝烟的清华园及许多中学,都留下我们成群结队骑自行车呼啸而过的身影。更有当“逍遥派”时,集体住校,白天在校园打篮球,晚上翻墙到昆玉河游泳,深夜聚在一起讲福尔摩斯故事打发时光的日子。 1967年,师院附中与北京各中学一样,学生中也出现“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三派鼎立,剑拔弩张、相互对峙的局面,“文革”思维和封建血统论是导致学生分裂的根本原因。我们也有过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揭竿而起成立学生组织的经历,校园里数百人之众颇有声势,现在回头想来不过是抱团取暖而已,那面“北京师院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旗帜被我们带到插队的草莽关东。那时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哪里知道水深浪险。各派学生组织的领军人物表演落幕后,殊途同归,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当做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 军训团进入学校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他们指定的革委会和红代会。1968年之后,“老三届”的学生从暴风雨中的校园直接走向社会,除少数幸运者当兵、进厂矿外,绝大多数人开始了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达1700多万,历经大起大落磨难的“老三届”中的多数人,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老三届”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这一代人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应该是他们对培育过自己的母校的最好回报。  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尽管当事人视角、立场不同,我们都有责任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法制制度的确立是何等重要。我漫步在首都师大附中的校园中,儿时的建筑格局已荡然无存,绿树丛中的蝉鸣带我穿越记忆时空,恰同学少年的身影使我又回到学生时代。学校是春华秋实的园地,教育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社会生活里人文素质堪忧,有待于中国教育的升华与改变。肩负着百年历史传承的母校,走过了跨世纪的风雨沧桑,校园里最美丽的依然是青春和希望。 林小仲2014年一稿《遥远的校园记忆》,为纪念中学母校首师都师大附中建校一百周年而作,刊载于校友会编辑大型纪念回忆文集《百年回首》一书。2019年1月重新修订,本文二稿刊登于此。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