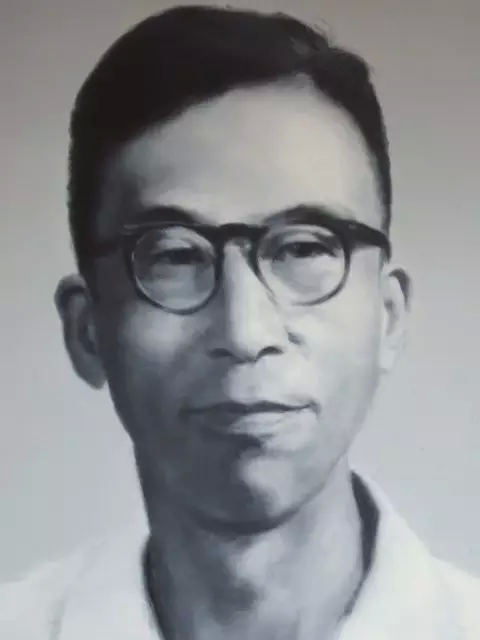|
按照当时领导上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刊登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还没有看到过学术水平比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随孙冶方、徐雪寒两位前辈之后竭力主张黎澍采用这篇文章。不久以后,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试刊”送到我手里的时候,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不久以后,当创刊号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却又不见了。 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当时,“开动机器,解放思想”的口号还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重大的步骤出台,文革的阴影还重重压在人们心上。顾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他的目的实际上要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的原因。他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资本主义”这个词就可以引起人们的神经过敏,尽管这是马克思说的,而且作者还注明了出处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顾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这句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写的,那正是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年月,而我的一九八0年一月读到的时候还只是为他的爱国心所感动,为他那千难万劫都不磨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所感动。我没有能像他那样充满信心地预见: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我们就很快会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着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孙冶方同志一再声明的他在五十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这个八十年代的新交郑重说起过,还特别在临终前嘱咐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说明这一点。冶方同志对顾准的古道热肠是其令人敬佩的。)顾准从一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身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五十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幺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十年的时间,先研究西文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他在三个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五月二日)的时间里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虽然它既没有完稿,也没有达到使自己满意的标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感到启发多多了。 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这话五四前后的先贤其实也是讲过了的,但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做笨功夫的榜样。他为弄清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一个框架里而得出一个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用模式,比如:中国有没有同西欧所谓的奴隶制一样的奴隶制?人们今天通常说的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是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原来也有人根据常识意识到了的。问题是迄今未见有什幺人肯下笨功夫来做这样的比较研究,而顾准却赍志以殁已经二十一年了。 《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的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顾准自幼出嗣外家,因此而改姓顾)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十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就起来也真是万幸,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私人之间的通信,讨论所谓“理论问题”也是十分危险的。“四人帮”还在监视着每一个人的思想,这些笔记只要被一个善于“上纲”的第三者发现,通信者就逃不了“现行”的罪名,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不是专着,这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 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工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 在当时一片要比照巴黎公社的榜样建立“北京公社”与“上海公社”实行直接民主的喧嚣声中,他论证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见诸于古代的希腊城邦,而不可能实行于后世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间接民主,只有政权容许“合法的觊觎”的有制衡的政治。顾准本来是把民主当作为自己的目的来追求的,但是探究的结果却认定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或者就目的)是进步。 为了揭穿“四人帮”蛊或人心的假革命的骗人口号,他分析了欧美政治史上两种不同的潮流与传统,论证了法国一七九三年式的潮流和传统势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独裁的皇权,由人民的专政变为对人民的专政。他揭示了这种假革命的哲学上的源头在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与基督教一神论的结合,在于黑格尔式的“真善一致”的绝对精神。他说,“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幺,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是可悲的。” 顾准无休止的探索一直到对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规律”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是为他的来自基督教的世界模式论服务的,然而它们既不能为经验所证明,也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相违背。 《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且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能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已是孑然一身而且病入膏肓去死不远的人了。他自己也想必知道他的“奋斗到底”其实不会有什幺人理睬。他明明白白说自己是在“喃喃自语”。但是他还是要写,要用他自己说的"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写,一直写到死。虽然他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却不是为市场而写作的。 下面的一段话也许最能表明顾准的思想历程: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的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 “娜拉也走以后怎公样?”这是顾准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使顾准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寻根究底的精神。 有人说,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也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的顾准。 在那“史无前例”的时代,被称为挟“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以袭来的大风暴当然也震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的反思,但是谁都没有像顾准那样执着,样用功,想得那样全面,那样深刻,那样彻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笨”! 据说我们现在又进入了第二个文化热的时代,其特征是国学热。顾准没有能如他自己所计划的那样,在完成对西洋史的研究后开始对中国史的研究,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也自有真知灼见。他指出,“没有世界史的对比,中国历史其实是不可理解的。”“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社会心理有不少零散然而精辟的论点,我诚恳地希望有志于振兴国学以促进中国“雄飞世界”的学者能够从顾准的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后世决不能忘记的是:顾准地在什幺情况下求索的。当然,“自古圣贤多寂寞”,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如果说在中国被戴上帽了成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劳改的人并不少的话,像顾准那样被迫与至爱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却又终不免自杀,子女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自己还不得不签具脱离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这样的地步:永远不会与他划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虽然与他同在北京,也因为他的身份而始终被阻至死未能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但是这样的苦难也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始终为祖国的命运,人类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写作。在顾准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大女儿才读到父亲的遗稿,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读后记:“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幺呢?!” 顾准才智过人,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强调他的女儿在写完上面那段话以后引用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的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的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人们以为的程度。”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