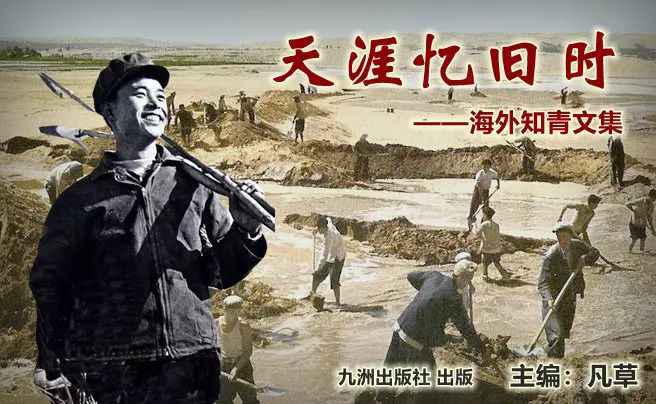|
上山下乡到了1974年已经形成了一定制度。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月每人十元钱,用来购买国家定量的粮食。买粮要去二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粮站。第年开始国家不再管,知青和农民一样从队里分口粮。十元钱,买了粮油还略有盈余。第一年我们还常常买蔬菜。一年以后,菜就很少了。分的油吃不了几个月,一年有一半时间没有菜油,当然也就谈不上炒菜。佐餐的主要是辣椒和从城里带回去的咸菜。 做饭先得学会生火。大灶烧煤,得先点燃麦草,然后一手拉风箱,一手持煤铲加煤。烧的煤是从三十里外的县城拉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找不到窍门,满屋是烟,火却腾不起来。农民一般家里有老年人做饭,而我们总是下工回来后再做饭,不外是蒸馍(馒头)、烙饼、擀面条、熬玉米茬子粥之类。一下工,就得赶快挑水做饭。做饭手脚还得快,蒸馍最费时间,尽量放在晚上。麦收忙的时候,常常饭还没吃到嘴里,上工的钟声就响了。 除过第一年的生活费,接受了知青的生产队还会收到一笔专用款,用来给知青盖房子。我们在饲养室大院的士屋住了两年,等着给我们盖房。但拨下来的钱早被队里用来应急。两年后,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院子。那是一个按照当地式样盖成的农家院子,里面一半院子是对檐儿房、中间是天井,两边的房子房顶后高前低,向中间斜下来。一边几个女同学住,另一边朝着天井的一面是敞开的,做厨房和放粮食农具的地方。外面一半只有西面盖了房子,是我们两个男知青住的地方。 因为是给知青盖房子,因陋就简,料定你们住不长。房基地是原来村子东南角的大路,大路向东移了几丈,不再从村子里面穿过,我们的院子就坐落在从前的路上。多年的老路比周围的地势要低一些,拉来黄士垫平,仍然是松软的,住进去不过几个月,一面院墙在一场大雨后塌掉了半边。 一到冬天,北风就从房子的门下和房檐下的椽缝中灌进来,我们用麦草和棉壳塞住房檐下的缝隙,用麦草编成草帘子,挂在门上挡风。挡住了风,可挡不住那冷。当地人多烧火炕过冬。我们一来不会烧,二来也没处去捡烧炕的柴草。所以屋子里没有盘炕。睡的仍然是床。没有床板,在土坯砌成的两个土墩上,架上叠了几层的晒棉花的竹箔,铺上褥子就是床了。寒夜无眠,在院子里烧一盆火,乘火旺烟低的时候端进屋子,可也只能维持一会儿。清晨起来,屋里挂的湿毛巾常常是冻得硬梆的。 从外表上看,知青与农民的一个大差异是穿的衣服不同。农民的衣服,特别是男人的衣服,多为土布,一般只有黑白二色。白色是本色,黑色是染出来的。土布是妇女从棉花开始,搓捻、纺线、织布,在漫长的冬夜一步一步完成的。木制的织布机往往透着黯黑色,不知道已经伴随过多少代人。农民穿的鞋也是手工做的,鞋底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妇女上工一般都会带着鞋底,歇响的时候就纳上几行。 村里只有适龄的女子和年轻媳妇会穿花衣服,许多是定亲或结婚时男方送的。当地女子十四五岁就说好了婆家,一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不过二十岁就出嫁。常年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人显得老相。一生孩子,几年后就不再穿花衣服,成了说不清年龄的婆姨。男人则只有那些当过兵或家里有人在外面公干的人家,才会穿上洋布的衣服。有些孩子多家境不好的男人,衣服每每要穿到鹑衣百结。夏天的时候,许多小孩干脆是赤条条,不沾一缕。 知青的衣服当然不会是士布的,许多是城里父兄的工作服。农民的棉袄多为紧身小袄,棉裤的裤腰宽大,可以折起来,再用腰带系住以为保暖。我们的棉衣多半较为宽大,或是城里的短大衣,为了抵住旷野的寒风,经常用一根麻绳,拦腰一系。如果有人能搞到一件军大衣,那可是好东西。白天可以御寒,晚上顶半床被子。
当地农村很少有机械,一个公社十七个大队(自然村)有一个拖拉机站,几台拖拉机或是跑运输,或是辗转各队帮助翻地,但后者的次数有限。我们队里一台手扶拖拉机,时好时坏,用处不大。上面的柴油机经常被拆下来另作他用。比如停电时用来带动磨面机。运输主要靠马车,或是靠人拉的架子车。每年麦收时,我们队最吃紧的就是靠一挂马车、一挂牛车把地里的麦子运到打麦场上。 给人们生活带来最大好处的机械似乎是磨面机。除此之外,现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在化肥和机井浇地这两样上。为了提高产量,化肥在当时已经广为应用,有些地已经因为用得太多而出现板结。机井是利用打井机械打出的深井,用电动或柴油抽水机抽水浇地。但这只是辅助,真遇到大旱,全靠浇水是不成的。日常用水仍然得用镳轳从十几丈深的井里绞上来,再一担担用水桶挑回去。 没有机械帮助,农活主要是单调的体力活,简单重复,只要不惜力,那是很容易学的。下乡的第二年我就成了一级劳力,慢慢地也学会了那些带点儿技巧的活计,比如扬场(用木锨把碾好的麦子均匀地扬起来,借风力把麦皮吹走,脱粒的最后一道工序),推土车(又高又重,只有一个木制的独轮,饲养室推土起圈用的,不会推很容易翻倒),打墙,以及盖房的小工。 我干过的最重的活要算有一年交公粮。因为是一批育种的小麦,粮食得用麻袋装,一袋二百斤左右。粮食由拖拉机运到县城的库房,我们去了五个人,拖拉机卸了车后,我们负责把麻袋过秤,再扛进库房,扛上好几米高的麻袋垛。二百斤的麻袋,两三个人架起来,放到扛的人的肩上。麻袋堆得像小山,上去的路是麻袋堆成的楼梯,一个麻袋一级。那是得一口气冲上去的,一停下来,就登不上去了。我们干了大半夜,不知道卸了多少辆拖拉机拉的麻袋包。 碰到有晚上干的活,队长经常会找到我们,农民一般不大愿意熬夜、离开热炕头。通常晚上要干的活是浇地,机井抽上来的水,顺着水渠流到地里,管的人要看着让水顺着一垅地流过去,发现跑了水就得赶紧堵上,浇完一垅再浇下一垅。这活并不累,但是磨时间。最难受的是天冷的时节,漫漫寒夜,只有幽深的夜空和闪烁的寒星相伴。黎明前是人最闲的时候,可也是最冷的时候。 不是农忙的时候,干活并不太累。干得多,吃得多,那是要费粮的。况且是给队里干活,给集体干不等于给自己干。因此一般干活都是悠着来,不能太快太猛。农闲的时候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农民常常是在混工分,这是大锅饭的通病。不过这工分好混也不好混,到底时间摆在那儿,每天从早到晚不得闲。一下来仍然会饥肠辘镳。农忙的季节当然又是一番景象,因为那时的活儿是必须干完的。 最辛苦的是夏收时节。“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进六月(阴历五月)全村就紧张了起米。只待“夜来南风起,小麦复垅黄”,就开镰割麦。麦子主要是妇女和弱劳力的活,精壮劳力负责把地里的麦子运回来。拉麦子的人每天微明即起、到了地里,用木叉把麦子挑起来,装成高高的一车,用绳子绑住。然后护着马车到场里再卸车。中午天热,牲口休息,人不休息,在场上整理麦垛。下午一晌要拉到天黑才停下来。六月的炎阳下,汗湿透的衣服一下就干了。每次卸完车,就跑到旁边的饲养室大院去喝一瓢井水。即便如此,仍然是暑热难当。有一年夏天,等麦子上了场,我们一个车的人有一大半嗓子暗哑失声。 麦子上了场,可以歇口气,所谓龙口夺食,算是夺到了一半。另一半是紧接下来的打场,也就是脱粒。那也是要集中全队力量的事。天刚亮就得去摊场,把麦上的麦竿拖下来,在碾得一平如镜的足球场那么大的场上铺上厚厚的一层,让太阳把麦竿晒干。吃完早饭后,套上牛拉着石滚子在场上一圈一圈地碾,把麦粒从晒干的麦竿上碾下来。前面碾过,后面的人再用木叉把碾平的麦竿挑得隆起来,以便干得快一些。然后再晒,再碾。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开始起场,用木叉把表面的麦草挑起来,抖一抖,然后把麦草收走,下面剩下的麦粒、麦皮和土的混合物用推板和扫帚归成堆。然后是扬场,借风力把麦皮和土吹走,剩下的才是麦粒。 起场的时候,全村人人上阵。偌大的场上,人声沸腾,尘土飞扬,煞是紧张。如果运气不好,天边翻起黑云,夹着夏天的阵雨呼啸而来,那就得赶快把碾了一半的场匆匆收拾起来。夏收的时候,人们不会混工分,那是要出全力的。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尽在于此。整个夏收要持续一个多月,等夏收结束,每个人都晒得又黑又瘦。白居易《观刈麦》一诗中有言,“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一千多年前的描述仍然是那样贴切。不知是时光倒流,还是时光把这块土地遗忘了。 多年之后我驱车经过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看到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田。联合收割机在行进中把麦子割下来,同时把脱好的麦粒直接倒进旁边行驶的卡车里。于是我想起了那些曲背弓身割麦子的身影,堆得高高的拉麦子的马车,尘土飞扬的打麦场,还有被烈日烤干了汗水的人们。
开始上工没用多久,劳动两个字就失去了那个时代赋予它的光辉。干活就是干活,简简单单的沉重的体力劳作。刚开始的时候,年轻人难免莽撞,风风火火。一起干活的老农就会说“忙嘛的,地里的活哪能干得完”。干活的日子久了,方才体会出这句话的沉重。 于是日子在一天天单调的周而复始中流去。没有书看,没有色彩。那是没有什么亮点的生活。单调贫乏的生存缚住了梦的翅膀,而我们这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知识青年,最灿烂的梦也不过就是招工进工厂而已。对于世界上存在的其他多姿多彩的生活,我们根本无从知晓。那些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大多数只有当兵才能走出去。知青有的时候会走村串队,找同学聚一聚,特别是在下雨天不上工的时候。不过各队情形大致相当,并没有多少新鲜事。于是多半是打打牌,穷开心而已。记得当时买不到扑克牌,我们玩儿的牌是自己做的,最好的一种是工厂的工人用一种硬塑料片做的。有时大家聚在一起会唱歌,唱的歌有许多是口头传唱的。有些是不知道什么人编的,有些是把一些老的曲调重新填了词。歌词多半反映下乡知青的情感,辛酸凄苦。与当时流行的革命进行曲迴然不同。记得当时同学中流传过一本手抄的《外国民歌二百首》,我们从上面学了不少歌。 那几年,农村少有娱乐。不记得村里有什么专门的娱乐活动。冬天本来是农闲的时候,是陕西农村一年最好的时光。忙了一年,那是该赶庙会,唱大戏的时候;老人和婆姨家在烧着热炕的家里蒸白馍,准备过年,年轻人成帮结伙牵着狗满塬上撵免子。可那几年正在学大寨,号召农闲不闲,要求人们深翻改土,把坡地变平。县里、公社一级一级下了指标,要求上报深翻改土的数字。于是,农闲变了农忙。连过春节的喜庆也冲淡了。 然而,古老的黄上地是不会让人们轻易忘却自己的根的。村里的生活仍然尽可能地遵循着几百年的风俗习惯。人们按节令走亲戚,娶亲先纳彩礼,送葬披麻戴孝。而一旦外力的控制减小,生活就又弹回到旧有的轨道。到1978年的春节,学大寨已经没人提了,牵狗撵兔子又开始露出苗头。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一份报纸,是《陕西日报》。报纸送到农村,已经是日报的几天之后。不过那时的报纸反正没有什么好看的。偶尔生产队开会,开会前等人到齐的时候,有时会抓个人来念念报纸,算是关心时事,然而没有什么人会去听。旧报纸多半被拿去糊了墙,或是卷旱烟抽了。 偶尔公社放映队会到村里来,在老槐树旁的空地上支起银幕,放露天电影,不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部老掉牙的片子。即便如此,如果傍晚听到相邻村子放电影的广播响了,年轻人还是会走几里夜路去看电影。如果有什么剧团下乡唱戏,年轻人会十里八乡地赶去看戏。一般的收音机只能收到一个陕西电台,而一般人根本没有收音机。有些人家有有线广播,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歇响的时候,大队部的大喇叭会响那么一阵,播播新闻。人们最想听的是秦腔,不过广播和收音机里只有“样板戏”。 村里人常有人说起从前的老戏,也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才子佳人或帝王将相的戏目。有些戏目已经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在当时却都是属于受到批判,被禁止的一类。偶尔会有个老人念叨起戏文,于是几百年的传承就在支离破碎的讲述中续下去。其实,就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传统在民间的延续而言,这些老戏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村里也有人还能唱出整段的老戏。有些老的曲牌是可以即兴唱的。在陕西多年我没有学会听秦腔,总觉得那唱腔近乎声嘶力竭地吼。唯一一次被秦腔打动,是在一个晚秋的下午。我们一行人赶着牛在村南扶犁耩地,在秃黄空旷的田野上慢慢移动。一个村民扯起嗓子唱起了秦腔。唱词在旷野上飘散了,那嘶哑的声音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仍然是吼出来的秦腔,但那是从心底流出的声音,当地人所谓的唱凄惶。无需丝竹管弦,在空旷的天地之间,只有这吼出的唱腔才最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