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又回一次凤阳。那时移民澳洲已十六年。 以为离得远了,久了,渐会忘记,却不料,越发想了。 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借了辆旅游车,请了个司机,半夜十一点多上海出发,一路几次停车问路,天亮时,“大溪河”到了。 往事如烟 变了。新街很宽,能开四辆车,两旁全都砖房,有的二层楼,公路从街心穿过。老街还是二三米宽,还是曲曲拐拐,一段泥路一段碎石路,还仍见不少茅屋,这辈子忘不了的茅草屋顶的泥屋。 “看,这屋还在,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打煤油。” “记得吗?这里原是饭店,开店的叫老顺子。” “这里,看这……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七一斤……” 一路走,一路说。 原先的公社办公所前停下。 是幢楼房,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幢砖泥结构的楼房,过去时代土匪的炮楼。这楼第一次出现知青眼里时,很破,很烂,但渐渐,越来越高。当年这幢楼里走出的人,眼睛都朝上,当年这里的知青,都仰头看这楼里走出的人。 即使最清高的,也做过接近这幢楼的梦。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不再说话,看着那楼,猛烈抽烟。 往事如烟,飘过来,飘过去。 老街稍作停留,正式下乡。先去阿五的庄。 两个孩子的指引下,阿五找到了毛杰。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也读过书,当年特别喜欢和我们这些下放学生玩。见阿五,他倍感意外,把我们热情请进他家。 屋挺大,砖房瓦顶。墙上几张印刷画,画中是女人新鲜的脸。有电视机,尽管老式,但想不到。有电灯,一根电线接一灯头,房梁上绕一圈,荡下,插一个灯泡。想当年,做梦都想有个电灯。还是泥的地,地上一团团鞋上刮下的泥,有的仍是湿的。没家具,一张床,一张缝里嵌泥的桌,还是一根凉绳东墙拉到西墙,绳上挂满四季替换衣服。 坐一阵,聊一阵,庄上转一转,和遇到的老乡一起照几张像。 毛杰送我们出村,临走,阿五硬塞他一叠钱。 “当年他年对我很好,帮我挑水、买粮,买了粮还帮我从公社挑回来,这些都是当时的我不能胜任的……那时,我常吃白饭,没菜,也没钱买,他常送碗盐豇豆、割把韭菜给我……” 踩着稀烂泥地,进萧良的庄。 萧良当年吊儿郎当,给“贫下中农”印象最不好。他爸是高干,为让儿子早日离开农村,找了很多关系,来头都很大。几次,被逼无奈,萧良上了省城,但临到最后一刻,父亲的信,还是被他撕了,扔了,或当手纸擦了屁股。他离不开农村一帮哥们。一个人离去的路,即使通天堂,也寂寞。 萧良有个相好,是知青,也是同校一起下放的同学。这女生自己不觉得,庄上却多了个单相思。一晚萧良去她那,被那单相思发现,半夜赶去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一听,小蛮子搞流氓,那还了得,当下找了两个民兵,徒步七八里,赶去抓人。“你逃不掉了”。一到门前,部长大喊。萧良也绝,知道逃不了,床都不下,像只鸵鸟,身体拢成一线,躺直,蒙上被。他以为自己个小,不动,不会被发现。被窝里拖出后,他被五花大绑绑去公社,关在炮楼里。那女生够意思,去看他,还买了烟,从窗口扔进去。后来,领回生产队前,部长指示,要开批判会。批判会上,萧良一声不吭,手拿毛巾,坐小板凳上,一次次,装着擦汗,擦掉大把大把的泪。 萧良找到了他当年住过的屋。屋还在,只是已倒,剩下几面断墙,墙内乱草齐腰,一条水牛在吃草。 “照张相吧。”我说。 他不说话,也不看我,走到断墙前,站好。 照片上的他,头发都秃了,头顶只剩小鸭绒毛般一撮。他穿件西装,里面一件红毛衣,双手插口袋。他笑着,是傻笑。他的眼睛是红的,看得到里面闪动的泪。 刚来时,萧良发疟疾。那时我们都发,高烧四十度,温度表打到头,萧良是第一个。找不到医生,只能上公社。队里要派人送,我们都说不要。我们说不要,是为都被一幅画所吸引:一条水牛,拖一辆板车,牛背上坐我们中一个,头戴草帽,手执柳条……太神气了,太富诗意了。队长想劝,劝不住,只能站在村口目送我们上路。 疟疾这病发起来怕人,不发时,也就身子疲软。萧良躺不住了,非要坐上牛背,由他赶车。一上牛背,心漾开了,笑了再笑,还一再问,自己像不像神仙牧童,大家都说就少一根短笛,他就双手做个吹笛的样,嘴唇闭成一条缝。“吹”着,越发得意,叫我们统统坐上车,然后柳条一下下抽牛肚……牛小跑起来。开始没人在意,想当然认为:牛老实,吆喝几声再加几鞭就行。可越抽,牛跑得越快,牛一跑快,拖着的板车就晃荡,板车一晃荡,左右前后一摆、一冲,车柄便一下下重重捅到牛屁股。牛疯了,彻底疯了,飞也似的奔跑起来。我们一个个板车上滚下,萧良吓得脸都弯了,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牛背上下来,临到最后一刻,才闭眼朝这路边草丛一个猛扎。 疯了的牛,一气奔进一条水沟,绳断了,板车像从炮膛里射出来,车柄深深扎进沟边的泥里……我们愣了,吓愣了,面如土色,半天张着嘴,没人说得出一句话。 阿五问,记得那次杀鸡吗? 那次,阿五和萧良来我这,我们去老乡那买了只鸡,又去大队部小店打了酒,准备美食一顿。没人会杀鸡。萧良说,一刀砍下鸡头就是。我说太残酷。阿五自告奋勇说他来杀。可他哪是杀鸡,是锯鸡。刀很钝。他用钝了的刀在鸡滑腻的颈皮上拉来拉去。拉半天,破一点皮,见一点血,再拉,总算见骨头了,见血一股股流出。老乡教我们,杀过后,只要将鸡颈弯过来,塞到翅膀下,扔到屋外就行。我们没扔,而是人道地将鸡放到屋外地上。然而,刚返身,只听身后一阵“扑腾、扑腾”,那鸡挣扎几下,站了起来,被锯一半的头颈软绵绵地荡下,吊着个血淋淋的头,跌跌撞撞朝我们直冲过来。那不是鸡,是鸡鬼。我们吓得魂飞魄散,逃进屋里,这个跳床上,那个跳桌上,“人飞蛋打”。 饭后,一起出去逛荡。没地方逛,就去浩浩荡荡的漫天湖。 一边逛,一边唱。唱的是插队的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进了历史史册,一去不复返。 迎着太阳起,背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是我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踏遍了偏僻异乡。” 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但那天都喝了。一个个喝得晕晕乎乎,脸彤红。阿五红得最厉害,从脸红到颈脖再红到手。最离谱的是,停下小解时,大家看到,他连鸡巴都是红的,彤红彤红……看得我们一个个叫着、笑着,跌倒在漫天湖里…… 还是忍不住 去过萧良的庄去我的庄。 根据方位知道,庄子已在附近。可这魂牵梦萦、醒里梦里“见”了千百遍的地方,就在左右了,我认不出。 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车看看。 下车,见路边不远墙根下坐一排晒太阳的妇女。我朝她们走去,想向她们打听一下。可走着,游移的目光不再游移,停住了。那些看我走过去的妇女,目光也停住了,有了反应…… “这不是……这不是……” “是是是……黄惟群……我是黄惟群……。” 赶紧几步上去,和她们握手。一个,两个……刚握两个,又觉得自己不行了……试图忍,忍不住,不得不转身,背脸,朝一边挪去…… 我已认不出这地方、认不出这庄子,但我认识这些人,她们让我确定,我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 她们,曾经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生命紧紧联系一起。她们,每个人每张脸,都是一段记忆。 老了,都老了,但透过覆盖着的老相,彼此都能在对方脸上找到那张熟悉的曾经年轻过的脸。 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说:“……这都多少年了……” 来了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当年是大队民兵营长。原先在外当兵,复员回来后,当了大队民兵营长。他问要不要上庄走一走?我说好。 先去我当年住过的地方。 原地已造出新屋,是砖屋。屋前坐几人,其中一中年妇女,一眼认出了我。我也记得她,大家叫她小邱,当年庄上少有的几个小媳妇中的一个,性格温和,胖乎乎,总笑眯眯。 我努力笑。 “看看谁来了,谁来了……”她朝屋里叫丈夫。 她丈夫叫亮子,和我差不多年纪,当年主管队里喷雾器,专喷“520”农药。可他没一点常识。那天,在我的牛屋,为查机里还剩多少药水,他点燃火柴伸头去看……“哄”一下,“520”喷火了,喷他一脸……脸烧坏了,眉毛也烧没了,谁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可结果,他还先娶上了老婆。 小邱说:“你原先的屋就在这。”我问:“哪?”她说:“就这,就我们这个屋。”说着又问:“去不去家后看看,那里还剩一堆土,是你当年屋子的墙。” 毕竟是女人。 感激她,非常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还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没去看那堆土,不想太伤神。 我对萧良做了个手势,让他帮我和亮子小邱还有民兵营长一起照几张相。不知还能做什么,只知什么都带不走,除了几张相片。 走出家门,见几女孩,小邱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女儿。” 女孩大约二十岁,挺漂亮。于我,重要的不是漂亮,是气质。她已完全不像农家女,而像学生妹,像城里人。 她和我的过去没关系,我离开时,她还没出生。面对她,我能开口了。 我问她多大?现在干什么? 她一甩眼,扬眉反问:“干吗?调查户口呀?” 我笑了。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笑。不仅为她,也为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不同了,语言也不同了。 庄上的最后日子,我住小登子家。 小登子出生富农,父母死了,姐嫁了人,哥因破坏军婚被关牢。小登子每年一半时间在外,不是讨饭就去哪打短工。我那牛屋倒后,生产队安排我住他那。在他屋里,我教过书,开始教“扫盲”,后从一年级开始正式教。我还在这屋里自己动手糊过几排桌,是用泥和芦杆糊的。 写过篇《小登子结婚》的小说,是根据原形写的。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鸡巴头挑被单喽。”那家伙翘老高。一次次,他撅个肚,用手打得那家伙东晃西晃停不住,一边则一脸正经,咬牙切齿望着它骂:“狗东西,割了你,你就老实了……” 门敞着,可家里没人。 小登子家没变。附近左右就他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杆扎的房顶,唯独不见的,是我当年教书时糊的几排学生课桌。里间是我当年睡觉的。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有张床,床上铺了条凉席,床旁一条板凳上,堆了些小孩衣服。 我问民兵营长,小登子结婚了?他说早结了,已有两孩子,都五六岁了。 写《小登子结婚》时,没想到他真有结婚的一天。 庄上转一圈,回到停车处。人越聚越多。一张张脸,猛一看,不认识,停上一二秒,全都能认出。 一个年轻人走近对我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记得吗?”仔细看,认出来了,我教他时,他大概十岁。另一青年也说做过我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他们一起照了相。 告别老乡,车开不远,下车,站路上,对着那片土地,我又默默望上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到哪,都跟着我。 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谁也别陪我,让我独自一人,在这土地上,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我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坐下去,想叹气就叹气,想流泪就流泪。太久了,憋得太久太久。太多记忆,太多太多,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的记忆,甩不掉的,这辈子甩不掉的。甩不掉的记忆,只有迎上去。这滋味,也许很苦很涩,但是苦是甜、高兴欢喜或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太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我万里迢迢来这,为的就是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即使是痛苦,也是享受,痛苦的享受。 萧良喝醉了。返沪途中,午餐时,小半碗的白酒,一气喝了三四碗。 萧良以前也醉,醉了就哭,边哭边说他爸不喜欢他。他是独子,父亲的最爱。劝他,劝不住,他说他爸喜欢的其实是他妹……开始大家以为是真,后来发现,只要是醉,他都这样哭这样说…… 这次不同。车在开,他不坐,站着,摇摇晃晃,一会脱件衣服,一会又脱一件。大冬天,脱到最后,只剩一件棉毛衫。边脱还边说,说他自己没出息,既不是富商,又不是作家。开始,我们还帮他“开脱”,说你一个服装店,一年收入一二十万,你那高干爸爸还在黄金地段给你留了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可说着发现,他醉了。一会他说,要点把火,把阿五的钱全烧了,一会又逼他投资,还不能投他处,只能投大溪河,并拍着胸脯豪迈地说:“不到大溪河非好汉”。说过阿五又说我,他说你算什么作家?你写过大溪河吗?不写大溪河算什么?算狗屁!他还说要把我的澳洲护照烧了,他出钱,帮我重新申请一张大溪河护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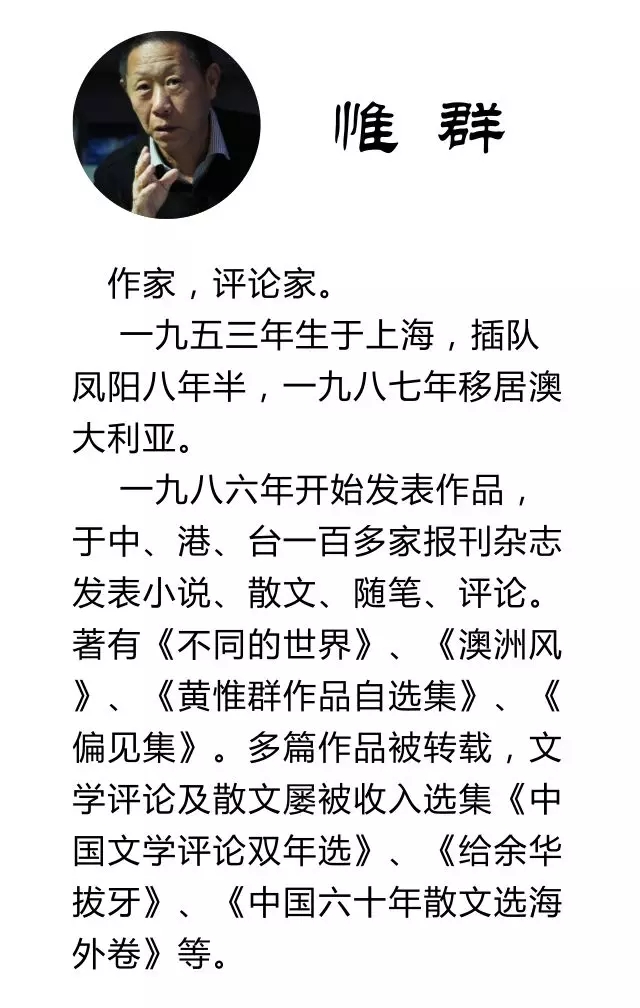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