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年年底,离开凤阳八年多。 八年多时间中,刻骨铭心的插队记忆,无时不刻出现在我、我们的生命中。那时已决定移民澳洲,要走了,得回凤阳去看看,不管曾经的生活是否苦难,这片土地养育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子。 坐火车到蚌埠,找到插队时的同学小何。 小何早一步上调,进了蚌埠铁木家具厂。他是同学中对文学最有兴趣并最具天赋的,我们走得近,聊得多,一起在田埂上朗诵过普希金、泰戈尔,也一起做坏事偷过老乡的鸡。他去蚌埠后,他的宿舍是我们一伙乡下知青的“据点”,谁上蚌埠,都去他那,来去上海,蚌埠转车,也去。他宿舍的门上,终年放把锁匙,任何人随到随进。有时半夜,掀开被,冰冷的身、冰冷的脚,不管不顾地往他热烘烘的被窝里钻。睡他那,还吃他那,闲时他陪,忙时,他给饭菜票,我们自己去厂里食堂。 86年,他读完电大中文系,88年,他去日本一桥大学读语言学,硕士读到博士,完了留校当博士后,专业上颇有成就,出过两本过硬的专著。 他,就是常言所称的“赤屁股朋友”。 伤心的小站 蚌埠没停留,当天小何陪我下乡。 一路谈的是写作。那时我的所有作品,写的都是插队生活。 第一篇小说《黄土》,开头第一句: “火车钻进了茫茫无际的黄土,消失了,剩下两条亮晃晃的铁轨,阳光下静静卧躺。” 他说:“像一幅画”。 是的,一幅画。一幅刻在眼里的画。 火车把我们带来,卸下,走了,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连同希望,从我们刚刚起步的生命中带走。 我俩曾一起逃票去蚌埠,怕被抓,蚌埠前一小站下车,然后徒步二十里,一路问询,找过去。是夜晚,漆黑一片,唯有淡淡月色,忧伤、柔和、温暖,伴些许兴奋。翻过一座山,见城市灯光了,久违的灯光,带来的强烈亲切感,让两个长居农村的人兴奋得颤栗。 晚上,火车站长椅上坐一夜。那时上蚌埠、去南京,都在车站椅上过夜。天一亮,赶紧呼吸城市空气,捕捉细枝末节的城市记忆:柏油马路,两旁的商店,穿过树叶落到水泥地上的阳光气味,挤车的人群,汽车喇叭的鸣响,空气中弥漫的水果清香,身边来去的干净整齐的衣服...... 蚌埠坐长途,先去凤阳城。 凤阳中学的老友徐兄,上外法语系69届大学生。本该前程似锦,因文革,梦想破灭,学业中断,先下乡劳动,后被分到离我插队处十八里的地的板桥中学当语文老师。 板桥是个区,我所在大队原属大溪河公社,后划给江山公社,江山属板桥管辖。 徐兄是我一亲戚的朋友的内弟,认识后发现,我们还是远亲。插队时,每次赶集,我都去板桥中学找他。每次,他都用他的煤油炉为我开小灶,炒许多鸡蛋,然后一起喝酒,听他说很多话,说当年上外法语系的风光,说精英班的才子感觉,说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教师,说他有过的几个女朋友。曾经,他骑车十八里,到我插队的生产队看我,在我的牛屋住了一晚。他给过我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帮助,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当他的听众。那时他其实很痛苦,他是在用幸福的追忆驱赶内心真实的痛苦。而于我,和他交往,成了安徽生活中一个亮点,一团可贵的温暖。 离开安徽很长一段日子,老做一个类似的梦,梦中,我从上海、南京、或蚌埠回生产队,板桥车站下车后,一如既往去找他,可突然发现,他不在了,找不到了。没有了徐兄的板桥,无际空旷,无际苍凉,空旷苍凉得我发慌。 86年,和他一起分到凤阳的六九届大学生都走了,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出了国,有的调去了大城市,只有他,娶了蚌埠太太,留在当地。 那晚,我和小何睡在他那,聊天到很晚。什么都不敢多说,怕他受伤。他也什么都不谈,不谈调动,不谈考研,不谈离去的同届六九届大学生,只谈刚来他这住过一阵的老父亲。 安徽的冬天太冷,怕父亲受冻,他坚持和父亲睡一被窝,坚持把父亲的脚按在自己的胸膛。他说小时父亲也这样帮他捂脚,他说父亲的脚已完全没有热量,他说父亲想挣脱但他使劲按住,却同时,眼泪失控地唰唰流下,他说他爱他的父亲,很爱,从小他的父亲给了他无限宠爱……他唯一没说,他是在用他的孝道惩罚自己,惩罚自己的失败人生。 到凤阳当晚,徐兄和小何陪我一起去县农机站看望小高。 小高是我中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非常漂亮,当年学校一二千人,她从操场上走过,目不斜视,却有那么多眼光不约而同随她而去。插队凤阳时,她和我是一个大队的知青。 一次,大队知青会上遇上,说起了话,从此,就都想再说。 后来,她来我这,我去她那,很频繁。每次她来,我都送她回去;我去,她又送我;她送了我,我当然再把她送回去。来来往往,月光下,那段乡间的路,缠绵起来。 那年冬天,和她一起回上海。我说,到南京坐船吧。我想坐船时间长。她说好。她说好时,脸上漾出了喜悦。 火车上,两人合吃一个盒饭。轮船上,趴着栏杆,望着海水,同说少男少女的话。 到上海,她来我家,然后约好,我去她家,然后再约好……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次又一次。电影院里,靠得很近,她的鬓发,带着体香,抚弄我脸腮。我们轻轻地说话,轻轻地。 那次电影院出来,过马路,突然出现一辆车,她惊了惊,一下抓住我的手。过了马路,她还抓着。希望她一直那样抓下去……可到底,她松开了。那手软软的,很柔,从我手心手背慢慢脱离,滑了出去。 “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道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列车还没到达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列车开走了,继续向前。站台上,灯光昏黄,飘着雨星,站着她孤零零一个。 她和县城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在了当地。 那晚停电,走道很黑,找到她时,她正在屋里,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看着说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起身,但马上,又控制住自己,一付矜持。“回来看看呀?”她说,甚至没请我们坐下,只说了声“自便”。 我们没坐多久,坐不久。我说,走了;她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 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泪流满面 第二天,告别徐兄。 这一别,十八年未见。我离国时,他正调往蚌埠,因彼此变动,失去联系。很多年,到处打听,一直找他,可找不到。十几年后,我请朋友——澳洲安徽同乡会会长帮助,几经周折,通过合肥侨联找到蚌埠教育局,再通过蚌埠教育局找到蚌埠民事局,终于知道他已调回上海。然后,又通过市公安局朋友,在几个同名同姓的人中,到底找到了他。徐兄已退休,返聘在一中学当教导主任。 人生,由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组成,不能让一个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人,一个曾经给过我帮助和温暖的人,说“不见”就不见。 离开凤阳城,我和小何先去临淮关。 最后几年,我常一人步行去临淮关。回沪前买花生去那,分到棉花想弹成被带回沪,也去那,上县城,临淮关又是必经之地。那里还曾有个知青朋友,分在砖瓦厂,寂寞时,常去找他,在他那过夜,和他说说话。 汽车到站了,在街口。 路边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煤渣路,坑坑洼洼,一滩滩大小积水,再前面是铁轨,亮晃晃的铁轨。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的卡其脱卸面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正在努力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是“喷”!一时间,差点失控,想不管不管地扑在地上,抱住土地,放声大哭一场。 使劲忍!拼命忍! 喉管断了似的疼,眼泪早已成线,不往下淌。 街这头到那头,来回二十分钟,眼泪,就那样不停地流,不停地沿着脸腮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临淮关到石塘坐的是汽车。以前乡下没汽车。 一路无语,石塘到江山中学,八里地,我和小何都没说话,一句没说。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说而没说的话,不用说。 看天,看地,看村庄,天认识我们,地认识我们,村庄认识我们,脚下的泥土也认识我们:“回来啦?”“回来了。”“去了很久了。”“很久了。” …… 远远,看见了江山中学几排教室。 “家败,这不是黄惟群吗?”阳光下,毛校长手遮太阳远远招呼道。 学校老师全都走了出来,惊讶,欢喜,热情洋溢。 “结婚了吗?” “结了。” “在哪高就?” “厂里。” “听说小陈混得不错,大医院当了医生。” “是的,他不错。” 问这问那,我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将要出国。这块土地上,感觉不该说这些。 学校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插队的生产队,五里地的路。 队长陪我们东头走到西头,散了很多烟、很多糖果,这事以前插队时也做。西头陈姓几家屋前坐一阵,匆匆赶回江山中学,那里的老师们等着我们。 当晚睡在付老师家。回城第二年,他父亲带庄上三个社员去上海卖猪肉,晚上找到我,我和我妈让出房间,睡去邻居那,留他们住了一晚。付老师说,他父亲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要把我们请去他家。 熟悉的夜,静谧的夜,不时几声狗吠,难以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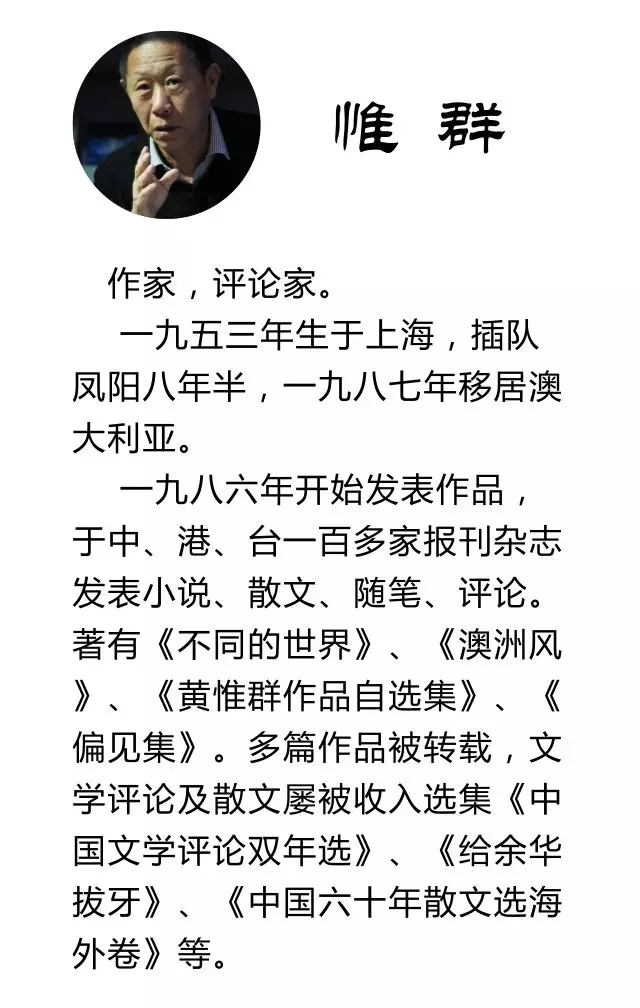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