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0日,是“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逝世20周年,他是我岳父施士元先生的挚友。两位寿逾九旬的核物理学家之间的友谊,绵延78年之久。 我手头存有王淦昌老伯给我岳父的13封信。第一封信是王淦昌为从事核弹研制隐姓埋名17年之际,于1965年11月21日悄悄写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一封信是1997年3月16日写的,赠我岳父《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一书,距王淦昌逝世只有1年零几个月时间,他还在忙碌不休。 王淦昌与施士元于1920年同时进入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首届,拜读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宗师门下。当时清华物理系一共4名学生: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钟间。1929年毕业后,王淦昌与施士元都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王淦昌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被爱因斯坦称作“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物理学家麦特纳女士;施士元到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两人都是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1933年施士元在巴黎大学作博士论文答辩(右二为居里夫人)
从王淦昌的信中能够领略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亦可看出王伯的谦虚品德和敬业精神。我们小辈也与王淦昌多有接触,深感他的学者、长者风范。 王淦昌特别谦虚。为祝贺他八十寿辰,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7月出版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其中以苏步青先生的贺诗代序,由周培源先生作序,汇集了杨振宁、李政道、钱临照、钱三强、程开甲、周光召等50多位科学家和亲友的文章。收进该书首篇的施士元所写《从核物理黄金时代谈起——为祝贺王淦昌八十寿辰而作》一文,系统评述了王淦昌卓越的科学成就与艰苦奋斗精神,称赞他“西马反超泡室前,国际风云路八千;投身核弹研制中,沐阳山沟十几年”,“几十年来,他日日夜夜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才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惟其难能,因此可贵。际此寿辰,千里之外,高举美酒,敬祝一杯”。王淦昌一再婉拒对他的高度评价。他在1986年7月15日信中写道:“我自己知道天资既不高,努力学习又很不够,以至蹉跎几十年毫无建树。同志们为我八十岁写文章,是万万不敢当的。但我也无法不让大家写。只有恳请你们不要写。”信中他还幽默风趣地说:“‘王淦昌受其学生们的景仰,……但美好的事物我们都希望保留下来。’我建议把这段去了,因为我并不为我的学生们景仰,也不能和大熊猫相比。” 
王淦昌
1991年11月19日他在信中再次表示:“士元我兄惠鉴:你好!手书敬悉。关于你要为我在现代物理知识上写文章,我感到非常惭愧。希望不要再写了。原因如下:你在《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那本书上已经写得很多很好了,我也为此很感激你。” 王淦昌的贡献之大,不是本文所能说清的,但仅从他赠送给我们的为青少年所著《无尽的追问》一书,就可以得知,1969年、1975年和1976年的我国三次地下核试验,都是他在现场直接指挥的。他说,1969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一些领导干部还不能出来工作,组织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1975年和1976年的“这两次试验也是我现场指挥,到第三次试验时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不过我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一直坚持在第一线,坚持亲自检查,逐项验收”。 王淦昌不让人称呼他“大科学家”,遇事常说“我不懂”。例如1990年3月16日信中称:“士元我兄:你寄来的大作The Structure of Electron(《电子结构》,编者注)我又送给了我们研究院的较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请他们看看,他们的答复现在附上,请你审阅。我因不懂,无法参加意见,只能转达,专此。即请研安!”有一次我和夫人施蕴陵去看望他,他对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教的蕴陵说:“你的专业我不懂。”他从来不以担任某种领导职务为荣。他在1965年11月21日的信中写道:“原子能所的职务只挂个空名,并无实际联系。”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又写道:“本拟回京后即写信给你,因为不断的会议,致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只得等开完会(连续约有五个会)后,始能有暇写此信。其实开会我只跑跑龙套,没有起什么作用。看来龙套还得跑。实属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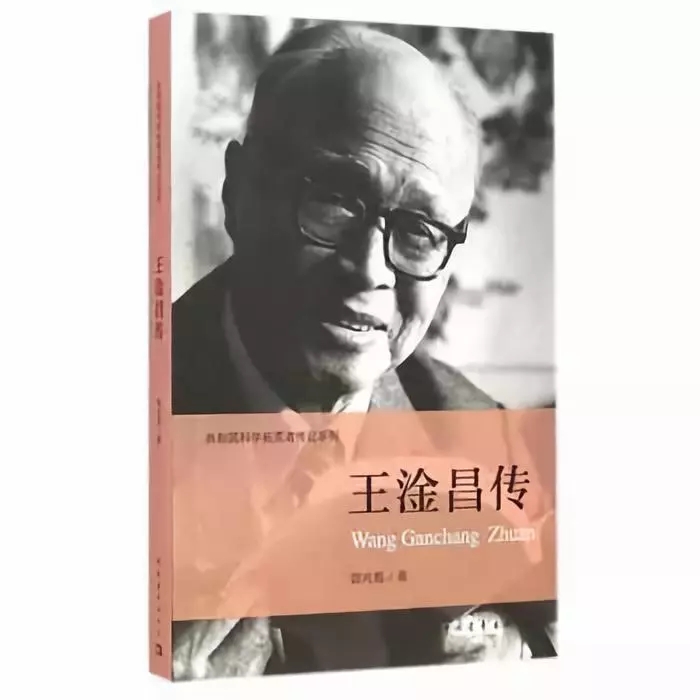 王伯特别重情谊。这更多表现在学术交流方面。例如,他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关于氚靶的问题,据我了解,都是进口的(据说从苏联进口的),你们可得到,我建议要求承担些任务。例如测高能中子对某些元素的非弹性散射等……”1989年9月13日信中还谈到:“我前些日子,去苏联一次,是应那里的老朋友邀请的。去了二个星期。……除Dydha的联合所外,还参观了高能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设备都很好,经费也很充足。比我们是好多了。但我国若能少而精,也未必比他们差很多。”他们二老既是同学同行,又亲如手足。1965年11月21日王淦昌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很多时没有见你,很是想念。前次看见你校鲍家善魏荣爵两位教授,曾请他们向你多方致意。近来在物理学报上常看见你发表的文章,足见你的研究工作,仍是活跃,很是钦佩。……便时希望常通通信(通信交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院宿舍X楼X号),信可以由我家人转来(只是费些时日)不胜盼祷。弟淦昌上”  二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南京再见一面。时光又过去十年,1995年3月19日,王淦昌在信中说:“今年4月中旬将去上海。若有机会将来南京看望你。我的次女仍在南京师范大学。我经常和她电话联系。在此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在南京的电话号,因为这样我可以和你电话联系啊。” 次年2月7日,他在信中写道:“士元我兄惠鉴:久未通音,思念为劳。前得清华校友通信第32期第89页见你与吴健雄先生的合影,很是高兴,特此祝贺,还有你为叶老师企孙的铜像揭幕仪式赠的油画一张,我也看到,非常好,也向你祝贺。我现在仍如以前,非常的忙。但很想来南京看望你,1995年我去了上海,很想来南京看你。惜未成行。下次有机会必来看你。”1997年2月14日的信中介绍了他去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四川成都、绵阳,广东深圳以及上海等地的感受,称“见到各地都兴旺发达,与十年以前大不一样,实属可喜”,还说“今年也将去杭州、上海一带。若有机会,必来南京拜访我兄。最近友人为我出一本书,伺机当送上不误”。 
施士元
王淦昌的信中还表现了他对两人共同相识的学者和朋友的关心,如多次提到周培源、袁翰青诸位先生以及他们在清华的同班同学周同庆先生的健康状况。 令我们尤其感动的是,王伯将对我岳父的情谊转化到对我们小辈身上。1966年2月5日在信中写道:“您的二位女儿在北京工作,我从前听同庆兄谈过,但把名字忘了,真糟。请您再告诉我她们的名字和住址(一位在北大?离我家很近)我去联系,请她来我家玩玩。虽然现在我在外的时间较多,但仍有不少次数回京。”此后,信中一再牵记、关怀我们。其中,1984年7月9日的信中写道:“刚才与俞邃同志通了电话,知道他家里都很好。你的女儿蕴陵同志要到8月初才放假。又要去昆明开会。他们都是骨干分子,忙也是应该的,很好的。”1993年2月12日于信中说:“前些时候,看见令媛蕴陵同志及快婿俞邃同志,非常高兴,特别因为蕴陵身体非常健康,和以前判若二人,堪为庆贺。”由于我是二老之间的实际联系人,王伯在1989年9月13日的信中说:“令婿俞邃同志为人最好,经常有联系,关于你的情况,都是他告我的。我很感谢他。”1986年5月,我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王伯来我家中看望,并赠我派克笔和俄汉词典。他还解除了我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引发的对那次旅程的顾虑。 王淦昌非常关心对后代的培养教育。上面提到的《无尽的追问》一书,是1997年12月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讲述他毕生事业的科普著作。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每当我在马路边空地散步,看到一群群小学生、中学生走过,一种责任感就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尽力多做一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我本人则亲历王伯一件感人至深的事。1998年7月,90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的王淦昌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我的母校江苏省如东中学60周年校庆题词,写下苍劲有力的“面向新世纪育才树人”9个大字。当时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感慨地对我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再给我5年时间也好呀!”  王淦昌的高尚品德,与我岳父之间的深厚感情,铭记在我们小辈心中,成为鼓舞我们上进的动力。 (本文刊于2018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