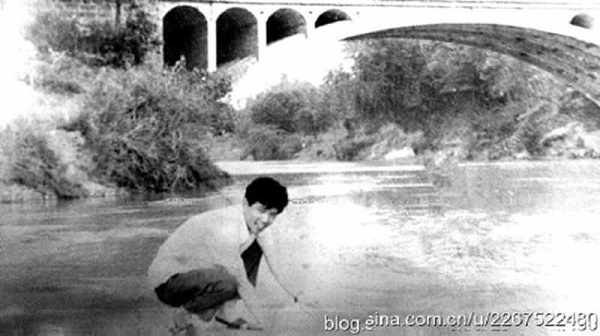|
人们常说:河流是人类的母亲,它涉及人类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及未来发展。澜沧江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是一条哺育东南亚多国的母亲河。流沙河被称之为西双版纳的母亲河。澜沧江被称为古老而美丽的“众水之母”。也成了让世人不无遗憾的“无源之水”。流沙河是位于西双版纳西部的一条主要河流,干流长近一百公里。据说“流沙河原名南哈河”。“南哈”,是句傣语,是当地傣族对西双版纳流沙河的称谓。古代西双版纳傣族便称此河为南哈。由于此河主要流经平坝,河床上多沙无石,故名为“流沙河”。 70年代初期,刚到兵团时见之的就是那亚热带的风光。当时年少,对初见的一切刻骨铭心。人生难忘是初识。眼前的蔗田、蕉林,甚至是那亚热带气候的阳光及吹来的热风都伴随最初踏上社会的记忆。对当年的流沙河怀着别样的情愫。 遗憾是如今当年那一条奔腾不息、清澈纯净,急流湍急,河的上游是卵石的流沙河,早己失去当年的秀美灵气。我喜爱当年的流沙河,那时的流沙河沿岸,果林茂密,花草遍野,竹林满坡,水源丰富。随着两岸土地的大量开发利用,森林资源骤减,河水流量已不及从前。沿河两岸已逐渐被西双版纳林立的高楼和田园风光取代。到处是连片的橡胶园、茶园、果园。昔日高大乔木与竹林交错的景致,西双版纳流沙河因源头坡陡源短,干流河床平而多湾,每逢遇到连日暴雨,源头洪水夹带泥沙涌入干流,时常造成大小不同的灾害。 我对流沙河心驰神往,看着那缓不济急的流沙河,它仿佛是一股盛满情感的水流,含着泪,带着微笑,挟着波涛,伴着歌声,淙淙地流进我的心田,缓缓地在我脉管里流动。 当我离开版纳,调回上海时,我发誓,一定要来到流沙河边,掬一捧清冽的河水,浇灌我这干涸的心田,因为那长长的河水,流淌着我当知青时那些长长短短的故事……。 那是刚到兵团不久,我与指导员(军人)一起在团部参加知青工作会。为了早点回连队,指导员说带我走小路回连队,比坐车往营部绕圈要快多了。于是,散会后,我们沿着小路,穿街过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流沙河畔摆渡。 傍晚时分,太阳西斜,晚霞把村寨、胶林、稻田都染上了一层桔红的颜色,河水也染成了金黄的鳞波,连我自己也沐浴在桔红的晚霞中。这时,远处响起唱歌的姑娘来到河边,眼前已聚集了晚归的男女傣族,他们毫无顾忌地走向河里。姑娘们把筒裙拽在腋下,随着水深渐渐提到上面,最终如头巾般盘到头上,赤裸的蹬在水中。小伙则背对着女性,脱下了裤子,捂住下体也跳进河里。男女同浴的天体浴场,那时是那么平常,纯真而美好。劳动回来的这种沫浴无疑是一天中最惬意的享受……。 我听过许多人讲过,西双版纳傣族在河里洗澡是不分男女的,但是,对我一个刚从上海来到这里,真的面对眼前一群赤裸着身子的男女,真如梦神话,心想偷窥女人洗澡,在上海是要被定“流氓罪” 的。我有些羞涩,更是害怕,紧跟指导员身后,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不敢抬头张望……。
突然,一阵骚乱喧嚣,只听见河里的女孩们叫着“羞、羞……!”我拉拉指导员的军装说,她们在骂我们羞?指导员说,她们在叫“水、水……,是欢庆的意思,不是羞……”。话还没落音,接着几个赤裸的女人用水向我们泼来,她们一股劲泼,一股劲叫着“解放军,解放军,利多啊,利多多!(傣语:好啊,非常好。)……”一眨眼,指导员被泼得象只“落汤鸡”, 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干的地方。这时,我早已逃之夭夭了。 一会儿,我见岸上有几个傣族姑娘把指导员的军用黄挎包抢了下来,我大声叫着,指导员包被抢了,但没人理会,我看姑娘们在一堆竹箩旁边,往垮包里塞着什么,我真的纳闷,她们把指导员泼得水淋淋的,还要恶作剧,往包里塞什么怪东西,肯定不怀好意!我大声告诉着指导员,但他若无其事,还对我憨笑着……。 水不泼了,挎包被她们塞得鼓鼓囊囊的,又还给了我们,只见指导员两掌合十,鞠躬致意,还笑容满面,叽里呱啦的说着什么。随即,指导员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渡船旁,我走到他旁边,心里还琢磨不透挎包里塞了什么,指导员按住我的手,不让我翻他的挎包。 我们跨上渡船到了对岸,指导员问我,饿了吗?我说,有点。他让我一起在甘蔗地边坐下,放下挎包,我急忙打开,还真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挎包里装着用芭蕉叶包裹着的什么。打开来,是鲜嫩的凉鸡,真是让人馋涎欲滴的腌菜,有香茅草烤小鱼,糯米粑粑,还有一种叫“豪罗索”的傣族年糕……,更让我惊喜的是,包里还有一瓶苞谷酒。 除了这些吃的,包里还放了许多花朵,也许是傣族姑娘对解放军的一片爱心,是那样的美丽而又感人。 我问指导员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去年在傣族寨子开了一次“拥军爱民”会,以后他们就把指导员当成亲人了。我们兵团与老百姓就建起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 后来,每次我与指导员出差走在路上,只要经过傣族寨子,总会被好客的傣族拖去作客,或者会遭路边河里洗澡的傣族姑娘泼水。 据说,解放军是他们翻身解放的恩人,所以,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最爱解放军。从此后,我理解了当时流行的那句话,“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的真正含意了。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