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风起东南
1955年4月11日,一架隶属于印度航空的民航飞机,经香港机场中转后,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这是一架由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749A型飞机,注册编号VT-DEP,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 起飞5小时后,正当飞机接近印尼海岸线时,右侧引擎处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浓烟烈火迅速淹没了飞机,失去控制的飞机在半空中发出三次求救信号,最后在爆炸声中断成三截撞向海面,机上乘客全部遇难。 多年后,成元功回忆起这一噩耗,仍觉惊心动魄——作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卫士长,他清楚地记得,那架被称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上,乘客都是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而周恩来原本也是计划搭乘的,后来临时决定取道缅甸赴会,这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找来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要他调查坠机事件。这位熊副司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后龙潭三杰”之一、革命年代曾担任胡宗南秘书的地下党。在他的调查下,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空难是由国民党保密局策划、针对周恩来的暗杀事件,他们买通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在飞机引擎下安装了TNT炸药。 当时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基本都有自己的专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专机是两架C121大型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庞然大物,赫鲁晓夫看到后颇觉自惭形秽,命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了图-104客机,后来首次访问英国亮相时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轰动,极大地满足了赫鲁晓夫的虚荣心。 
图-104亮相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飞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中方曾组织航空领域人员参观图-104。面对这架当时人类航空工业的登峰造极之作,参观成员一面惊叹,一面不免发出感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己制造出如此先进的飞机? 1955年的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进行中,偌大国土上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底子,毛泽东很清楚:“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直到1965年,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乘坐的仍是从巴基斯坦租来的飞机。中国何时能够制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但关系国家领导人的安危与颜面,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能力的象征。这个问句在此后大半个世纪里反复回响,一直绵延到今天。 二、筚路蓝缕 1959年5月,中国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到苏联图-16轰炸机厂学习。当时中苏正处蜜月期,老大哥豪迈地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员说:你们上课认真听就好了,不用做笔记,回头我们把这些资料用火车给你们运到中国去。 无论苏联还是美国,最早的民航飞机都源自自家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像赫鲁晓夫的图-104,技术来源于图-95轰炸机。一向摸着老大哥过河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打算在轰-6基础上研制客机,而轰-6的技术,则来源于对苏联图-16轰炸机的仿制。 然而这边苏联老师的话音未落,那边中苏友谊的小船便翻了,苏联一夜间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所有图纸资料,至于承诺的用火车送来的资料,那就更别想了。之前认真听苏联老师话没有做笔记的中国技术员,立刻傻了眼。 万幸的是,那批学员中有一个叫马凤山的人。 马凤山,江苏无锡人,1949年考入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毕业后进入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工作。他精通俄语,在苏联学习时格外认真,勤奋地写下了厚厚一本笔记,飞机设计所需的关键试验与参数都被他巨细无遗地记了下来。 苏联专家撤走时,国内轰-6飞机的研制正进入攻坚阶段,飞机研制工作一时陷入停顿,这时马凤山的笔记立刻身价百倍,成为千金难买的技术资料。这本笔记交上去后被列为绝密文件,谁要翻阅,先得经过政审,还得厂领导签字保证。 轰-6的研制成功,马凤山笔记可谓功不可没。顺便说一句,尽管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但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轰-6及其后续改进型号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力轰炸机,时至今日,最新的轰-6K仍是中国远程轰炸机的主力选手,坊间戏称“六爷”。 
服役至今的轰-6,目前仍是中国空军主力轰炸机
轰-6研制成功后,顺理成章的,中国也考虑在此基础上尝试发展自己的民航客机。 1970年,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说了句:“上海工业基础那么好,可以搞飞机嘛”。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大飞机立刻成为炙手可热的项目,也正因为这句话,尽管上海航空工业基础薄弱,轰-6也诞生在西飞,但客机的研制却落在了上海。 1970年8月,客机项目正式立项,被命名为“708工程”,这一工程后来有一个更广为人知、也更为悲壮的名字——运十项目。 运十立项后,上海很快汇集了当时中国航空工业的顶尖人才和资源,西工大、西飞等单位都抽出大批人才支援708工程。 赫鲁晓夫的图-106座机停驻北京时,马凤山也曾前往参观,这时被调来担任技术总负责人。与他一起的参观队伍中,还有一个叫程不时的年轻人,当时正在沈飞研制军机,也在一纸调令下举家搬到上海,后来成为运十的副总设计师。 尽管得到了高层表态支持,但运十的研制仍然是步步维艰。设计团队中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调来,在上海的工作环境非常差,技术人员甚至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程不时回忆: “当时,我们借用一个废弃的候机楼作为设计室,用夹板隔了几个空间,一借就是20年。后来,还在一家飞机工厂的集装箱里办公。没人顾得上生活条件,生产是第一位的,大家就想着早点把飞机造出来。” 运十飞机是我国的飞机设计首次从10吨级向100吨级飞机目标的冲刺,但技术人员都只有设计中小型飞机的经验,无论是材料,还是设计方案、总体布局、结构,都面临着诸多全新的挑战。 当时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国内还很少见,运十团队首次尝试用在运十研制上。他们好不容易从上海计算中心申请到少量使用时间,但几乎都是在午夜和凌晨,只好日夜颠倒地干。他们留下的经验和资料后来成为经典教材,在大学里用了十多年。 
马凤山与运十设计人员
技术上的难题还好说,还有些更棘手的干扰,来自技术之外。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运十项目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无端干扰。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的马凤山,很长时间里都没有相应的职务,还经常处于被批判的地位,飞机设计工作也屡屡被指手画脚。 比如,有完全不懂飞机的人要求运十安装5台发动机,因为发动机越多对毛主席越忠诚;要求运十一年就上天,作为国庆献礼;某“造反派领导”要将铸钢的井字框用到飞机上去,幸好被马凤山阻止…… 在种种内外困难下,运十设计团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诸多难题,于1975年完成设计方案定稿。1976年7月,第一架运十飞机下线,送往西安做静力学试验。这架飞机总长42.93米,最大起飞重量110吨,可排178个座位,代表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最高水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民用飞机在适航领域完全空白,马凤山力主紧跟国际标准,带领人员翻译了数百万字资料,最后编写出《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 (CCAR-25),填补了这一空白。CCAR-25 至今已翻版多次,但马凤山主持制定的基础内容始终无人打破。 1980年9月26日这一天,运十终于迎来首飞,此时距运十立项已近十年。十年心血,成败在此一举。马凤山立下了军令状:可以用生命担保其安全性,并愿意在首飞时随机组上天。 上午9点37分,伴随着轰鸣声,运十飞机自跑道起飞升空,爬升到1350米左右的高空,绕着机场飞了两个大圈,最后在一片欢呼声中安全着陆。坐在飞机客舱中的马凤山不禁感慨万分。 
运十移出厂房
当时聚集在机场周围的数千名上飞厂职工,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传奇,刚刚开了头,很快便要煞尾了。 三、关山难越 1978年,当运十研制工作进入后期,设计团队紧锣密鼓为首飞作准备时,一支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悄然抵达欧洲,在法国、德国、瑞士等几个国家考察访问。在那里,他们被西方发达的技术深深震撼。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员工,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效率相差80倍;法国一家钢铁厂年产量350万吨,只有7000名职工,而国内武汉钢铁公司,职工是其十倍,产量还不如人家;大众汽车公司的一间工厂,每天下线的汽车就有1000辆,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轿车产量…… 考察团回国后,在大会堂向最高领导层汇报,从下午3点一支开到晚上11点,听者无不动容,大呼“石破天惊”,邓小平当即拍板要学习西方,引入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 “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大潮,已是山雨欲来。 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历史时刻,这一抉择对于彼时孱弱的国内工业体系来说,或许已是最优路径,但对于刚刚问世便被裹挟其中的运十飞机来说,真可谓生不逢时。 就在运十首飞几个月前,麦道公司总裁麦克唐纳来访,得到邓小平接见。麦道公司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颇为陌生,但当时却是美国民航三巨头之一,与波音、洛克希德三分天下。70年代后,麦道在竞争中渐渐落后,将目光投向远方的中国,其合资组装麦道飞机的提议,获得了中方高层的首肯。 运十项目的处境,一下变得非常尴尬。 运十首批次本计划生产三架,但02号飞机完成首飞后,项目便失去了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03号飞机尽管已经完成2/3的工作量,但之后便陷入停滞,完工遥遥无期。 1981年,三机部和上海市政府召开运十论证会,邀请了包括范绪箕(航空专家,原南京航空学院院长)、吴仲华(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俊奎(北京航空学院教授),以及经济、冶金、化工方面的55位专家,对运十飞机实地考察后举行评审会议。 会议给国务院提交的报告结论是:“运十的研制工作不要停,队伍不要散,成果不要丢……建议运十应走完研制全过程,取得完整的技术成果”,并提出了再研制3架、2架、1架等几个方案,但此报告上报后,未获批复。 之后,三机部向中央财经小组请求拨款,上海市也曾向国家计委请求继续研制工作,并愿意承担一半研制费用,最终依旧杳无音讯。栖栖遑遑中的运十,在那几年里试飞130架次,足迹遍布北京、合肥、乌鲁木齐等多个城市,试图争取一线之机。 1984年西藏发生雪灾,国家组织飞机运送救灾物资进藏,运十主动请缨,在除夕前一天由四川飞往西藏,顺利降落在拉萨机场,成为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大飞机。此后运十又先后六次往返西藏,运送物资40余吨,顺利飞过这条“死亡航线”。 然而,这一切将运十继续下去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1986年,运十向国家财政部申请3000万元研制费用被否决,自此项目被彻底终止。 
1985年国库券上的运十飞机,一年后,运十项目被终结。
在运十长达14年的研制过程中,国家共投入5.38亿元,其中研制费3.34亿元。这笔钱多吗?作为对比,不妨看下另一个数字:光是1972年一年,中国对外援助就有51.5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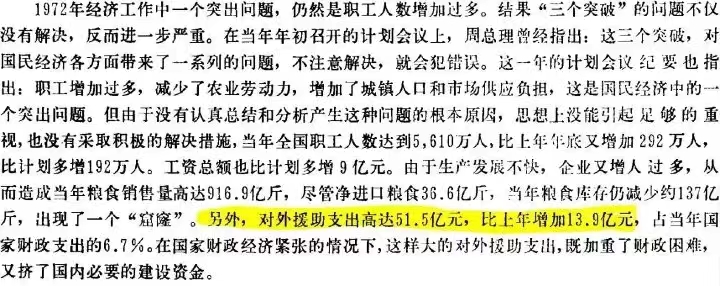 就在西藏救灾的那一年,上海汽车厂与德国大众组建合资公司,各行各业都开始开启“市场换技术”的合资模式,跃跃欲试的航空产业也不例外。 1985年3月31日,运十下马仅一个月,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与麦道签订协议,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制造运十的厂房要给MD82生产线腾地方,于是,运十生产线上的所有设备、工具都被拆除,当作废铜烂铁处理掉。 西藏易飞,关山难越;念念不忘,终无回响。 四、风雨如晦 平心而论,运十确实从立项之初便问题重重,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中国大飞机发展早期的种种问题——定位模糊、决策混乱,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的失利埋下了诸多隐患。 《中国航空报》航空专家张宝鑫说:“从出发点来看,运十并非针对民航,最初想法是为领导人出行而研制。” 运十研制团队几乎都是军机研制人员转行的,因而在设计上对运营成本、使用强度等没有像民航飞机那样考虑,要放到商业市场上参与竞争,在当时几无可能。 实际上,这也是苏联民机遇到的同样问题,苏联设计师很少考虑客机的燃油经济性、舒适度等,比如,当波音大力发展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以降低油耗时, 石油资源丰富的苏联没有及时跟上,等再回头时已被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年代,我国民航当时刚刚起步,运十研制过程中,民航并没有起到管理、协调、管控、验证等作用,连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都没有,对适航取证这些事情更是一片空白,运十可以说生不逢时。 生产管理体制上,运十飞机每个部件的装配工作,都由领导以作战命令方式下达,规定在若干小时内装配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技术人员连续作战几十小时不闭眼,饭菜都送到装配线上,连医生护士都准备好随时待命。 当我翻阅到这段资料时,只能无奈地感叹一句:精神可嘉,然而,工程技术自有其客观规律,当某些东西凌驾其上时,结果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种种,多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运十的折翼总难免让人感慨唏嘘,视为巨大遗憾。 运十研制的时候,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国产,技术人员集成了许多自主创新的工艺、材料、方法。美国《航空航天周刊》将运十列为中国与国际航空技术接轨的唯一工程,评价运十“将中国民用飞机设计水平推进了15年”。 然而这一集全国航空力量技术攻关十余年的成果,最终却付诸东流,生产线被拆掉,样机和设备被销毁,工艺和技术被尘封。北大教授路风,在2004年撰写的《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写道: “运-10下马最大的遗憾,是摧毁了整个中国民用大飞机的产品开发平台”。 他将运十的下马比喻为“自废武功”,产品开发平台的丧失,导致中国民用航空技术与美国、欧洲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20年后,当中国重新酝酿开发大型民机时,猛然发现横在眼前的,是一个更高的门槛,以及我们已经退化萎缩的技术能力。 在一切为了经济建设的80年代,停下来的不只运-10,还有核潜艇09项目、东风-22洲际导弹等等。比如1988年,我国核潜艇成功完成深潜和导弹发射最后两个试验,时任总设计师黄旭华形容自己当时一喜一忧: “我高兴是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 随着运十项目下马而荒废的运十设计团队,正是不幸有此遭遇。程不时回忆,部分设计人员实在找不到事干,被派去设计上海的交通手册,编完之后还要去做销售工作。 更糟心的是,另一边,与麦道的合资也远不如人意。 开始的MD82飞机仅仅是在中国组装,无论上游的设计还是下游的零部件生产,都掌握在美方手中。这样的合作,一没有培养能力,二没有掌握技术,实质上使得中国飞机制造厂沦为麦道的组装基地。 此后的MD90飞机生产,中方要求国产化率达到70%,上航、西飞、沈飞、成飞等中国航空工业的中坚力量悉数参与其中,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这段历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航空工业水平,一些企业承接波音、空客的部件转包生产,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在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方面,国外厂商是绝不肯丝毫让步的。如果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中国大飞机的发展,将与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如出一辙——获得一定的本地化生产能力,但培育不起自主品牌,市场被西方巨头瓜分。 在大飞机领域,合资的最终结果甚至连汽车行业都不如。1997年麦道公司因经营不善被波音兼并,波音要求立即停止麦道与中国的合作生产,生产线拆除,资料销毁,这一被寄予厚望的合作项目戛然而止。 运十终结后的这十年,就这样再一次竹篮打水一场空。再之后,中国航空业还曾将目光投向空客,试图合作开发AE100飞机,但兜来转去,最终在巨额技术转让费前不了了之。 这一连串的失败,对中国民用航空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八九十年代,航空人的日子很不好过。原上海飞机制造厂厂长刘乾酉回忆,麦道飞机停产后,由于长期没有项目,几千人面临下岗,人才大量流失,上飞很多技术骨干流失到了国外。 运十团队的部分人,后来幸运地参与到ARJ21飞机项目中。ARJ21飞机是70-90座的支线客机,2002年9月立项研制,2008年首飞。虽然不是大型干线飞机,但设计上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航审定上,完全与国际标准接轨,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一直参与其中。 528个试飞科目,398个适航条款,一个一个地完成,最终才在2014年获得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所有这些,此前在我国的航空领域一片空白,因此ARJ21对民航工业贡献巨大。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而是一个国家的试飞。 ARJ21设计团队的骨干,大都之前参与运十项目,总设计师吴兴世、副总设计师周济生、机气动设计师赵国强,他们都曾在一条战壕中并肩作战。虽然运十折翼,但ARJ21的成功,或许多多少少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慰藉。 遗憾的是,运十的总设计师马凤山,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幕。 马凤山与运十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马凤山积劳成疾,1984年不再担任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所长等职务。麦道项目展开时,他一再强调,自主研制这条线不应丢弃,但最终无法挽回局面。1990年4月24日,年仅61岁的马凤山离世,骨灰安葬在徐汇龙华公墓。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至此,中国第一代航空人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已将近尾声,但中国大飞机的故事,仍然道阻且长。 五、雄关漫道 2012年7月,《财新·新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高铁国产化幻觉:2万亿市场换来按图制造能力》的“神文”,直指中国高铁“国产化率虚高”的问题,并认为中国高铁出口困难,成为巨大的债务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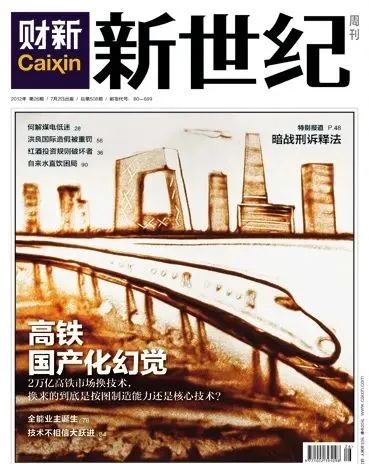 今天回头去看,中国高铁已是大国工程的典范,但实际上发展历程并非全是坦途。高铁的立项是在2000年前后,2008年开始大规模运行,但直到2018年前后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这个过程整整花了18年。 对于国产大飞机来说,尽管过去三十多年的曲折探索难言成功,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作为现代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大飞机是考验国家意志和战略眼光的超级工程,无论是计划体制下忽视市场竞争,还是迷信于“外部合作”,稍有不慎,便会满盘皆输。 如何最有效地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产业升级,高铁已经做了一个最佳示范。大飞机的研制周期和难度要远远高于高铁,对耐力和意志的考验也更严峻——当然,如果跨过坎坷,最终的回报也将丰厚无比。 根据中国商飞发布的市场预测年报,从2021年到2040年,全球将会交付4万余架喷气式客机,总价值超过5.9万亿美元,仅中国市场就会有超过9000架飞机交付。如果我们不能参与其中,那么这场饕餮盛宴的绝大部分,都会被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公司瓜分。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飞机拉动的,其实是整个国家经济。 在美国,航空业贡献了2.3%的GDP和超过400万个工作岗位。日本通产省也曾对500项技术扩散案例做了研究,发现60%的技术来源于航空工业。从投入产出效益来看,每向航空工业投入一万美元,10年后可以产生50-80万美元的收益,对经济的拉动远远超过家电、汽车等产业。 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绝不能没有自己的大飞机产业。 2003年,政府换届,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给国务院写信,提出重新启动研制国产大飞机的建议。2008年5月,中国商飞在上海揭牌成立,被命名为C919的大飞机项目蓄势待发。 
C919组装车间
对C919,网上经常被拎出来争论的一个问题是:
“国产化率只有60%的C919究竟算不算国产大飞机?我们是否只是造了个壳子?” 这个疑问是有来由的。 C919的研制,中国商飞采取的是“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系统集成由国内自主设计,机体部件(机头、机身、机翼等)由国内供应商承制,航电、飞控、燃油等选择与国外供应商联合攻关,为此成立了16家合资公司。至于最关键的发动机,自研的长江1000A尚有待时日,C919目前使用的是美国通用和法国赛峰合资生产的LEAP-X1C发动机。 
C919供应链分布
一辆汽车大概由两三万个零件组成,而像C919这样的大型客机,细分结构繁杂,零部件数量超过100万个。C919的研制,以上海为龙头,全国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近20万人参与项目研制和生产——这不仅仅是一架飞机,更是一条蕴藏巨大潜力的产业链。 上世纪70年代,波音开始将碳纤维材料应用到飞机上,日本东丽公司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打入波音供应链。波音为降低成本,也乐于扶持日本企业,东丽长期派遣数百名技术人员在波音协同技术攻关。如今,东丽已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碳纤维巨头。 这种“主制造商-供应商”的模式,其实也是其他飞机制造商采取的主流方式,波音、空客这两大寡头也不例外,像波音787项目,转包生产的零部件大约占65%;空客的4000多家供应商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其中在中国就有100多家。 即便拿所谓“造壳子”——也就是机体设计为例,技术难度并不比航电等内部系统低。 在这个领域,“减重”是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全世界的飞机设计师们都清楚,对一架飞机来说,“一克重量比一克黄金更珍贵”。有人测算过,飞机上每少装一瓶可乐,一天就能节省1000美元;一架客机如果可以减重300公斤,每年就能给航空公司带来1000万美元的净收益。 而飞机的重量,又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机身材料,二是机身设计,这背后,是材料、冶金、工程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动力学等等无数学科专业的集成——换言之,C919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不如说是一次对中国工业全方位提升的机遇。 运十下马时失散的人才队伍,也再次成长起来。电视直播C919下线时,曾有网民评论,很高兴看到飞机旁边的工程师很年轻。这支团队主要来自北航、南航、西工大等高校,担纲的技术管理者们大多三四十岁,他们还要打几十年的持久战。 当时网上有一张照片,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已年过八旬的程不时在人群中翘首以望,当年意气风发的他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运十下线时已白发苍苍的程不时
六、长沟流月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特意拜访了波音公司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记者问他:“这个家庭怎么样,幸福不幸福?” 领导说话自然要比普通人有水平,他引用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90年代的波音,无疑是中国市场上“最幸福”的飞机制造商,仅1990年,中国与波音签订的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订单,总价值就达90亿美元。波音的一位华裔工程师曾颇为得意地对同事开玩笑道:波音737部门有1/4员工的工资,都是中国发的。 那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时代,也是国产大飞机彷徨失措的岁月。 回首世界航空历史,民用飞机的发展路上躺着累累残骸:麦道公司连年巨亏,最终波音兼并;制造出F-22、C-130等著名军机的洛克希德公司,在民航客机领域一败涂地;加拿大庞巴迪,在进军大型民机时遭到波音空客联合绞杀,最终黯然退出…… 中国商飞志在跟空客、波音抗衡,但长路漫漫,谁也无法轻言胜利,好在谁也不会忘记过去的运十,以及镌刻在大场基地石碑上的四个字:“永不放弃”。 
2015年,运十旁屹立起“永不放弃”的石碑雕塑。
C919首飞那天,当年运-10飞机的副总设计师、已经87岁高龄的程不时特意带来了一把年轻时用过的小提琴,在首飞现场演奏了一曲《我爱你中国》。而72岁的吴兴世忆起运十往事,只简单地说了句: “这辈子能够有幸,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当年运十失利,团队解散,马凤山积劳成疾郁郁而终,生前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也没有能够看到中国大飞机真正起飞的一天。C919首飞的一刻,已是暮年的吴兴世想必再次回忆起三十年前,与马凤山等先行者并肩奋战的岁月。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 历史在变迁,事物在前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从起于微末难越关山,到如今步步为营逐渐壮大,历史的宏大叙事背后,是一代代实业报国的赤子之心,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