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黑一雄堪称异数。不同于“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中的其他两位:萨尔曼·拉什迪和V.S.奈保尔,尽管有着日本和英国的双重文化背景,他却是极少数不专以移民或国族认同为小说主题的亚裔作家。即使读者和评论家试图从他的小说中找寻出日本文化的神髓,或梳理出后殖民理论的印迹,石黑一雄本人却总是有意无意隐去作为亚裔的族群认同,而更以身为国际主义作家自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嘲“不知家在何处”,且无论在自我意识、还是在事实上因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八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读者的“无国界”作家,他的创作看似无关家国、故土情怀,却始终弥漫着感伤的回忆。或许在他看来,回忆,也只有回忆,才能让小说文本自由出入于欧亚文明之间,在这个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现代世界中,激起人们的普遍共鸣。 纵然石黑一雄作品的题材何其丰富多彩,其实都埋藏了一条共同的主线,那便是:帝国、阶级、回忆,以及童真的失落。而回忆更是他最偏爱采用的叙事方式,出版于近年的长篇《千万别丢下我》(2005)也不例外。透过克隆人卡西的回忆,小说缓缓展开她住在海尔森学校的童年岁月,那是一个不复重现的世界,唯有留存在卡西的回忆之中。经由回忆,卡西不但是在重新确认自我,认识他人,经历启蒙,同时也在缝合起生命中不经意散落的时时刻刻。 显然,石黑一雄无意与科幻小说作家并置。在小说中,没有关于人类与克隆人可能爆发的冲突等在科幻小说中习见的情节,人类的世界也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石黑一雄着力凸显的是,在不可违逆的既定命运下克隆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的尊严与责任、希望与挣扎。而且,他也没有把克隆人作为他者,而是作为人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小说写的是克隆人的心灵世界,却是以人类置身其间的缺陷重重的世界为背景,写尽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以及人对存在与命运的超越。在小说的结尾,卡西与她的“同伴”汤米终于重拾爱的勇气,即使爱的到来,为时已晚,但它不是一时的肉体激情,它是灵魂上永恒的平和与宁静,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带走的回忆。 在获1989年度布克奖的长篇《长日留痕》中,回忆得到了异样的呈现。 整个故事从表层上看是一次旅行,它同时也是历经世事的男管家史蒂文斯进入自己过去生活深处的旅程。史蒂文斯服务于达林顿府三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尽力使自己成为男管家中的杰出人物,追求这一阶层所特有的“尊严”,与此同时,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不得不冷漠地处理父子亲情,盲目忠实于其主人达林顿却无视后者一度与纳粹交往甚密、甚至帮助极右势力的现实。这种盲目也使他甚至失去了与心爱的女管家肯顿小姐的情感。 出于史蒂文斯特殊的经历,在讲述自己的感受与想法时,会不可避免地替自我辩解。此时,作者讥诮的声音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如此,史蒂文斯正儿八经地说着自己的陈年旧事,作者的“伴奏”却使得他的“正儿八经”失去了应有的效应,从而回忆在严肃中不经意间透出了幽默的基调。同样,史蒂文斯尽管因为过于坚守“职责”而错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从“职责”里找到了“尊严”。这当然令人怀疑,但他的寻求依然有其庄重之处,其中隐藏着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的悲剧。 事实上,这种悲剧的虚无感,在石黑一雄的作品中一以贯之。他的处女作《远山淡影》(1982)讲述了二战后长崎一对饱受磨难的母女的故事。她们渴望安定与新生,却始终走不出战乱带来的阴影,最终以母亲成功移民,而女儿自尽作为悲情结局。此后获惠特布莱德文学奖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的《浮世画家》(1986)生动展现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浮世画家的回忆与思考。直到二战日本的战败,他才恍若大梦初醒: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他的艺术理想也真如其名称一样毫无根基,虚浮于世。 在石黑一雄看来,因为大多数人始终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来知人论世,因此常受到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我们误以为自己在坚守职责,到头来却常会发现自己站错了位置。此时人生已然耗尽。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因为我们受挫却依然寻找理由让自己感受某种乐观因素。也因为此,石黑一雄认为,人类在真正的绝境中挖掘希望的能力既非常悲怆又相当崇高。“我是说,人们在困境中寻求勇气是何等的令人惊奇。问题只是,生命消逝得太快。” 同样是回溯性叙事,出版于2000年的《上海孤儿》无疑更能凸显石黑一雄宽阔的写作视野。小说的背景为1937年被日军包围中的上海。当时整个世界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主人公班克斯幼年在上海生活,后因父母失踪而回到英国,如今已成为英国上流社会有名的侦探,但他心中一直存着关于父母下落的谜。为了解开这一心结,他重新回到上海,在今日的战火与昨日的回忆中展开了调查…… 对于石黑一雄而言,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创作“国际化小说”,即适合各国读者阅读的小说的意图。在小说里,他的笔触在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首都伦敦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之间来回穿梭,同时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置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外国租界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展现东西方的相遇与碰撞,以及不同种族的人生百态。 这种跨文化的视野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石黑一雄特殊的文化背景和血缘出身。1954年,他出生于日本的长崎,五岁时跟随父母亲迁居到英国。他的父亲是一名海洋学家,受雇于英国北海石油公司,因此,他得以成为居住在英国乡下郊区的亚洲孩子,并且逐渐地和周围的白人文化融合。中学毕业后,石黑一雄先后就学于英国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1980年,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居住在伦敦郊区,开始潜心写作。 “国际化小说”的创作实践,难免招来追逐全球化的“时尚”的质疑。对此,石黑一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日益变得国际化,作家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全球的读者。只有把目光投向国外,面向全球,不只是拘泥于本土,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更触动心弦,颤动全人类的心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黑一雄认为,尽力突破地域疆界,写出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才是一个作家应该矢志努力的方向。“如果小说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进入到下一个世纪,那是因为作家们已经成功地把它塑造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国际化文学载体。我的雄心壮志就是要为它作出贡献。” 2015年3月,蛰居许久的石黑一雄推出最新作品《被掩埋的巨人》,其创作过程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但与许多颇受期待的文学新作不同,这不是一部壮丽的史诗,会讲述跨越一个世纪的烽火连天;也不是一篇对他个人经历的精心拼合与再叙述。对这则娓娓道来却感人至深的故事,作者自己给出的判定是“寓言式的”。 《被掩埋的巨人》故事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亚瑟王时代的不列颠,那是一段我们知之甚少的历史时期。小说讲述一对年迈的夫妻希望寻回他们失落记忆的经历,与此同时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却似乎全都染上了一种群体性的失忆症。 男女主人公艾可索和比特丽丝获准离开他们生活的村落,踏上了路途,一路上先后遇到了一群嗜血的精灵:一头曾经凶残无比、如今年老体衰的巨龙;一位充满激情、胸怀复仇烈火的武士;还有一名倔强的船夫,将旅人们渡往伊甸园般的神奇乐土。很快,他们从垂垂老矣的高文爵士(就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中的那位高文)口中得知,巨龙那附了魔的吐息就是这记忆迷乱的源头。 节选 海湾上的日落。背后的沉默。我敢回到他们那儿吗? “告诉我,公主,”我听见他说。“这迷雾消退了,你高兴吗?” “也许这件事会给这块土地带来可怕的后果。但对我们来说,消退得正是时候。” “我一直在想啊,公主。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更加牢固?也许有了迷雾,旧伤才得以愈合。” “现在这有什么关系呢,埃克索?和船夫握手言和吧,让他把我们渡过去。既然他先送一个,然后送另一个,为什么要和他吵呢?埃克索,你说呢?” “好吧,公主。我按你说的做。” “那就离开我,回到岸上去吧。” “我会照办的,公主。” “那你还耽搁什么呢,丈夫?你以为船夫就不会不耐烦吗?” “好吧,公主。不过,让我再抱你一次吧。” 他们在拥抱吗,即使我把她裹得像个婴儿一样?即使他必须跪下来,在坚硬的船板上把身体扭曲成奇怪的形状?我想他们真的拥抱了,只要他们没开口说话,我就不敢转身。我怀里抱着桨,轻轻摇晃的水里,有船桨投下的影子吗?还需要多久?最后,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到岛上再继续谈吧,公主,”他说。 “我们就到岛上谈,埃克索。迷雾一散,我们要说的话会很多。船夫还站在水里吗?” “是的,公主。我现在就去,和他握手言和。” “那就再见啦,埃克索。” “再见啦,我唯一的挚爱。” 我听见他涉水过来。他打算跟我说句话吗?刚才他说要握手言和。可是,我转过脸,他却没有朝我这边看,只是望着陆地,还有海滩上的落日。我也没有去看他的眼睛。他从我旁边经过,没有回头看。在海滩上等着我吧,朋友,我低声说,但他没听见,继续涉水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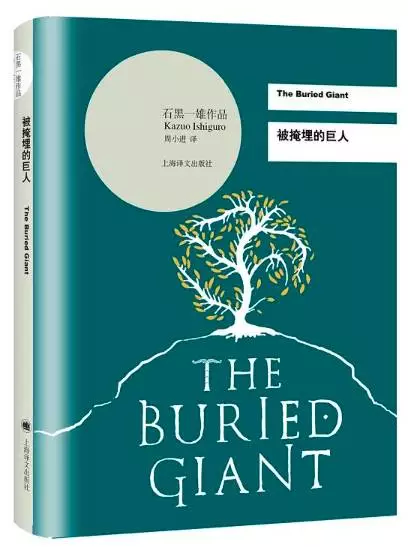 [英]石黑一雄/著 周小进/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1月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