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理群先生在2015年出版了《丰富的痛苦》一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也是钱先生自己最为看重的著作。承蒙钱先生题赠一册,笔者深感荣幸。钱先生这部私下里有着“偏爱”的作品,旁征博引、倾注深情、鞭辟入理,注入了宝贵的心血,可以说是一部呈现心路历程的美丽而带着“痛苦”的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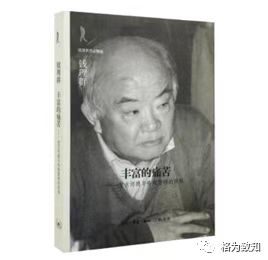 
一,《堂吉诃德》与《哈姆 雷特》
这是《丰富的痛苦》一书的副标题。按照作者自己的介绍,这本书的任务“仅在于描述:描述两个文学幽灵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走到东方的故事;描述东、西方各国作家怎样出于对人类(首先是知识分子)某些重大精神命题的共同关怀,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以及个人精神气质的特点,… 共同创造了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的故事。”而最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将是我们考察与描述的重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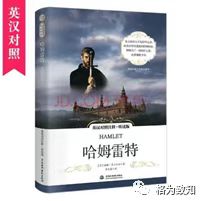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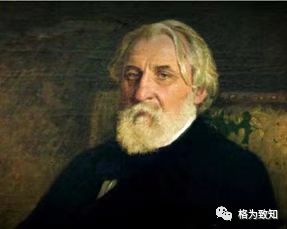 当然,这两位不朽的文学幽灵,指的就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经过了几个世纪,在远离这两个人物诞生的西班牙和英格兰的中国大地上,他们的形象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的典型性格和独特精神,仍然在芸芸众生中依稀可见,更在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伟大文学作品之所以永垂不朽,就是因为“人们可以超越暂时性的审美、理念观念与风俗习惯,排除一切时代功利的干扰,从历史与审美本质上去把握其超越时空的客观本来面目和永恒的价值。”钱先生这段话,把经典文学巨著的永恒价值阐释得淋漓尽致。 经典的文学巨著,既反映了社会和时代,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和推动时代。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钱理群先生所要着力探索的,正是这两部伟大著作和这两个鲜活人物,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潜移默化的深刻作用。他为我们指明了中国知识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鲁迅和瞿秋白,并从而诠释了20世纪初以来,众多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向西方寻求真理、乃至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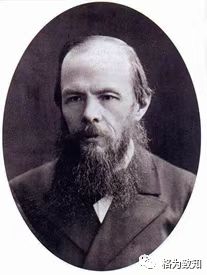 及至这两部著作和这两个人物传到中国,更出现了原著者或许未曾料到的后果:他们启发和激励了一大批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促成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他们心目中的革命道路。这将在下面第三节中讨论,也正是钱先生此书着力探究的重点。 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精神象征 在粗浅了解的层次,一般会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位自不量力的骑士,或者与虚幻的对手搏斗的偏执者。但是随着这位骑士形象的东移,他变得越来越高大。英国19世纪的批评家海兹利∙赫士列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的是一种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著名英国诗人拜伦在他的巨著《唐璜》中,高度赞扬了堂吉诃德“永远追求正确的东西”,“单枪匹马挡住结成一伙的强者”,由衷地赞叹:“使他疯狂的竟是他的德行”,这是“一切故事中最惨痛的故事。”拜伦以诗人的深刻,揭示了《堂吉诃德》史诗般的伟大和高尚,以及它同样史诗般的悲剧色彩。 富有思辨精神的德国人对堂吉诃德则另有一番更具哲学意味的评价。大哲学家黑格尔以辩证法的逻辑,深刻揭示了《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喜剧性的矛盾”:“一个凭知解力安排得很有秩序的世界和一个与它脱节的孤立的心灵之间喜剧性的矛盾。”堂吉诃德的内在矛盾在于,塞万提斯“把他的英雄描绘为具有本来就很高兴的许多方面精神资禀都很好的人”,“但在他身上骑士风变成了疯狂”。堂吉诃德的性格魅力正在于“对自己的行动的内容和结果…不用思考的震惊态度”,以及不计后果的人生态度,而黑格尔认为,这是“伟大的,天才的,和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品质是相得益彰的。”钱先生认为,到黑格尔这里,“人们已经开始以一种比较复杂的眼光与态度去看待这位西班牙骑士,从内在矛盾中去把握这一形象,这自然是显示了一种成熟的。” 在德国,是诗人海涅第一次把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连在一起。他说:“在幽默讽刺的伪装下,(堂吉诃德的)正直诚实显得最为动人心弦。这又使我想起那位奇怪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世界上最诚实不欺的人。他装疯只是为了取得一个疯癫的外表而已。”诗人海涅其实是一位颇为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思考集中在他那个时代德国所提出的的两个基本命题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和相关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他对风靡于德国的精神至上的唯心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指出,对绝对精神的崇拜,竟成了德国根深蒂固的国民性。这样他以一种独特的新眼光来看待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他的仆人桑哥∙潘查:“莫非他想用寓意的手法,让堂吉诃德体现我们的精神,让桑哥∙潘查体现我们的肉身?”然后他发现,仆人“始终比那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主人明晓事理。”并由此得出结论:“肉体有时候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然而在现实世界,精神有时会主宰世事,钱先生如此总结:“作为理想与热情化身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堂吉诃德),对于广大群众的精神控制力量,在政治和宗教的革命中是显得特别突出的,这是一再为各时代、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所证实来的事实。”如今读这段话,历史和现实的镜头匆匆闪过,似有一丝凉意。 再往东移,就到了广袤的俄罗斯大地。在那里,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借鉴西欧杰出作家的先驱者。他提醒果戈里注意借鉴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创作经验,而别林斯基则明确地指出:“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别林斯基作为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评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都是近代新艺术的奠基者:“在16世纪,完成了艺术方面最后的改革:塞万提斯用无与伦比的《堂吉诃德》击败了诗歌的虚伪理论倾向,莎士比亚则使得诗歌与现实生活永远调和、结合了起来。”在别林斯基心目中,莎士比亚更是与荷马、普希金一样神的存在。他对哈姆雷特的认知,远远超越了他的同时代人。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世界既是“异乎寻常的崇高伟美”,又是“朴素、平凡和自然的。”这应该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哈姆雷特》正是“戏剧之王的灿烂王冠上的一颗最光辉的钻石。”他认为,“哈姆雷特!… 它伟大而又深刻:这是人生,也是人,这是你,也是我,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那崇高或是可笑,但总是可悯又可悲的意义上… ”。钱先生认为,“这不仅是别林斯基个人与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哈姆雷特的认同,更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与莎士比亚以及他的哈姆雷特的英国文化的认同:这博大、深刻、真实、朴素的诗之精灵是不能不使人想起俄罗斯母亲广袤无际的大地之魂的。”同时别林斯基更特别指出,俄罗斯和德国在精神的基础、本质和实体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他对哈姆雷特的探讨,就以德国伟大诗人和学者歌德的经典评论为基础。他认为歌德提出的“认识责任后的软弱”的概念,“包含着整个剧本的基本思想”,是“天才理解了天才”。他沿着歌德的思路,把哈姆雷特概括为“有着伟大的思想却只有幼童似的意志的人”。然而他比歌德进了一步,指出哈姆雷特最终还是“从斗争中解脱了出来,就是说,他战胜了意志的软弱。因此,意志的软弱并不是基本的概念,却只是另一个更普遍、更深刻的概念的表现 ─这就是分裂的概念,分裂是怀疑的结果。”其实在别林斯基的眼中,哈姆雷特具有美丽而伟大的灵魂,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力的,因为 “一个人的精神越崇高,他的分裂就越是可怕。他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胜利也就越是辉煌,他的幸福也就越是深刻和神圣。这便是哈姆雷特的软弱的意义。” 而在文学实践中,俄罗斯伟大作家屠格涅夫以极具世界性的眼光,发表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里程碑式的演说,成为继海涅之后又一位阐释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大师。屠格涅夫认为这两部伟大诗篇具有“永恒的生命”,对于这两个“真正无穷无尽的典型的研究”也将是永无止境的。屠格涅夫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他敏锐地意识到“《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同时出现是值得注意的。”并且精辟地揭示“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极。”他第一次从人类天性对立两极中,揭示了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两个文学典型的内在精神联系。这无疑是对这两部文学巨著和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最高层次的洞察,也提出了关于文学的社会价值的普遍诠释。屠格涅夫在做这种探讨的同时,开展了自己丰富的文学创作,其中也自然贯穿了他对二元化人性的认识,凝结了他从两位先贤收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趣味。《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等脍炙人口的明珠,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笔下的罗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堂吉诃德精神,而不是哈姆雷特气质。罗亭在自我感觉里是与堂吉诃德相通的,但是也有十足的哈姆雷特气:上半身是堂吉诃德,下半身是哈姆雷特,因此是典型的二元化性格。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齐名的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家公认,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同属欧洲文学中复调萌芽接近成熟的那一发展趋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一发展趋向的完成者”,他们之间有着深刻的文学与精神联系。在他极具影响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堂吉诃德》:“世界上再没有比这部小说更深刻有力的了”。当他在著名的小说《白痴》中试图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堂吉诃德。因为在他看来,“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堂吉诃德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他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时又滑稽可笑。… 对被嘲弄的和非常可贵的美产生了同情,因此引起读者的好感,激起同情,这是幽默的奥秘。”钱先生总结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梅斯金公爵(《白痴》的主人公 ─ 引者注)将塞万提斯所创造的西班牙骑士的堂吉诃德精神发挥到了极端,从而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内在的形而上意义,或者说,升华到了一个宗教的高度。” 俄罗斯另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赫尔岑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极高评价,或许可以作为本节的小结。他说:“塞万提斯用辛辣的讽刺向世界宣告骑士的软弱和不合时宜,”而莎士比亚则“结束了艺术浪漫主义时代,开辟了新时代”,他认为哈姆雷特可以看作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典型”,“哈姆雷特的性格达到了全人类普遍性的程度,尤其在这怀疑与沉思的时代”。在俄罗斯文学的土壤里扎下根的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以及他们所塑造的两个伟大生动的形象 ─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那里得到了充分而公允的理解和阐释。 三,中国知识界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精神 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个幽灵,直接或经过一些中介,特别是俄罗斯的诠释,继续向东方漫游,在中华大地上也深深扎根。写到这里,钱先生的大作也进入了下编: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在中国(20世纪:20-40年代)。这其实是本书的重头戏,也是钱先生的匠心发掘。 1, 鲁迅与周作人 首先将哈姆雷特介绍到中国的是1895年严复先生所译《天演论》的导言。1903年上海出版《澥外奇谭》,包括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次年林纾和魏易将《莎士比亚故事集》译为中文,其中哈姆雷特的故事译为《鬼诏》。真正被《堂吉诃德》深深感动的,则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于1908年在日本读到这部巨著的德文本。而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真正做出科学评价的,是出版于1918年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这样评述这两本书:“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即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 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 然古之英雄,先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堂吉诃德也,此可长思者也。” “至《哈姆雷特》等作,则不涉宿命说,而以人性的弱点为主。”这些见解,在那个时代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到1922年,周作人又专文介绍这两部书,并引述了屠格涅夫的著名阐释 ─“这两大名著的人物足以包举永久的二元的人间性,为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堂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哈姆雷特代表怀疑与分析”,同时,“这两种性格虽是相反,但正因为他们在那里互相撑拒,文化才有进步。”另一方面,堂吉诃德与他的仆人又分别是理想和经验的化身。这些见解,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显然融入了对五四运动和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反省与反思。那个时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与堂吉诃德有一种共同的对乌托邦理想国的追求,因此很容易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于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乌托邦之梦是个很好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这样描述他们的梦想:在中国“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平等”。而与此同时,还有被鲁迅称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的“个人主义”,即经济上平等,思想上自由。 这种二元的诉求,其实是存在天然的矛盾的。鲁迅认为,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的要求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也是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村”运动,就是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周作人正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新村的设想,包括悠哉游哉的规律的生活,完善的公共设施,供给制分配,等等,似乎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耕读生活的进化,与儒家的大同思想有一脉相承之色彩,完全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其问题则正如胡适所批评的,与现代社会的“分工进化的道理相悖。”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问题是如何看待在经济自在的生活中的思想自由,以及如何实现理想国的途径。即使像罗素这样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宣称“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于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流血革命”。这些主张,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周作人则认为共产主义是宗教的虚幻,他虽然尊敬为共产主义殉道的英雄,如李大钊,但却坚定地认为,这毕竟是一种非理性的迷乱,是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所不取的。周作人更安于舒适的现实生活,“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许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这种观念,或许就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反之,对周作人积极鼓吹“新村”运动持怀疑态度的,正是他的长兄鲁迅。鲁迅冷静而务实,“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将黄金世界的理想预约给人们,而是要找到变革现实、创造未来的道路。”对所谓的“黄金世界”,鲁迅也提出质疑。鲁迅的质疑深刻而彻底,他追问:在黄金世界里“还有没有黑暗?”他的哲学是“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这显然是辩证法的哲学,也与毛泽东斗争绝对性的观点相符。同时鲁迅又是非常求实的,或者用哲学的语言来说,非常唯物的。他总要努力划清对彼岸的梦幻世界的理想追求,与此岸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这其实也正是抓住了堂吉诃德精神的要害。鲁迅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部排斥”。他痛恨中国社会的瞒与骗,为此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现代中国文学的不朽典型。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阿Q与堂吉诃德精神上的相通,尤其是后者的消极一面,即把想象、主观愿望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所产生的精神迷乱。但是阿Q的奴性,却是堂吉诃德所绝对没有的,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剧,也是鲁迅特别痛心之处。鲁迅的深沉与堂吉诃德的浮躁形成鲜明对照。鲁迅的精神结构要远为复杂,思想也要阴沉许多,这种精神气质其实更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了。哈姆雷特具有强烈的怀疑色彩,包括对于他自身的怀疑与否定,如屠格涅夫所说:“他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这是哈姆雷特精神、气质的一个本质方面。鲁迅在他的《野草》里,有着非常类似的感觉,他以“影”的名义自白:“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而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听起来,这真像是哈姆雷特的中国化身的独白,而且把哈姆雷特的自我怀疑的命题发挥到了极致。但与哈姆雷特不同的是,“越是清醒于绝望,他越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越是反激出他的更大更强的行动的意志力。”即便对于死亡,他也转化为对生命形态和意义的思考,从而写出这段震撼人灵魂的名言:“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1, 瞿秋白 瞿秋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深深的印记,他的人格魅力也感动了无数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后人。按钱先生的描述,瞿秋白“对于人的精致的精神生活以及生活与精神的自由无羁,有着几乎是本能的向往。”这当然是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所决定的。上述“新村”运动自然会令他神往,但他很早就对这个运动提出质疑,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中国第一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佼佼者。这首先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终极理想的吸引,而不是钻研马克思理论的结果。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信仰与本性的矛盾,时时陷入“二元论的人格”。这自然让我们又想到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他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从俄罗斯文学中典型的 “多余的人”,酝酿出他最后的“多余的话”。他觉得无论做教授,还是政治家,都不是他的本色,都有点像“戏子”的表演。而他内心深处呼喊的是“回‘家’去吧。”这也像堂吉诃德最后的忏悔:“一生虚幻,临殁见真”。钱先生又指出:“在清醒地自省这一点上,瞿秋白其实是更接近哈姆雷特的。”他的贵族气质和内心冲突,确实像20世纪中国的哈姆雷特。他的历史悲剧,也正如歌德对哈姆雷特的概括“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些精准的写照,多么贴切地描绘了瞿秋白,真是一句“多余的话”都不需要了!然而直到今天,瞿秋白无比真诚的《多余的话》还在深深地感动着我;他的美好理想,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他对这个世界的依恋,都归结为这样美丽的文字: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2,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在中国的异化 1930年代挑战鲁迅和周作人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在革命的光环下,以堂吉诃德式的盲目与愚蠢而自命不凡。其实他们不仅根本不懂得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对西方的文学典型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精神实质也理解得很浅薄,从而造成了对这两位不朽人物的某种中国式的异化。鲁迅尖锐地指出:“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最后选择自杀的俄罗斯革命诗人叶赛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鲁迅看来,要求“完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备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这种清醒的认识,或许可以回答许多人的疑惑:如果鲁迅活到革命胜利以后,会如何?在这一点上,俄国革命胜利后执掌文化事业领导权的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可以作为借鉴。卢那察尔斯基在内心深处理解、欣赏并且向往堂吉诃德超时空的博爱、仁慈的理想原则,但同时对革命暴力的思路与实践又是充分理解的。所以在他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最终的命运是被革命抛弃、继续漂泊去做永远的精神追求。鲁迅对这种人物安排有所保留,他站在社会变革者的立场来评价堂吉诃德,尊崇堂吉诃德“因感到现实的不平而热烈地追求理想的精神。或许我们可以设想,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的命运未必相同。 而在那一时代中国的文学家们,把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灵魂化解到中国文人的形象中,如文学评论家赵园女士所概括的:注入了“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贬抑,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剥夺,这显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忍从传统有关。”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究竟会不会产生真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精神呢?鲁迅、瞿秋白于1932年和1933年先后撰写了《中华民国的“堂吉诃德”们》与《真假堂吉诃德》两篇杂文,反复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都必然表现为一种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彻底精神,而在中国这样的有着中庸传统的东方国家里,却必然将其钝化、调和化,从而失去了自身。即所谓“异化”也。 4, 旧中国最后一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抗日战争的烽火,激发了无数国人慷慨以赴的豪情壮志,堂吉诃德成为一种奋不顾身的象征和榜样。于是在这个东方大国,竟然出现了堂吉诃德全民化,至少是全知识界化的奇迹。反之,哈姆雷特却因其软弱和犹疑,成为被讽刺的典型,并且引起对中国国民性过于忍隐以至于丧失勇气和机会的特点进行的反思。但是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个体的堂吉诃德式的奋斗,完全没有胜利的机会。经过痛苦的探索,一些知识分子终于在革命圣地延安,在群体的昂扬中,看到了希望。如钱先生所描述的,“这是个体向群体的归依”,是从“诚实的个人主义”走向战斗的集体主义。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又丢失了自我个性与怀疑主义,只渴望得到历史的主体─工农兵及其领袖的认可,而远离了哈姆雷特的精神。本性的知识分子气,或哈姆雷特气,与理性的追求,产生剧烈的矛盾,这可能是所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挣扎的炼狱。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同样经历战争的洗礼,内心也同样充满矛盾,即如吴宓先生的“二马之喻”:“言今日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愿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吴宓和他的同道者,显然更寄情于后一道,从而成为为中国传统文化卫道的骑士,在内在精神上逼近塞万提斯笔下的西班牙骑士。 当历史走进另一个关口,新中国的桅杆在远方地表上依稀可见的时候,中国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又在面临新的抉择。被称为胡风派的七月派诗人近乎狂热地迎接新世界,鞭挞“骄傲与颓废”和“虚无主义”的“可怜的知识分子”。他们鼓吹摈弃哈姆雷特气,追求堂吉诃德式的单纯的、英雄的生命。但他们同时强调自身的独立思考。钱先生指出,“正是对自我的战斗的个性充分肯定与执着,使七月派诗人实际上与高度统一和绝对服从的时代要求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不协调,这同样是预示着、决定着他们以后的命运的。”可以说,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气,酿成了他们以后的悲剧。另一派以穆旦为代表的诗人,则具有浓重的哈姆雷特气质。他们对未来心存忧虑和恐惧,敏感地预见“那日益接近的未来,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希望, 更会给我们带来失望。”虽然他们准备皈依,但也知道,那皈依的后果“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认为:“哈姆雷特比堂吉诃德更勇敢,因为他敢触动人类的病痛。”钱先生则认为“现代哈姆雷特的全部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敢于正视并且拥有‘丰富的痛苦’”。 漫游到中国的两个幽灵,到1940年代末尾,被赋予不同的灵魂和使命,对未来也做出截然相反的预言。从那时起,七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实践对这些预言也给出了答案。在新的时代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精神还会在神州大地上徜徉,还能为我们诠释许多行为逻辑、思想主张和世事走向。 四,为什么是“丰富的痛苦”? 这部著作的着眼点,显然是人类精神发展史,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不仅限于中国、但核心是中国,而贯穿的精神链条则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人物。非常深刻与特别的是,这两个人物恰恰代表了人类精神中几个主要的矛盾对立面:勇敢与怯懦,理想与现实,盲目与怀疑,冲动与犹豫。他们之所以不朽,所以历遍全世界的漫游而经久不衰、永葆生命的活力,就是因为他们太典型,太具有代表性,而又太富于戏剧性了。 钱先生的这部著作,旨在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这样的研究和考察,会使人丰富,但也必然会体验痛苦,“智慧的痛苦”。因为“作为人类智慧的体现的知识分子,痛苦是其天然属性。”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这两位不朽人物自西方向东方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反映了“人类智慧发展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应的智慧的痛苦不断深化、丰富的历史。” 《丰富的痛苦》,适得其名也。 (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