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收到带着油墨清香的《陈染文学年谱》,时光仿佛被打开了一条回路,使我回望到自己四十年来走过的文学小径。那些写作生活中秉烛独行的夜晚,那些遮蔽了喧哗的角落,都在这份作家年谱中徐徐展开,鲜活起来。纸页间那些色彩纷呈、敏锐深挚的论述,多是我从未见闻的,让我重新凝视自己漫长的文学小路,让我忆起几件当初感到挫败,现在却倍感幸运的小事。这些岁月中的微末,本以为早已忘记,今天却在这份年谱里重逢。 记得当年,被视为先锋小说和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的《私人生活》首次出版之时,或许是有些超前,又或许是有些反传统,出版社的编辑怀揣“爱护”之心,对那些他们眼中“不合时宜”的文字尽数修剪,对“敏感内容”进行了“净化”。当初,我感觉那些被剪掉的段落,如同未及睁眼便夭折的婴孩,永远地消失在我当年那台笨重的286电脑硬盘中,化作历史尘埃,连一声啼哭都没有发出,我再也寻不见它们;那些红笔删减勾画的墨迹,如同判决书上一枚枚殷红的印章,雕刻在我年轻时候的心房。当初这些改动,确实带给我未完成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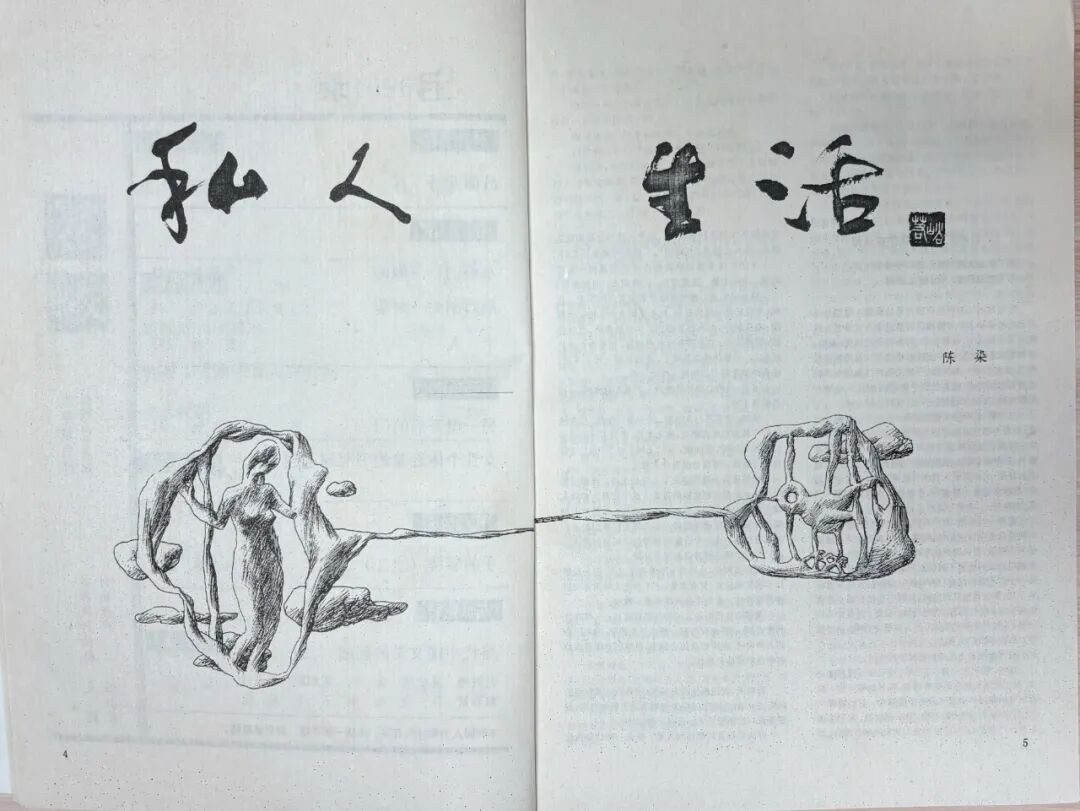 陈染《私人生活》首发于《花城》杂志1996年第2期 我当然知道,这个“过滤筛选机”,是这本书得以在市场上流通的定海神针,我必须在体系里完成这个流程。 然而今天,当我回望那段时光,那些殷红的红墨水如今已褪去光泽,只是淡淡地洇染在记忆中。时光也仿佛过滤了当初的不甘,没有了遗憾,甚至心生一种侥幸心理——正是那些适时的取舍,剪掉了“旁枝侧叶”,才使得存活下来的篇章获得更长久的生命。正是这种“爱护”,才让我的文字以“清朗”的姿态抵达众多读者,并安然栖落在他们的书柜里。 与此同时,那份最初的疼痛与束缚之感,竟成了意想不到的养分——它在无形中为我的文学小径撬开冻土、拆除藩篱,让光在这里跨过围栏,穿越我们不曾看到的暗物质,自由畅行。 值得回味的是,当这部被修剪过的作品参与当年的某文学大奖评选时,评委会在最后一轮评选中,终以敏锐的嗅觉,在字里行间读出一些残留的“异质”,最终未予通过。 记得当年一位老前辈指着我的书说:“现代主义推崇潜意识、荒诞化和碎片化,其核心是个人化、唯心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产物。我们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不是我们的文学路径。” 我当然非常懂得主流文学奖的导向性。 其实,我曾与老前辈在一幢大楼里进进出出十几年,他和蔼的样貌给我留下好印象。然而,我平素日常状态下的温婉与内敛,丝毫无法影响他对我思想的不认可。我感到无奈。其实,什么主义文艺观我并不关心,觉得只有从个体、底层,由下而上推演建构的理论,才是正常的逻辑;而以宏大空洞的概念框架往下推演建构的,多是反常识的。 在我当时看来,这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失落。而在今天,当我重新忆起那些个细节,反而深深感激这段插曲带来的沉淀。它如同一场春雨,恰逢其时扑灭了我潜滋暗长的浮躁,泯灭了我差点骄傲起来的膨胀。它如同一个警示,让我懂得文学创作需要如履薄冰的敬畏,需要敛气收息、和光同尘的低调,让我安静且诚实地回归到文学本身的小路上。 起初,我并不关心文学的各种“主义”,但从此之后我心里就照进了有关“主义”的多彩之光。 手中的这份年谱沙沙作响,像是翻开一段段时间,它牵引着我,让我忆起另一件早年的风波。 很多年前,我的一本插图版书籍,选用了中央工艺美院一位著名油画家的图案,其中含有身体不宜裸露的部位。结果此书刚一出版,油墨未干,字里行间似乎还残存着印刷机的余温,一位近水楼台的发行人员看到了书里的插图,她立刻警觉起来,并向上做了汇报。两天后批示下来,一声令下,刚刚发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近两万册图书,全部如数收回。然后,由出版部刻了一枚小鸟图案的印章,在那张插图的隐私处逐一盖上。 《私人生活》首发杂志的标题页 这事件给我带来很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其实,这位发行人员与我没有任何交集,更无恩怨,她只不过是在某种僵化中规训得久了,条件反射般地做出了反应。我那时没有辩解,因为深知有些沟通如同在迷雾中呼喊,有些申诉如同在说人家没有文化。 回首往事,不觉莞尔。记得那时的我曾经说:我的道路是一条绳索。这不免夸张。而今,我却由衷地想,这与其说是一场坎坷,毋宁说是别开新意的周折,让我学会在磕绊中风雨兼程。 这条小路虽然满是泥泞,却自成天地,有其葱茏的诗意;虽然没有遍地的红花、喧天的喝彩,却自有百花芬芳,有野草和昆虫们合唱。我在这条小路看似逼仄的石缝间,依然可以冒出一篇又一篇小说、一段又一段锦章。它们不去攀附通衢大道上的锦簇花团,却自有其幽微深沉的呼吸,自有别一种幽香。在这里,文学更像一枝本自具足的花朵,花开花落,开谢由己,它不被潮起潮落所役,不被月圆月缺所困,它不被条文规训,不受时空禁锢,再板结的硬土它也会破壳而出,探出头来。 这场荒诞剧,如同一面放大镜,照见了长久以来的草木皆兵的思维定式,它让我愈发沉入那条挣脱束缚的文学小径。 这条小路蜿蜒曲折,却也常常峰回路转,让我明白命运的波动并非总是困厄。 我至今记得有一阵时间,“自由化”问题风云乍起,单位里空降了一位作风硬朗的新领导。上任伊始,未及旬日,就开始调换兵马。某个傍晚,他忽然招我谈话,夕阳透过百叶窗斜射在他一侧的脸孔上。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你才华出众,你去追求你的那种‘自由’吧”。他继而告知,在他外出开会返回之前,希望我把档案取走。 我一时哑然失语,心里五味杂陈。走出办公室,已是暮色四合,我踏着黄昏中飘落的树叶,无奈地返回家中。 然而,世事难料,命运有时也开玩笑,他在南方开会期间不幸出了车祸,再也没有回来。对于生命的骤然消逝,唯有沉重和叹息。毕竟生命之重,比过任何可承受之轻。去职之事不了了之。 这次未完成的去职,却成了一个意外的转折点。我便这样留在了文学的深潭之中。这潭深水的表层,各项“指标”似乎都在安全的边界内,然而水面之下,那些思想的暗流与压力从未止息。我学着做一枚细微而柔韧的水滴,做一枚可忽略不计的水分子。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浅出”,在深浅之间寻找自己独特的“泳姿”,寻找自己的呼吸方式——所谓“深入浅出”,就是既能沉浸其中,又能保持抽离,做个深潭里的浅泳者。 我寻找着,磕绊着,一个猛子居然游了几十年,学会了以柔韧应对压力、以定力对抗盲从。直到有一天,我的小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抵达岸边。而靠岸处,正是这条小路的又一起点。 这一场有惊无险的“擦肩”,见证了生命的无常,也让我对那条小径所蕴含的独立不群,更加流连与眷恋。 不幸往往孕育着万幸,暗夜预示即将降临黎明。 人间的路往往就是这样:有些小路,本以为身至迷途,出口难觅,然而忽然就柳暗花明,出其不意抵达通路,如同惊喜绽开的嘴角,裂开一条新的蹊径,酒窝里盛满新的光明;有些路如通衢大道,笔直恢宏,庄严肃穆地通往宏伟殿堂,通往人生旅程的纪念碑,高耸的路灯如同林立的卫兵;有些路如同九曲回肠的江南雨巷,让人心旷神怡、依心像意,看似行云流水、无拘无束,却是通往本真的最短距离;还有些七转八弯的路,看似迂回曲折,仿佛南辕北辙,其实是暗合“围魏救赵”的最佳捷径。 有些路人潮汹涌,似遥遥领先的阳关大道;有些路如孤寂的旅人,默默地隐于偏僻处;有些路风来乘风、雨来载舟,固然是顺风坦途,却须时刻警惕风向变动;有些路只闻蔓草野花的沙沙声,不见掌声沸腾的观众,却也不需要整齐划一的口令,不需要走一步、退一步的手令。 脚下这条小路,有时朝霞满布,有时也会晚霞西落。仿佛一条老者的皱纹,蔓延伸展。 几年前,我终于搬离居住了二十年的熟人老楼,怀揣飞翔之情,迁居到一处闹中取静、心远地偏的居所。 这里的花园小径,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模样。每天傍晚,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被牵引到琥珀色的小径上,我的脚步踏着青石板路上的光斑树影,仿佛与它们做着无声的交谈。 我会站在某个时光的褶皱里,回望那些转瞬即逝的道路——文学之路自不必多说,单以铁路轻轨和邮政马车为例,就足以让人兴叹。当年那拖着长长的灰白浓烟的绿皮火车,谁承想今日已化作风驰电掣、时速突破三百五十公里的银龙?那时一封饱含思念的家书,需邮差跋山涉水数日方能抵达,而今仅凭指尖轻触,语音便可顺着天路瞬息传来......这般沧海桑田,不胜枚举。 而我们的文化、文学系统中的那些绿皮火车和邮政马车,是否同样加大了功率,变成双驱或者多驱了呢?!在几十年之后,当后人回望今人执守的某一“康庄大道”或者某一朵“时代浪花”,是否同样感叹:后浪早已把之前的那个“大道”和“浪花”消融在时光之中。当人们仰望苍穹,仰望星空,看到亿万年前的那些耀眼的银光,是否会顿悟,重要的不是盘踞在哪一条看似永恒却终将消失的大道,而是不断趋近那个终极文明的通道。 我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遥望更远处。 大秦王朝精心修筑的“马路”,今在何处?曾几何时,那条大路上车轮滚滚、战马萧萧,那些用大秦专制铺就的通天古道,而今不过只剩几处残垣、几株蒿草。商君书的“竹简”,今在何方?曾几何时,那些竹片上刻满严苛禁律,令人心惊胆战、闭口无言,而今也只能寂寞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中。 那些宏大的驰道与古册,都曾经被以为永远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永不消逝,殊不知王朝终究会被前行的车轮碾碎泯灭,真正留下的只是一条条鲜活的从人们的内心深处、从骨中、从肉里生长出来的心路。 这条路貌似绵软纤细,却是无比柔韧,它附着在我们的骨髓里,积淀在血液中,铭刻在基因里,一代一代承传,生长成自己的一部分。 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驿道,怎么能踏出自己回家的路!那双别人的鞋子,怎么能抵达自己心中的远方! 眼前这条小路,虽非壮阔的交通枢纽,却宛若一条承载文明信息的网络高速。这里,每一口空气中的颗粒物都小于PM2.5,含氧充盈,远胜于那些喧嚣主干道的氧含量。这里,每一条清泉都似一条抹布涤净人间尘嚣,每一片绿叶都如一颗薄荷糖带来清凉,每一颗碎石都像苍宇中点亮的星灯。 它超越地域的藩篱,挣脱体系的桎梏,甚至无所谓归属哪个民族、哪个国度。它无须坐标系参照,无须指南针定向。它的终点或许不是某个中心地带,不是标榜功勋的里程碑,不是任何耀眼的领奖台,甚至不是那种被世俗认可的标签化“成功”。 它只是以人心为导航,通往一处文明的所在,一片不被虚假裹挟、不被禁锢驯化的开阔地,一片干净、温暖且自由的人类共同的原乡。 在这里,人人都能脱去虚假伪装,从而照亮真实的心房。 一条道路,重要的是它自身的质地品格,而非地图上的标签。笔直宏大的“国道”“省道”固然直指宏图,闪光的路牌如同勋章,指向无上的荣耀。然而,小路自有小路的泥土芬芳,当我的脚底踏在潮湿的地面,我可以听到它温柔的呼吸,触摸到它热热的心跳。 它容纳任何类型的脚步,它接受缓坡、水洼及沟壑,它包容积水、泥潭、土坷垃,它兼纳岔路、弯道和拐角,它允许百花的种子在路边生根发芽,它不干涉狗儿在树干下撒尿......它懂得与地形浑然一体,与地势起伏和谐相依。 这条容纳万千的小路,消解了单向度线性的取向,拒斥了千“路”一面的同质化,谢绝了被规训谏诫,所有的生命都能在这里和合共生。 当全球化的压土机碾过大地,只有这种保存了个性与差异的阡陌,才能在生态循环中真正地伸展自如。它用最低的姿态,擎起最高的自由。 当然,选择这条小路,或许意味着舍弃某些既得名利。然而,当决意为心愿放弃利益的时候,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看透之后,选择接纳,接纳而不同流;选择兼容,兼容而不齐趋。 当有一天,我看见自己二十余万字的小说被一位陌生读者抄写在笔记本上,并赋予它万千解读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文学永远在人们的心灵里发生传递,产生“电波”,没有权力与奖项的“变电站”,照样可以在读者心中发出轰鸣声。 至此,还有什么可遗憾呢?还有什么可争辩呢? 倘若此刻,我可以乘坐时光机回到四十年前,回到我的二十岁,站在今天的阅历刻度上,回望成长道路上种种缺失及蹉跌,我想,我依然会坚持这条略显寂寞和萧条的文学之路,不悲不喜,波澜不惊,自若安然。 还有一种潜藏的小路,不仅别人看不见,我自己也难以寻见——它掩埋在大脑皮层的褶皱里,形成网络一般的脑回路。 关于脑路,我想透露一个秘密,几十年来我从未走漏风声:我的脑海里有一个自动开合的屏障,遇见某些信号的时候,它会自动闭合或者开启,如同电脑的开关键。只是,这个功能常在自我意识之外,不经逻辑思量,不由我自主操控,而是直线到达。 就像有时我们不经意间闻到薰衣草的花香,一下子就想起衣橱里某件褪色的衣衫;或者,远处飘来一阵薄荷油的清凉,整个人立刻就会陷入某段夏日时光;而有时候,脑路却被瞬间断电,不由分说。我说不清其中的缘由,但这个屏障确实存在。 当我置身于鼎沸的人群里,或者面对某一位安静的个体,再或者沉浸在某一本图书、某一事件当中,其实我并未真正完全地置身其中,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确定,似乎脑回路悄悄分岔,脑中雾气蒙蒙哪儿也不在。 事后再回溯,我常常不解而惘然。有时候,我会忽然想起早年那糟糕的高考,答卷时的我到底在哪里?更多时候,我会扪心自问:四十年来我独自行走在这条寂寞的小路上,而现实中的那个我到底在哪里?那个我到底是谁?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并不全然认同。性格或许决定我们最初是被繁华大道吸引,还是为雨雾里幽深的小巷驻足,但认知才是那盏指引方向的灯。 我家阳台上曾养过一棵龟背竹,叶片硕大油绿,饱满而蓬勃。明明它向光而生,忽一日我竟见它转成一种奇异的弧度。细查才知,是花台架子的藩篱,使它的根茎枝丫被扭成畸形。 我们固有的那些认知何尝不被樊笼所制?仿佛那个花架的上限,框架越高,自由度就越高,生命被局限、被扭曲、被异化的程度就越轻。 我常想,那些栽种在花盆里的树,在狭窄的盆土局限中、在无形而压抑的樊笼里,永远长不出森林的模样。我多么想把花盆里的树,移种到我的小路上,让它们望见天空。 我愿意相信,文学的小路,无论怎样迂回曲折,无论穿越多少磕绊迷障,最终一定是朝向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那是任何应时应景的意识形态都不能遮蔽的永恒之光。 我愿在这条蜿蜒小路上,留下一个个清晰的脚印,以一颗小水滴的姿态,沿着思想的光亮前行,汇入那片自由的瀚海、一个无疆的文学星河。 现在,我依然习惯关拢房门,静坐案前,凝神专注,手指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舒适的家居布衣,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没有什么神圣使命的高昂,也没有什么意难平的低落,只是缘于心里偶尔涌动一些模糊不清的思绪,像一片云那样倏忽而过,需要我用真实的手指去触摸、去抓住,并把它们在键盘上轻轻地敲击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所有那些过眼云烟——无论《私人生活》的修剪红线、老前辈的“主义”僵化、插图版图书被召回,还是未遂的解职风波......那些将思想铸进统一模具的林林总总,终将被时间所风化。 如今我已鬓染白霜,岁月中的那些记忆也在渐渐褪色。这份年谱所串起的充满波折的文学小路,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历史,这些文学的褶皱镶嵌在每一个人的经历中,它将在挫败与幸运、束缚与自由的起伏中继续蜿蜒。 或许,这条蹊径小路仍在生长——它从我指尖的键盘延伸到云端(服务器),在人类尚未命名的维度里,它正用光的语言书写新的篇章。 当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如同一颗颗闪动的星星,撒落在银白色的屏幕上,当那些隐藏在岁月里的零碎片段,被涂抹在空荡荡的纸张上,我心里悬着的念头仿佛终于落了地。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6期) 作者简介:陈染,1986年于《人民文学》《收获》发表小说,1989年出版首部小说集《纸片儿》。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私人生活》,被译介至美、日、瑞典等国。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