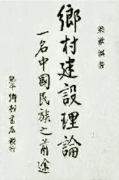难忘的十八个月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崔伟星 时间:2023-11-13 点击:

看到这张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去固镇插队的老照片,仿佛又让我回到了当初。
我是1974届华山中学毕业生,我是自觉自愿淌入上山下乡这条河的。1975年3月5日,我们扛着红旗、唱着战歌,意气风发地来到安徽省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张北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生涯。1976年9月5日因故离乡返沪,竟然正好是18个月。然而,我却创造了两项“记录”:第一,我是我们这批知青中插队时间最短的;第二,我也是一次性待在农村时间最长的,因为在丁庙的整整一年半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秉承实业救国理念的父亲,虽然在建国后饱受历次运动的困扰,依然将他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作为家中独子的我身上。而我的大姐,是1967届中学生,已在1969年插队在安徽省固镇县任桥公社。根据当时的政策,我是可以留在上海的,并已收到了上海电线二厂的通知书。但是青春的激情、理想的情怀,一次次地点燃起我胸中的火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伟人的激扬文字是我们的青春的宣言。我义无反顾地要求去农村、去最艰苦落后的乡村插队。
轩然大波在家中掀起,父亲伤心至极,从学校取回我的决心书坚决扣住,以令人窒息的无言来对付我这“不雕朽木”。母亲眼泪不断,无法理解我这“不孝之子”的行为。特别是她曾经去过固镇姐姐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落后与贫穷,“烂泥房子,窗也无没格,一只只黑洞洞眼,里厢墨赤里黑,日子苦是苦煞”,实在不明白我为何还要重蹈姐姐的前辙。年轻人有逆反心理,父母的反对,反而增添了我的决心,以为这都是习惯势力、落后势力。天将降大任于我,冲破习惯势力、落后势力的包围是我走向成功的第一步。针对母亲最担心“你吃不了苦的”威吓,我毅然一周不食荤菜,决心用事实证明“我是吃得起苦的”。
就这样,抗争以我的“胜利”而告结束,我顺利地迁出了户口,顺利地来到丁庙,开始了“教育农民、改造农村”,进而“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豪迈征程。
随着时间的延续,我逐步抛弃了当初那些不切实际,充满理想色彩的想法,沉下身子与社员打成一片,竟然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经历:
第一次抽烟。丁庙种烟叶,社员也都有抽烟的习惯,不但男人抽,女人一旦结婚生孩子后,也就百无禁忌了。社员抽烟又买不起香烟,除非需要办事来客,一般土气些的抽烟袋,“洋气”些的自己卷烟。我人生吸的第一支烟是队长给我的,记得是在开队委会时,他裁好纸,卷了一支喇叭烟递给我,“小崔,你尝尝”。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既然来农村了,就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就要有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习惯。于是,点着烟猛吸一口,结果呛得咳了好一会,但心里乐滋滋的,好像自己又爬过了一道坎。
第一次喝醉酒。如果说吸第一支烟是来自善意的友情,那么我的第一回醉酒,像是陷于“卑鄙”的阴谋。那时队里有派性,人也有私心,“心怀鬼胎”的会计、记工员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做些手脚,徇私舞弊。当时张北的会计是属于另一派的,平时我们都比较客气,也没啥私人来往,这天他“反常”了。我到他家里算工分对账,他殷勤地拿来白干酒,弄一点花生米,不停地倒酒给我喝。此前我可是从来没有沾过酒,这下子就碰上了60度的老白干,几杯下去我就彻底醉了。当我醒来时,帐全部已被会计“算清”了。至于是否真的是“阴谋”,其实我至今依然未“酒醒”。
第一次骑马。1976年春天,从内蒙古军马场下放了一批军马,我们生产队也分到了2匹,成了稀罕的宝物。平时只在电影里看过扬鞭跃马的镜头,此刻有机会“身临其境”,那是多么潇洒的事呀。于是凭借知青的特殊身份,我终于软磨硬抗地骗得了骑马的机会。我高兴地跨上马背,一松缰绳,两腿一蹬,“驾”的一声,军马放开四蹄奔驰在淮北大地。风呼呼地在耳边吹过,大关杨一棵棵向后飞去,我豪情万丈,不由放声高歌了起来。可是不一会就不对劲了,尾椎骨与屁股先是麻木,再是刺疼,一会完全不能沾马背了。我不自觉地拉紧了缰绳,微颤颤地抬高臀部,龇牙咧嘴地回到了牲口棚。下来都不能走路了,光板子军马把我屁股都磨烂了,我第一次骑马的豪情全没了。
第一次补衣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此话在家时理解不深,出了门就知道了重要性。在农村干活最费的是裤子和鞋子,使铁锨,蹬铁锹,没几天就裤膝烂了,鞋子破了,于是缝补就成了常活。下去没多久,我的裤子就磨烂了,于是抽个空我也学起了补衣服。穿针当然不在话下,剪一块布也很利索,缝上去可就太难了。不但针脚粗,线歪扭,缝了半天拿起来一看,坏了,前后片缝在一起了,真是哭笑不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呀,幸好小薛把我的裤子接了过去,没几下就补好了,后来她还教会了我套被子,否则真要盖棉絮了。
第一次住牛棚。1976年8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丁庙也不例外,许多社员家中也搭起了防震棚。为了及时预报地震的发生,保护集体和社员人身财产安全,从上到下“土洋结合”、群策群力,采取各种方式做地震预报。据说动物对地震的敏感度高于人类,大队也土法上马,安排我们知青观察牛羊牲畜的反应,张北队派我到牛棚值班。我身负重任住进了牛棚,两眼叮着老牛的反应,决心绝不错过一个微小的细节,将集体和社员的安危置于第一重要。盛夏的牛棚里闷热难闻,花生米大小的牛虻和“嗡嗡”的苍蝇四处乱飞,老牛慢吞吞地咀嚼着草料,不时甩动几下尾巴,驱赶身上的虫蝇。它吃饱了,蠕动起胃慢慢反刍,“哗”的一大泡尿水从身下飞泄而出,溅在地面像一条污浊的河流。紧接着,“啪”地一大堆牛粪落地,顿时骚臭味扑鼻而来,令人窒息反胃欲吐。我实在憋不住了,冲出牛屋大口喘气,真不想再踏进牛屋半步,可是心里惦记着地震预警,一咬牙又回到牛屋,“安危系我身,责任大于天”,我敢不尽责吗?
还有许多第一次,就不再一一细数了,都长留在我记忆中。
1976年9月初,一封家信彻底打乱了我在丁庙的生活,妈妈查出了重病。得到消息,我顿觉五内俱焚。18个月,我同妈妈刚刚分别18个月呀,在我离开时,妈妈虽然忧心忡忡,却还是健康的,精神矍铄地撑起整个家。如今,妈妈却突然地倒下了,难道是因为我的缘故,让妈妈伤心过度而染上沉疴?我不敢再想下去。18个月了,我竟然如此心硬,不回上海,不回家探望一下妈妈。我是怕见到妈妈责备的目光,是怕妈妈看到我而伤心,还是怕自己脆弱,见到了妈妈,会没有勇气再回丁庙?反正一切,都是源自于我的自私与无能,为了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竟然深深地伤了父母双亲的心。此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背人处让眼泪尽情流淌。我不能再多逗留一分钟了,我的心飞到了上海、飞到了妈妈身边。我决心要用我的孝心与良知,来陪伴妈妈战胜病魔。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离开了丁庙,离开了18个月来为之流汗、为之奋斗,曾期望度过一生的贫瘠的土地和善良的乡亲。当时我信誓旦旦地表示,一旦妈妈康复,我将立即回来。
就这样阴差阳错,我结束了18个月的插队生活。但它在我青春经历、人生道路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永不消退。
作者简介:崔伟星,上海市华山中学1974届毕业,1975年2月到安徽省宿县专区固镇县仲兴公社丁庙大队张北生产队插队。1976年9月返城。
晓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