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人韵士》中的名人与往事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4期 作者:钱虹 时间:2023-09-26 点击:
《雅人韵士》是我在宁波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博约书系”之一,其实就是一本学人随笔集。其中所收大都是我近年来在教书和学术研究之余,陆续写下的与名家恩师及诸多海外华文知名作家的交往纪实及相关述评,属于“非虚构”文学。
师 恩 难 忘
人的一生,往往会有许多偶然。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因为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和转折。比如,正当我求知欲最旺盛的豆蔻年华,偏偏遇上了灾难性的“文革”,从此十多年与学校、书本无缘;而1978年2月28日,当我怀揣着录取通知书去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成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许久我都一直疑心是在梦中。这是我人生中的两次“偶然”。每一次,它都使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与转折。前者,是亿万人始料不及的席卷神州大地的一场文化浩劫,它无情地泯灭了青年学生叩开人类文明宝藏大门的求知梦想;而后者,却又像阿里巴巴用暗语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藏金秘窟之门,像我一样的幸运者得到了泛舟学海、攀登书山的机遇,圆了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学之梦。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后,我就像一条欢快的小鱼一样,无比酣畅地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的营养。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不少国宝级名师,如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先生。我何其幸运,能够成为他们或亲自执教或聆听其教诲的学生。在我的人生之路上,他们的人格魅力、精深学问、学术品格和高风亮节深深地滋润着我,成为我进入学术圈的人生楷模。
这本书“师恩难忘”一辑中所收的数篇回忆散文,就寄托着我对他们的深深缅怀和浓浓思念。《先生风范,山高水长》即为纪念施蛰存老师而作。他被誉为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我念大二时有幸成为他亲自授课的唯一一届本科生之一,那年他七十五岁。一学期下来,这位年龄与我们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我们那届“小”学生中人缘颇佳,我们既钦佩他的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喜欢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丝毫没有一丁点儿著名教授的脾气和架子。从他的音容笑貌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长期遭受过人生种种磨难和不公的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毕业留校,有幸成为施先生的同事后,多次登门拜访,与他面对面交谈。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除了导师钱谷融先生外,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方言交谈。他操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无论说话还是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妙语如珠,让人如沐春风。

《仙风道骨,春风化雨》一文,回忆几位恩师中年纪最长、资格也最老的许杰先生。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建系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会员。他是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最早认识的作家。入学后不久,我在图书馆看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其中就收有他的小说《惨雾》《赌徒吉顺》等。茅盾先生赞许他是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我对这位以表现浙东乡村悲剧见长的名作家十分钦佩。研究生毕业后我与他成了同一教研室的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动,年近九旬的他拄着拐杖来了。我的影簿里珍藏着教研室同仁与许杰先生的一张合影,弥足珍贵。
《魏晋风度,坚守“人学”》记述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钱谷融先生,也是一位教会我懂得什么是文学、怎样做人做学问的学术引路人。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先生严肃地指出,他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实人,讨厌东钻西营搞关系的投机家,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如此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1957年先生写了那篇《论“文学是人学”》的著名论文,此后被批判多年,其间四次胃和十二指肠大出血,讲师一做就是三十八年,可他却从来没有后悔过,晚年的他对我说:“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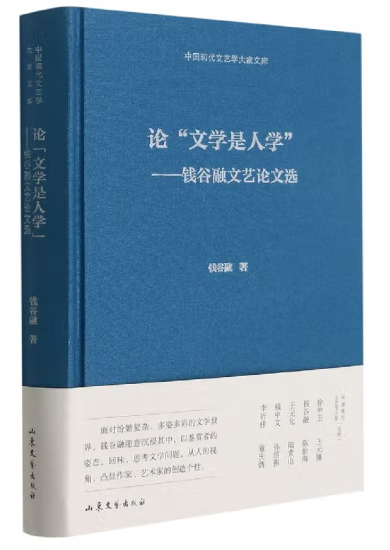
《铮铮风骨,国士无双》怀念我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系主任徐中玉先生。他在上述这几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中更为长寿。在超过百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中国文论和文学的标杆,历经磨难而以民族、国家大义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身处逆境而沉静,面临危局而敢言;兢兢业业俯首工作,甘于清贫埋首学问——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人生楷模与精神遗产。他的一生,端端正正地写好了一个大写的“人”字,成为我们后学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我后来之所以会选择文学研究为终身职业,是和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等老一辈先生们言传身教和鼓励支持分不开的。我发表的第一篇评论,就是选修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合开的“文艺学专题”课的一篇作业,是徐先生发还作业时鼓励我去投稿,后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上。虽然至今我已经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但受到徐中玉先生鼓励而投稿发表第一篇论文时的激动之情仍难以忘怀。还有在读研究生时,钱谷融先生为我的论文发表写推荐信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此后的任何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栽培与教诲。
名 人 忆 旧
第二辑“名人忆旧”中所收入的大都是与文坛名宿,如巴金、贾植芳、余光中、刘以鬯、钱法成等文学前辈交往的纪实性散文。
《那年春节,巴金给我签了名》一篇,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写了《〈寒夜〉悲剧新探》《〈寒夜〉人物谈——论汪文宣》等论文。文学研究会作家王鲁彦是《寒夜》中主人公汪文宣的原型之一。长期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不幸染上肺病,因为缺少医药,无钱医治,竟在1944年夏天痛苦地病逝于桂林,年仅四十三岁。出于对鲁彦等已故作家的崇敬之情,我由此结识了鲁彦的夫人——覃英老师,她和鲁彦的遗腹子王恩琪先生当时住在桂林路上海师范学院教工宿舍。渐渐地,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于是,我知道了巴金对王鲁彦及其家人长达五十余年的关怀与牵挂。1985年春节的大年初三,覃英老师带我去给巴老拜年。巴老用略带颤抖的手在我带去的《寒夜》上亲笔签了名。
《贾作真时真亦“贾”》是为贾植芳先生辞世一周年而作,回忆了我与贾先生的两面之缘。1986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导师钱谷融先生请他担任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开始见到他和中山大学吴宏聪教授时非常拘谨,说话也有些结巴。贾先生见我如此紧张,笑着对我说:“你的论文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你不要害怕,我这个主席虽然是真的,但教授本来就是‘假(贾)’的嘛。”他这一说,钱先生、吴先生都会心地哈哈大笑,气氛顿时变得缓和轻松起来,我说话也就利索多了。那天论文答辩十分顺畅,甚至还很愉快,贾先生后来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虽然他那一口山西话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我还是句句都能明白。从此,我一听贾先生的名字便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后来有一次,他坐在我们“小字辈”一桌,坦然而愉悦地接受我们给他敬酒。他姓贾,性情却是真的,从不掺假。
《凭一首〈乡愁〉》一文,写1988年我应邀赴港出席“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时,与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初遇及跨越“浅浅的海峡”后三十余年的交流往来。初次见面似乎很难一下子把他那些时而柔情脉脉时而博丽雄浑、构思奇妙而又风格多变的诗文,与眼前这位个头不高、头发花白、精精瘦瘦、说话慢条斯理的长者联系起来。他不像一个潇洒浪漫的诗人,倒像是一位矜持儒雅的绅士。在分别的那天,我收到了余光中先生最新出版的精美散文集《凭一张地图》。扉页上有他用一手漂亮字体工整的题词。后来,他又请人转赠给我两部在台湾出版的诗集《莲的联想》和《隔水观音》,上面也都有他的亲笔签名。睹字思人,如今已成了“遗书”。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写我与“香港文学泰斗”刘以鬯先生的海上文学缘。从1988年他发表我从上海寄去的《戏内套戏,梦中蕴梦——论白先勇小说及台湾版话剧〈游园惊梦〉》始,到2018年他以百岁高龄在香港辞世,其间我与这位沪籍“同乡”结下的深厚情谊,尤其是历经周折帮他找到了其在上海的故居(也是当年他创办的怀正文化出版社的社址),拍了许多照片寄给他。他很快来信说看了照片很激动,流下了眼泪。《香港文学》1991年5月号上发表了拙作《为了“拆除”的纪念——怀正文化社旧址寻访记》。在施蛰存先生的劝说下,1994年他终于带着太太罗佩云一起“回家”了,距离他1948年离沪整整四十六年。他去世后,有媒体报道说他离沪赴港七十年从未回过上海,这是不确切的。

还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和《“真的猛士”真性情》,都是写浙籍钱氏文化名人的文坛掌故,前者是写著名剧作家、书法家钱法成与浙江昆剧团《十五贯》的“昆曲复兴”故事;后者通过史料查证,厘清了五四文化名人钱玄同与绍兴古越藏书楼主人及与其女儿徐婠贞联姻之谜。
同 道 中 人
“同道中人”这一辑收入的数篇随笔与笔记,皆为多年来与海外华文著名作家,如卢新华、严歌苓、张翎、陈若曦、尤今、吕大明、谢馨、吴玲瑶、潘耀明等相知相熟的文友接触、交往的记人散文与阅读笔记,这些文友遍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菲律宾、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意在凸显其人文情怀及华语文字背后的人格与艺术魅力。
这篇《吐丝心抽须,锯齿叶剪棱》,是对《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及其文学创作四十年的夹叙夹议的述评。卢新华和我属于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高校的首届大学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1977级。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听说过复旦大学卢新华的名字:1978年8月12日的《文汇报》破天荒地用一整版篇幅刊登小说《伤痕》。而我写出长篇论文《论卢新华四十年文学创作历程》却是在2016年。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采取作家与评论家面对面的形式举行,我所评论的作者正是卢新华。
《“小说是作者的一个个梦”》《“海那边”与海这边》原是我编选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美籍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集的“编后记”,主要是文本解析。没有当论文来写,便从容舒缓很多。其中也不乏感性的评述,“读严歌苓的小说,会让你不再心心念念只想着一己的不幸与个人的悲欢。所以,编选她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在做一个个‘梦’的解析,一次次情感的探险。”

严歌苓作品集
《“曲”中情意结,“恋”时人婵娟》是我编选的张翎中短篇小说的“编后记”,谈我与张翎从相识到熟悉的文学交往。2002年秋天,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浦东名人苑宾馆举行,来赴会的“北美兵团”中,有几位声誉鹊起的 “新移民”作家,张翎是其中之一。而后,大陆及台港澳地区文坛似乎陷入了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泥沼,而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翎,却幸运地隔绝了这争名逐利的圈子,文心变得纯粹与清爽。她那些从容淡定、精致缜密的“业余”小说,反倒显得自然深邃,纯净大气,如《雁过藻溪》等作品。
《至情至性的人事风景》和《“艺术家只能听命于美神”》,分别是写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和法国华文女作家吕大明其人及其散文的。陈若曦,“她之所以在其散文中避免当一名浓墨重彩地描绘山水的工笔画师,更不想当一名口若悬河地炫耀名胜的旅行导游,乃是在于作者心目中对‘人事风景’的关注和留意,远远地超过了自然景观本身!只有人世间的人,这才是陈若曦最看重、最珍视的”。而吕大明,“她具有抒情的、唯美的、天然带有某种敏感与伤感的艺术家气质,是创作散文的最佳人选”。
《“放只萤火虫在心里”》写我所认识的新加坡女作家尤今,“尤今总也不显老。认识她已经二十年了,每次见她,总是乐乐呵呵的,很快乐的样子,一笑起来,发自内心的爽朗大笑,很有爆发力,一点儿也不遮遮掩掩。从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二十年过去,她还是这样”。她说:“心中有桃源,无处不天堂。”类似尤今般快乐的还有美国华文女作家吴玲瑶。《幽默是人生的“润滑剂”》即是写其人与其文的。在北美华文文坛,吴玲瑶为人为文皆以“幽默”著称,在她那些即使针砭时弊的杂文中,也往往看不见辛辣的讽刺,尖锐的挖苦,更不见声嘶力竭地大声斥责,吹胡子瞪眼地厉言呼喝,即使是面对不怀好意的挑衅,她认为最好也能利用智慧与口才努力化解,既一吐为快,又能报“一箭之仇”。真是趣味十足。
《缪斯赐予的典雅与浪漫》写大器晚成的菲律宾华文女诗人——谢馨。见识谢馨,只觉三“奇”。一奇,是她的“根”。她原籍上海浦东,属于“滴滴呱呱正宗我伲上海本地人”。二奇,是她的声。她做过播音员,有一副响亮而富有音乐质感的好嗓子。三奇,自然是她的诗了。比起豆蔻年华即扬名诗坛的早熟才女来,谢馨甚至颇有些大器晚成的况味。但这位缪斯女神赐予她以灵感与才情的“后起之秀”,起步不久就成为令诗歌王国瞩目的天之骄女。品其诗也在阅其人。
《非鱼非石,是景是灵》写的是有着香港“宋公明”之美誉的彦火(潘耀明)先生:一位广结文缘的香港资深散文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彦火先生不仅擅长写散文,而且是一位有着侠义肝胆的谦谦君子。文若其人,散文对于他而言,是再适合不过的文体。写散文,需要有真性情。从三十年前他为我慨然寄书,到看他在《书呆子的杂趣》为自己画肖像,虽不敢说彦火先生嗜书如命,但可以肯定的是,书就像他的亲人和恋人,多年来,他始终如一地与她们相依为命。也许,他下辈子仍会与她们相伴相爱。
余光中先生曾说:“散文家无以凭借,也无可遮掩,不像其他文类可以搬弄技巧,让作者可以隐身在其后。”散文既无技巧可以卖弄,却能把作者的才情、学识、人格、风度、气质、修养及个性清楚地袒露出来。思想感情的贫瘠,知识学问的浅薄,文学功力的欠缺,胸襟气度的窄仄,都会在散文中无处躲藏,让人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其实是极不容易写的。散文靠什么来赢得读者呢?我以为,靠真情实感,作者不能说谎,不能虚构,不能粉饰,不能矫情。总之,在写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我是真心敬重他们,爱戴他们,佩服他们,书写他们的。巴金先生生前说过,把心交给读者。如今,我把心交给《雅人韵士》中的每个描写对象。我之所以写这些人和事,尤其是其中有不少是文坛大家、学界名流和文学名人,不是为了攀龙附凤,借写名人来抬高自己;我也不是为了讨好名人,取悦别人。作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找我写评论的人不少,但我首先是读作品,看作品能否打动我,这也是多年前钱谷融先生教我的:“好的文学作品会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不能让人动情的作品,不能算好作品。”如果你的作品不能打动我,哪怕再有名气,我也是不会写的。这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坚持的学术底线。

感谢宁波出版社总编袁志坚先生,没有他的力邀,我不会想到要出版这本集子。感谢宁波出版社文学出版中心主任午歌先生,还有总编助理徐飞先生和责编陈姣姣女士,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这本集子也难以问世。谨致谢忱。
2023年3月26日写于越秀
(晓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