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刘希涛 初见叶辛,是在1990年10月,一个桂花飘香、枫叶流丹的季节。他刚从贵州调回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出任《海上文坛》杂志的主编。 他个头不高,宽宽的前额下一双晶亮的眸子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衣着随便,若不知他是位作家,还以为他是位朴实的农民或乡村干部……这就是叶辛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1998年8月,窗外,高温咄咄逼人,室内,吊扇呼呼旋转。在上海作协大厅安静的一角,叶辛微笑着和我握手,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他人生的阅历和生活的履痕。他侃侃而谈,薄薄的嘴唇里讲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叶辛原名叶承熹,出生于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他在上海一条弄堂深处呱呱坠地。那时的上海,五方杂处,百业纷陈,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1957年9月,和众多满7岁的孩子一起,叶辛背着书包怯生生地走进了住家对面的那所小学。那儿解放前叫作“跑狗场”,解放后改称“文化广场”。小学三年级时,《中国少年报》上连载了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老师每星期给他们念一节,边念边讲解。叶辛嫌老师讲得太慢,等不及,便掏出零花钱买了一本,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从此以后,他在众多爱好中又添了一件——读有趣的书。是书籍,给他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户。 1966年6月,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中学毕业的叶辛,看到纷纷扰扰的世界露出了它青面獠牙的一面:那些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挥着体操棒、铜头皮带打破了“狗崽子们”的头,逼着“走资派”在熊熊的火堆旁爬。火堆里,烧的都是叶辛爱读的书哇。喜爱思索的叶辛怎么也看不懂,他疑惧地退缩了,就此埋首书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下一些习作,在同学、朋友间传阅。 1969年3月31日,叶辛与妹妹叶文一同离开了上海。倚在南行列车的窗口,前去一无所知的地方插队落户。那是贵州省修文县久长公社永兴大队第三生产队,一个叫砂锅寨的穷乡僻壤,那儿离上海足有五千里路程,火车要开两天两夜。叶辛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奇特的倒春寒,雪花飘呀飘呀,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飘落在送他们的卡车上,飘落在连绵无尽的大山脊梁上…… 就这样,叶辛带着迷茫的热情到达了他的“第二故乡”。在那偏僻的大山沟里,他开始自食其力:从低矮的牛栏、马厩、猪圈的小门里,把猪粪、牛粪挑到农田里去;参加修建湘黔铁路,伐木,下河捞沙,开山放炮,抬石头。晚上,他则守着煤油灯,伴着茅屋外三两声犬吠,几乎每天都要写到夜阑人静。没有桌子,他就掀起铺盖,以铺板当桌;没有电灯,用墨水瓶改制个小油灯,摇曳的光焰,把他的帐子熏得漆黑。 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到一块儿抽烟喝酒、打牌赌钱、偷鸡杀狗、谈情说爱,叶辛心有不甘,一刻不停地写。别人在发牢骚、吹牛皮,他悄悄地带一块搓衣板,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写;赶场天,别人为打一顿牙祭忙着上街,他就躲在屋里写;有时起大早,赶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 在下雨即漏、刮风就摇的茅屋里,在天天以瓜代菜、以盐巴水充油水的日子里,叶辛整整11个月没尝到一片肉。繁重的劳动,营养的缺乏,让他掉了6颗大牙。在文学这条崎岖的小道上艰难地跋涉,他为心中的追求付出代价,可他什么也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 在热切的期待中,等待叶辛的却是退稿,一厚叠一厚叠,三四十万字的小说稿。外面包扎的牛皮纸已经撕破了,这在乡间的邮电所里是常事。捧着退稿,叶辛失望得掉了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一声不吭。他要面子,可他也扛得住失败。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省下钱来买煤油,并指望上海那些好心的同学给他寄稿纸,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下去! 如今看来,文学给叶辛的命运带来的打击,实际是在造就他。命运的重锤在他身上反复锻打,仔细加工,这使他痛苦,也使他成熟,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素质。 就在叶辛苦苦挣扎的日子里,他的痴情和执着,悄悄地打动了一位姑娘的心。她叫王淑君,是妹妹叶文的好友。这位温柔俏丽的姑娘动情了,开始为叶辛抄稿子。文学是他们的大媒,第一个发现并支持叶辛的伯乐,就是这位沉稳、充满智慧的姑娘。 1972年9月,公社决定让叶辛到耕读小学教书。除去课本,叶辛让孩子们读普希金的诗,念高尔基的小说……可这儿的孩子见识少,连“面包”也不知为何物。村里没有,小镇上没有,最后,叶辛回上海探亲时带只面包到砂锅寨。面包放在讲台上,他让学生排队上来看。 那一届叶辛教的学生,除几个年龄过线的以外,全部考上了中学。 教学之余所有的时间,叶辛都用来写作。他记气象日记,观察大自然的阴晴雨雪;他留神周围老乡,观察村寨上的世态人情…… 1977年春天,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叶辛在遭遇一百多万字的退稿后(后来他妹妹用这些废纸生炉子,天天烧几张,烧了一年多也没烧完),他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问世了。第一版20万册,第二版17万册,并翻译成了盲文、朝鲜文,改编成了连环画,还改编拍成了电影《火娃》。 那一日,说到这儿,叶辛喝了口水。他用一种深沉的语调对我说:“这本处女作是幼稚的,可它对我是多么的珍贵啊!” 自此叶辛越写越顺。电影《火娃》公映后,1979年的秋天,他躲在猫跳河畔一个偏僻的峡谷里,白天写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夜晚则着手构思一部新长篇《蹉跎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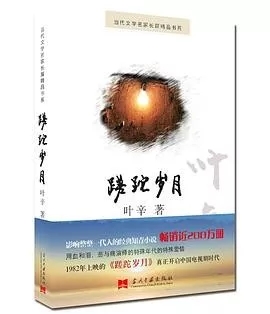 197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叶辛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干部子弟,由于父亲被打成了黑帮,关进牛棚,插队落户到了一个偏僻村寨。在那里,他和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相识了。姑娘在生产队里放鸭子,他在河滩上放羊,他们恋爱了,爱得深沉。粉碎“四人帮”后,痴情的姑娘以为命运之神会向她露出妩媚的笑脸,却不料严酷的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官复原职的干部以高压手段干涉儿子的婚姻。儿子抵挡不住大城市的诱惑,抛弃了恋人,酿成了悲剧。 叶辛的思绪泛滥起来,他夜不能寐,决定要写一写“血统论”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戕害,写一本新的长篇小说。不过,他要把它的结局写好,决不写成悲剧。这就是写作《蹉跎岁月》的直接起因。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光叶辛收到的读者来信就多达一千余封。在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代会期间,代表住地有个特设的售书亭,《蹉跎岁月》很快卖光了,却仍然不断有代表来问,结果大家发现作者就在身边。于是,有11位教授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蹉跎岁月》讨论会,请叶辛参加。西南交大一位姓曹的教授说,他从不看电视剧,有一次见女儿边看边哭,他也坐下来看,一直看到完,一夜没睡好,这是《蹉跎岁月》的魅力。 从《蹉跎岁月》到《家教》,再到20集电视连续剧《孽债》播出,叶辛作品的读者、观众从知青、文学青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叶辛把这种成功归功于“碰到了内行的好导演”。但作品的精彩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叶辛认为,电视虽为一种快餐文化,但它发展至今也需经典之作,作者要以严肃的态度进入创作,才能产生感人的作品。光想着赚钱,一两天就拿出一个本子来,实不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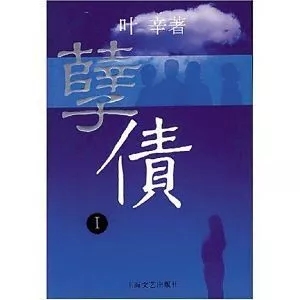 叶辛始终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写出人物心灵深处的感情和喜怒哀乐,还要写出性格内部深层次结构即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矛盾搏斗,以及由这种搏斗所引发的不安、动荡、痛苦等一系列复杂感情,更要写出人的灵魂在前进、退却以及堕落时所受到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包括反映这种社会关系的心理历程。能达到这种要求,方为好作品。 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尽管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他始终牢记自己归根结底是个作家。作家,就要以作品说话。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曾向读者奉献出讲述自己知青生涯的写真集《半世人生》,以及记录与妻子王淑君苦恋故事的《往日的情书》。这两本书,凝聚着叶辛的情与爱。 与大明星们装帧精美的写真集不同,《半世人生》没有矫饰的照片和矫情的文字,一张张昔日的黑白照片搭配着质朴的回忆文字,讲述着主人公人生旅程中真切感人的故事。 叶辛的恋爱季节是在砂锅寨孤军奋斗的岁月里开始的,王淑君慧眼识人,情坚不渝。两人从1969年相识到1979年结婚,苦恋了十年,而其中绝大部分的日子是在两地分离中度过的。在当时根本别想找到一部电话的情况下,维系两人情感的唯一手段就是写信。他们在书信中倾诉着相互的思恋和感情,互诉着插队落户生涯里的点点滴滴。带着被雨水浸蚀而看不清的字迹,这些书信没有经过一点修饰,按当时的原始面貌发表。 “承熹,自你走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这里的“承熹”,便是当年的叶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感情的加深,两人间的称呼已由“承熹”“淑君”发展到“亲爱的熹”“你的淑君”,再后来则是“毛头”和“甜甜”。“毛头”是叶辛对淑君的昵称,“甜甜”,不用说,你懂的。(他们的儿子就叫叶田,是要儿子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太多,甜甜地过一辈子呢,还是要让这昵称也“传宗接代”呢?) 在整理这些“往日鸿雁”时,叶辛的心头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回他的第二故乡——砂锅寨去看看。看看那儿的崇山、峻岭、房屋;看看他们劳作的田块、坡土、小路和桦树林;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是否还像原来一样清贫和苦累。 那年3月31日,正是29年前叶辛从上海出发的那个日子,他终于成行。山,还是那样的山;路,还是熟悉的路。岁月改变了容颜,但叶辛痴情不改,此心依旧。他的岁月,不是空白的。 那一次,听叶辛娓娓讲述半世人生,话语时急时缓,话头或深沉或轻灵,人生历程如一泓甘洌的泉水流经我的五脏六腑……我在想,在作协的领导岗位、在名人的社会角色、在作家自身的创作这三者之间能保持一种平衡,这和叶辛始终拥有一种执着与真诚的心态,不无关系。 从1990年结识叶辛至今,已整整过去了29个年头。在贵州生活21年,使叶辛有了与众不同的观察社会的冷静目光。回沪以来,叶辛对上海的生活形态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叶辛告诉我,他又一部新长篇《五姐妹》即将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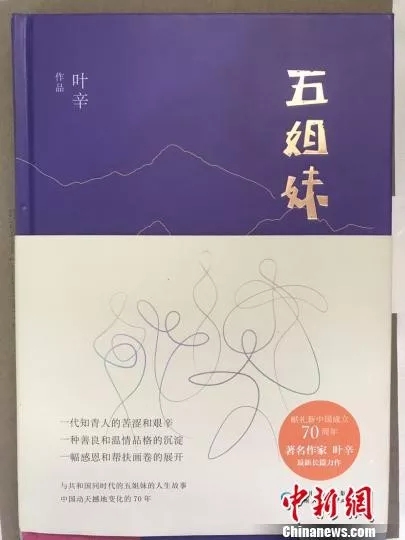 与共和国同龄的叶辛,还不忘“来处”,时常为业余作者与文友鼓与呼。前一阵子,他从江苏兴化驱车300公里赶到上海五角场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与近30位作家诗人一起参加采风,走进陈望道旧居,走进北茶园睦邻楼组,走进由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题写场名的江湾体育场,走过大学路,走进创智坊社区……他用70年的同龄,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五角场商圈发生的变化,并为并非地处市中心的民间文学团体上海出海口文学社,慨然题写社名、刊名,还带头撰稿。叶辛恳切地对我说:“希望文学社的成员写出更多有光芒、有温度、有理想、有筋骨的作品。” 不断用写作表达对国与民之挚情的叶辛,从壮年变成了小个子的老人。几乎每晚六点三刻,人们总能看见叶辛在居家附近的肇嘉浜路上散步。 (本文刊于2019年10月4日解放日报·朝花)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