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辰220周年纪念,全世界的读者都深情地铭记这位为世界文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

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写出了俄国曾经的一个时代,描绘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全景图画,这部经典不仅成为19世纪初“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且也为欧洲“浪漫的现实主义”的产生增加了俄罗斯的绚丽色彩。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界关于普希金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都可以从这部经典中找到阐释的丰富依据。图为根据普希金这部名著改编的电影《奥涅金》剧照

普希金肖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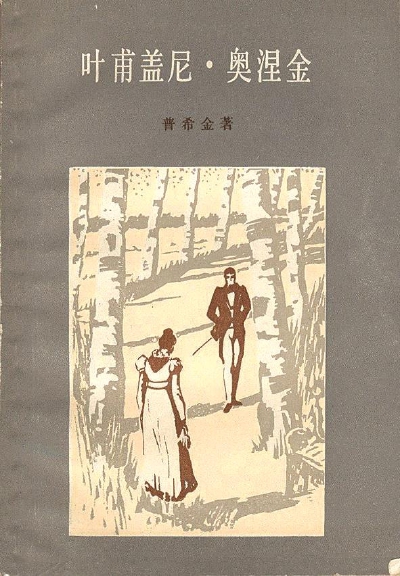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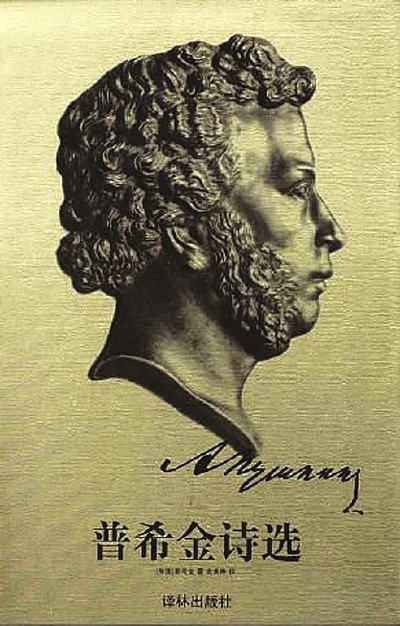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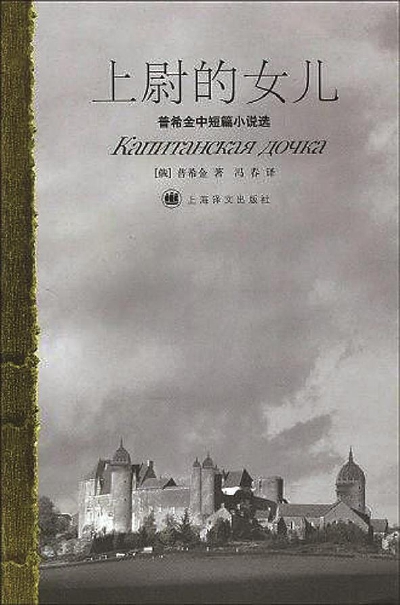 普希金作品中译本 普希金,一个文学读者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 尽管,由于评论界及创作界的更新换代,新生阅读界审美疲劳的原因,他作品的影响力曾经一度式微,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家为此忧心忡忡,但正如他自己曾经预言的那样:“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有一个诗人流传。”(查良铮 译) 2019年,迎来了这位世界大诗人诞辰220周年。正像俄罗斯19世纪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在普希金离世不久后一首悼念诗里写到的那样,“俄罗斯的初恋,我们不会忘记你”,而对于众多的俄苏文学读者来说,普希金的经典,也是他们的俄罗斯文学“初恋”。约两个世纪来,世界文学的读者深情地把普希金铭记,不久前,在诗人生活和创作过的“北方威尼斯”圣彼得堡以夏宫开启喷泉的仪式隆重地拉开了纪念伟大诗人诞辰的序幕。 俄苏文学“光明梦”的传统之源 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在概括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了战斗民族文学的“苦难审美特征”,他借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表述方式指出,俄罗斯文学是“我苦故我在”。然而,俄国文学自普希金登上文坛后,文学的叙述与抒情却不再一味地倾诉苦难,而从如歌如泣的倾诉中常常闪现出一道“忧伤的明亮”。正像高尔基对普希金感恩的那句赞词:“普希金像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的天空,燃起了一轮新的太阳;这轮太阳的光辉,立即使得这个国家变得肥沃富饶”。苏联著名的文化史学者利哈乔夫院士说:普希金那句“我的忧伤也明亮”感动了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伟大诗人艺术风格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俄国作家,他们在描写俄罗斯民众的苦痛时也没有一味沉沦,而时常写出苦痛中的坚韧与希望。“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高尔基自传小说《童年》的这句话,诗人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要苦苦地等待”这句诗都明显传承着一种普希金式的“明亮的忧伤”…… “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那快乐的时日,相信吧,终将来临!”普希金的这些光明诗句二百多年来,始终照耀着俄罗斯文坛。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提到过苏联文学“光明梦”的浪漫乐观特征。其实,苏联文学,主要是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悲情的乐观”的传统最早就是源于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那是一种基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的乐观信仰,这种深信人类美好未来的“光明梦”的传统与俄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接受歌德《亲和力》、席勒《欢乐颂》的乐观情绪有关。只要回味一下普希金“最心爱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连斯基诗意的憧憬就能深切地体会到: 他相信,命运选定一些人作为人类神圣的朋友, 他们结成的家族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终将照耀我们, 美不胜言的光辉啊,总有一天把幸福赐给人间。 (智量 译) 俄罗斯民族文化自信的诗意宣示 最近两年,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带到中国来的由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话剧先后在乌镇戏剧节、上海和北京上演,演出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剧场和剧评界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普希金旋风”。普希金的原著写出了俄国曾经的一个时代,描绘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全景图画,这部经典不仅成为19世纪初“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语),而且也为欧洲“浪漫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语)的产生增加了俄罗斯的绚丽色彩。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界关于普希金思想的“俄罗斯性”“斯拉夫性”“欧洲性”“欧亚性”“全人类性”都可以从这部经典中找到阐释的丰富依据。 更重要的是,通过普希金这部经典,俄罗斯文学找回了自己民族文化自信心,尽管,英国“湖畔派诗歌”和拜伦作品风格对普希金的这部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奥涅金”姓氏的创造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美丽的奥涅加湖,是彼得堡西北的一个静谧自然的所在,在湖畔,有浪漫诗人的心灵追求,在那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俄国湖畔诗人”模仿拜伦式忧郁症的惆怅、忧郁和徘徊。但普希金毕竟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了。法国文化学家丹纳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民族的文化特点。奥涅金这个姓氏的创造正是来自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普希金选取奥涅加湖作为主人公姓氏的来源,既为浪漫主义的使然,更是对作者俄国地理环境的钟情。奥涅金——这个由俄国湖泊化来的主人公姓氏具有俄罗斯地理意涵,而主人公却取了一个法国式的名字欧仁(俄语发音是叶甫盖尼,也译成“欧根”)则是反映了当时俄国上层对欧洲文化的崇尚,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在姓名符号上做俄欧对话的文章!而小说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更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族名字,一个普通而响亮的俄罗斯名字,它象征着诗人心中俄罗斯美丽的本土文化。奥涅金与塔吉雅娜,一个欧化的心灵漂泊的俄罗斯人与一个坚守斯拉夫价值观主人公在思想情感上的相互对峙。从这个意义上看,《奥涅金》整部小说既可以看作是作者与西欧文化的对话,进一步也是俄罗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初始的思想交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普希金这个经典中看出了留恋俄国乡村生活的“灵魂上的俄国人”塔吉雅娜的“圣象”意义,正是充分体会到了普希金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观的坚守。 《茨冈人》,普希金南俄时期最优美的传奇长诗,由瞿秋白先生最早翻译成中文。歌剧《卡门》,则被誉为世界歌剧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读者不禁要问,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为何在纪念普希金文章中要提及它们?当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陶醉在法兰西这部歌剧艺术中,是否能想到这里竟然也有普希金诗歌之魂呢? 回答是这样的:据丹麦文学批评大家,《19世纪文学主潮》的作者勃兰兑斯考证,正是《茨冈人》启发了热爱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著名小说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梅里美把普希金 的比萨拉比亚草原茨冈姑娘珍妃 儿的悲剧故事改编成了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嘉尔曼(卡门)的悲剧故事。作曲家比才和他的歌剧剧本在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卡门)的基础上,又结合普希金的《茨冈人》完成了著名歌剧的创作,特别是卡门咏叹调《哈巴涅拉》、堂·何塞的《花之歌》的歌词主题与歌词明显来源于普希金的原诗(《茨冈人》和《一朵小花》)。因此,当我们在欣赏歌剧《卡门》的传奇剧情与歌唱艺术时,实在应当了解俄国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对世界文艺的巨大贡献呢。普希金在世界歌剧经典的创立上也功不可没!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普希金经典诗歌选摘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爱情 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像我一样地爱你。 ——《我曾经爱过你》 我们的玫瑰在哪里, 我的朋友们? 这朝霞的孩子, 这玫瑰已经凋零。 不要说: 青春如此蹉跎! 不要说: 如此人生欢乐! 快告诉我的玫瑰, 我为她多么惋惜; 也请顺便告诉我, 哪里盛开着百合。 ——《玫瑰》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至美的天仙。 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 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 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 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倩影。 ——《致凯恩》 相关链接 从普希金寄出的这些信件里,窥见文学巨匠的另一面 致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824年4月初 我刚从基什尼奥夫回来就看到信件、包裹和《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谈话》(维亚泽姆斯基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写的前言《出版家和经典作家的谈话》原编者注)妙极了,不仅是观点好,这些观点的表达方式也漂亮,论断见解无可辩驳。你的笔法奇迹般地进步了。前不久我读过《德米特里耶夫生平》,文中所有论断好极了,但是该文技巧怪异,言辞偏颇。看了自己的评论文章与信件,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想在日内写点什么,谈谈我们可怜的文学,谈谈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和茹科夫斯基的影响。也许要发表,常言道:各说一套,生财之道。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俄罗斯,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有关浪漫主义诗歌,你的意见是对的;可是你抨击的古老的……古典主义诗歌,在我们这里是否十全十美,还是个问题。凭福音书与圣餐我再说一遍,尽管德米特里耶夫有过影响,但他不会、也不该比赫拉斯科夫和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更有分量。难道他一个人就能代表我们的古典主义的文学,如同莫尔德维诺夫一个人就能代表全俄反对派么?他又凭什么是经典作家呢?他的悲剧、醒世诗或者史诗何在?给谢维琳娜写几首寄语诗、转译吉沙尔几首讽刺短诗就是经典作家?《欧罗巴导报》的意见算不上什么高见,生《好心人》的气是不可能的。浪漫主义诗歌之敌何在?经典中坚何在?有空我们可以谈谈这一切。现在谈下正经事,也就是谈钱。斯廖宁给《奥涅金》出的价,多少合我的意。 致J·C·普希金 1824年11月上半月 弟弟,能否给我寄来那位德国人对《高加索的俘虏》的评论?(向格涅季奇要),看在上帝的份上,再寄些书来。如果出版家先生们不肯赏光,不肯把自己的选集、丛刊赏给我,你就让斯廖宁把它们转寄给我,其中包括布尔加林的《塔利亚》。 …… 多寄点诗来!多寄!多寄些来!寄《拜伦的谈话录》来!寄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来!这是我的精神食粮。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午饭前我写《笔记》,午饭我吃得很晚,饭后骑马遛遛,晚上我常听童话——借此弥补我那可诅咒的教育的缺陷。这些童话故事多美啊!每个童话都是一篇叙事诗!哦,上帝!差点忘了!请你办件事,把斯捷潘·拉辛枯燥的历史资料给我寄来,他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富有诗意的人物。 再见,我的欢乐。巴拉丁斯基的《芬兰女人》写得怎么样?盼。 致瓦·彼·祖布科夫 1826年12月1日 亲爱的朋友,我27岁了,该好好生活了,就是说,该享受一下幸福了。你对我说幸福不是永恒的,真是新鲜之谈!我操心的倒不是个人的幸福,在她身边我能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么?——然而,一想到将来可能有厄运在等着她,我就不寒而栗,一想到不能使她变成我所期望那样的幸福之人,我就不寒而栗。我的生活至今如此漂泊不定、如此动荡不安,我的性格反复无常、嫉妒、多疑、急躁,生硬,同时又脆弱——凡此种种有时不能不令我进行痛苦的思考:是否应当把如此温柔、如此美好的人间尤物的命运和我这如此悲惨的命运、如此不幸的秉性联结在一起?……天啊,她太好了!我对待她的举动多么可笑!亲爱的朋友,请你务必消除我的举动使她产生的恶劣印象吧。请告诉她,我比看上去要理智,证据么——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这个卑鄙的帕宁迷恋她两年了,才打算在复活节后的礼拜里向她求婚——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包厢里,另一次是在舞会上,第三次我就向她求婚!要是她认为帕宁是对的,就必然认为我是个疯子,不是吗?——你可要向她解释清楚,就说我是对的,即使见了一次面,我就不能犹豫不决了,就说我不敢抱有让她迷上我的奢望,就说我直接步向结局是明智的,就说既然爱上了她,就不可能爱别人胜过爱她,就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比她更美好的女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有比她更美好的女人…… (节选自《普希金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俄罗斯文学最早的中译,便是普希金作品 普希金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是我们中国广大的读者非常熟悉的,他的不朽的作品也是最为我们所喜爱的。 远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国就已经翻译了他的著名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当时这本书的题名被译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根据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史料,这不仅是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也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我国最早的中译。 接着在1907年,鲁迅先生即用令飞的笔名写了《摩罗诗力说》(发表在1908年的《河南》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普式庚(即普希金)的生平和作品,并指出:“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正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又介绍了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和鄂戈理(果戈里),这可说是我国最早介绍俄国文学的论文。 普希金的作品广泛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首先是1920年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收了沈颖翻译的普希金的两个短篇《驿站监察史》和《雪媒》(即《暴风雪》),瞿秋白还专为前一篇小说写了序言。1921年,《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其中刊载有普希金的传记和郑振铎翻译的小悲剧《莫萨特与沙莱里》。在单行本方面,共学社编译了一套“俄罗斯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种,就是1921年出版的安寿颐翻译的《甲必丹之女》,书前附有耿济之、郑振铎两人写的序文。1924年,亚东书局出版了赵诚之翻译的《普希金小说集》。从这个时候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陆续地被介绍到我国来,他的诗歌作品的译本,也开始出现在报章刊物上。及至鲁迅先生1934年创办了《译文》杂志之后,除零星地介绍过他的作品之外,还出过几次关于他的特辑,使中国的读者更有可能经常读到普希金的作品。 直到目前为止,普希金的诗歌作品、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差不多全部有了中译,每一种作品都有几种译文。 在此可以顺便讲的,就是当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上海曾建立了他的铜像,但在上海沦陷期间,日寇把这个铜像盗走,这样直到1947年方重新兴建起来。诗人臧克家当时还写了《竖立了起来》一诗,来歌颂苏联雕刻家多玛加茲基新铸的普希金铜像。普希金的铜像在今天受到上海市民的热爱,它不仅成为上海的文化胜地之一,同时也成为中苏友好的最好的象征。 (摘自戈宝权《普希金和中国》,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04期,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