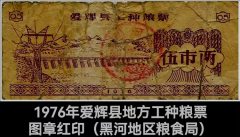“种瓜得瓜”的故事
来源:马苏龙 作者:马苏龙 时间:2024-10-21 点击:
(在爱辉公社三好二队下乡期间,曾担任过几年保管员;并参与生产队的经济作物经营管理。今看到群友转发的三好供销社旧址的视频,不禁回想起当年与供销社的交往。今儿翻出一篇十多年的拙文来,不怕大伙儿见笑,权作为“情系瑷珲”的回顾。不当,指正。)

“种瓜得瓜”原为佛教语,比喻因果报应关系。后比喻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儿要讲种瓜的故事,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且听慢慢道来。
每当在莱市场看到南瓜,总不由地想起七十年代初在黑龙江畔的边境小屯一一爱辉县西三道沟农村下乡时的倭瓜。
那时每户社员家的自留地都种些倭瓜,生产队也因养猪需猪饲料及要完成一定的倭瓜籽缴售任务,每年要种几垧地的倭瓜。
我原以为倭瓜与南方的南瓜是两个瓜种,其实它俩为同一品种,属葫芦种类,一年生蔓生草本植物,果肉和瓜子均可食用,有补中益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只是因产地不同而叫法各异。据有关资料称,南瓜是明代从西方引进种植的,在南方是长形的称为长瓜;而在北方则是扁圆矮型的,因当时矮和倭为同义而不同字,故北方称为倭瓜。我们下乡地的倭瓜主要是扁圆型的,因受到光照时间长的影响,皮硬肉厚籽少,又绵又甜,刚成熟时水分少,蒸吃有些噎人,放几天后增了甜,蒸吃时有一种栗子感的甜绵味,是非常好的辅助健康食品。当年红军在井冈,“红米饭、南瓜汤”;三年自然灾害其间南方以薯代粮,北方则倭瓜也救了大驾。倭瓜籽是相当有名的土特产,也称白瓜籽,个大、肉厚、味香,当年知青回沪探亲都要带上不少的倭瓜籽,南方人看到这么个大香浓的白瓜籽,都觉得稀罕。
1974年初我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兼管一些非主业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管理。这年开春到种倭瓜时节,我请土改时的老支书吕盘贵(即吕翠英大夫的父亲),由他领着七、八个上不了大田的二三线老社员,负责包括倭瓜在内的经济作物种植。既发挥老农丰富的生产经验,又解决他们出勤生计,我还落下个好人缘(老农在村里都有辈分,对他们合理安排可缓解不少矛盾)。这些老农对黑土地确实有感情,倭瓜的种植、锄草、施肥、压蔓、掐尖、授粉等每个环节都认真负责;我时不时也要“装”得像回事似的,到田头看看长势,与他们唠唠生产,对合理化建议给予支持,也了解了不少农业知识。老农告诉我:今年生产队安排知青戈榕养了十几箱蜜蜂,这小蜜蜂也帮着传授不少花粉,今年倭瓜指定能丰收。
到了上秋瓜熟蒂落时,只见地里青中夾红一大片倭瓜。原先估产能有十五万市斤,没呈想实际二十万市斤也不止。这分倭瓜可犯了愁了,如照以往分给社员按2分钱/斤扣款倒也省心。可这倭瓜籽当时是国家外贸收购的重要农副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香港换取外汇(日本点名要黑龙江爱辉的白瓜籽)。往年,那个头不高、干练而负责的三好供销社主任徐荣旺背着麻袋提着称的挨户上门收购,因群众自主处理,资源流失不少,费劲巴拉也划拉不到多少。为了支援国家外贸出口,队委会决定倭瓜分到各户,籽儿按一等品上交供销社,只要缴足任务,多余的瓜籽归己,倭瓜自留不收钱;不能按数缴籽,三倍扣款。但倭瓜出籽率多少以前谁也没谱。我随机称了三堆各100斤倭瓜,开瓜、掏瓤、洗籽,二堆瓜籽放在河南猪号由魏学芝、徐荣银两位很踏实的社员负责炕干,另一堆放在学校宿住的五保户(名记不上了)处。结果平均出籽率3.12%,即100斤倭瓜出瓜籽3.12市斤。做事要留有余地,决定分给社员100斤倭瓜按3斤籽缴供销社,余者归己。按每个家庭的每个劳力分200斤,非劳力100斤;倭瓜还是好的猪饲料,各户养的老母猪按300斤/头,肉猪200斤/头,仔猪100斤/头;这样各户都分到少者上千斤,多者数千斤。
倭瓜分到各户后,把大伙儿忙得屁颠屁颠的,紧着掏籽、洗净炕干后送三好供销社。供销社设在三好四队,也是三好大队所在地;往东三华里是一队高岗屯,往西四华里是二队西三道沟,往北过一片桦树林即三队北新村;四队在居中,也称腰屯。供销社原是间茅草顶的土坯子房,每年秋天都要抹一遍泥,否则墙缝里针尖大的眼会漏进斗大的风。1974年在原址西边新盖了砖垒的供销社,当时在屯子里看上去是座挺有派也挺扎眼的建筑。12月中旬已冰封下雪两月,快近年底结算,我到供销社一统计,全村80多户基本完成缴籽计划;当时有2户略欠点,以后也完成了。往年供销社在所属的四个生产队能收20来麻袋白瓜籽就不错了(一袋130市斤左右),这年光咱西三道沟送缴的就有40多麻袋,还全是一等品。这把徐荣旺主任乐得嘴巴像开瓢,看到我说,这几天二队社员拉着装瓜籽的小爬犁,像穿梭似的“嗖嗖”往这送,合着咱这新盖的供销社要兴旺。可别说,徐主任真获得那年度省劳模称号,还出席过全国财贸战线代表大会,记得1975年底升调到公社供销社去当主任了。
社员们也高兴得直蹦高。大部分社员不仅完成而且超额,超额部分供销社当场按质论价兑现(每斤一等0.59元、二等0.54元),或兑换些酱醋盐等生活日用品;不少社员除了留足自用外还加工成倭瓜条,当时这是备战备荒物资,晾干后供销社收购价0.26元/斤。记得木匠张庆元告诉我,他家共分3700斤,应缴111斤,实出籽120斤;不仅多了9斤籽的收入,还卖了200斤倭瓜条,一冬猪饲料也有了保障(倭瓜加豆粕杂粮煮的猪饲料,猪肉忒香)。这从大而言是支援了国家建设,从个人而言对社员又增加了收益。生产队出纳员张立建把缴售的瓜籽款从供销社算回来,一核算,扣除各项生产费用不仅略有盈余,还留有上万斤的猪饲料。应着当时的进步话一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都兼顾,尤其还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把邻村的社员羡慕得,在供销社看见我使劲地“忽悠”,道:还是你们西三道沟啊,路线正确!五十年前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当时,腰屯的生产队长是上海知青杨晓沪,他闻讯后特意找我了解这措施,后来也“比着葫芦画瓢”运用了这个定额管理的方法。
现今南瓜的作用正在被积极开发,有说是绿色健康食品,有说是可以防止糖尿病;南瓜子也铺天盖地哪个超市都有卖。可我总也忘不了当年那粉绵绵的老倭瓜,和现在南瓜籽没法比的个儿大肉儿香的倭瓜籽。
“种瓜得瓜”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成语体现了生物学的自然规律,即种什么籽种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层面,它也提醒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最终会导致相应的结果。
知青马苏龙
原撰于 2011—04—07
2024—09—10又改之
责任编辑:日升
“种瓜得瓜”的故事
马苏龙

马苏龙


“种瓜得瓜”原为佛教语,比喻因果报应关系。后比喻做了什么事,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儿要讲种瓜的故事,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且听慢慢道来。
每当在莱市场看到南瓜,总不由地想起七十年代初在黑龙江畔的边境小屯一一爱辉县西三道沟农村下乡时的倭瓜。
那时每户社员家的自留地都种些倭瓜,生产队也因养猪需猪饲料及要完成一定的倭瓜籽缴售任务,每年要种几垧地的倭瓜。
我原以为倭瓜与南方的南瓜是两个瓜种,其实它俩为同一品种,属葫芦种类,一年生蔓生草本植物,果肉和瓜子均可食用,有补中益气、润肺化痰的作用,只是因产地不同而叫法各异。据有关资料称,南瓜是明代从西方引进种植的,在南方是长形的称为长瓜;而在北方则是扁圆矮型的,因当时矮和倭为同义而不同字,故北方称为倭瓜。我们下乡地的倭瓜主要是扁圆型的,因受到光照时间长的影响,皮硬肉厚籽少,又绵又甜,刚成熟时水分少,蒸吃有些噎人,放几天后增了甜,蒸吃时有一种栗子感的甜绵味,是非常好的辅助健康食品。当年红军在井冈,“红米饭、南瓜汤”;三年自然灾害其间南方以薯代粮,北方则倭瓜也救了大驾。倭瓜籽是相当有名的土特产,也称白瓜籽,个大、肉厚、味香,当年知青回沪探亲都要带上不少的倭瓜籽,南方人看到这么个大香浓的白瓜籽,都觉得稀罕。
1974年初我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兼管一些非主业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管理。这年开春到种倭瓜时节,我请土改时的老支书吕盘贵(即吕翠英大夫的父亲),由他领着七、八个上不了大田的二三线老社员,负责包括倭瓜在内的经济作物种植。既发挥老农丰富的生产经验,又解决他们出勤生计,我还落下个好人缘(老农在村里都有辈分,对他们合理安排可缓解不少矛盾)。这些老农对黑土地确实有感情,倭瓜的种植、锄草、施肥、压蔓、掐尖、授粉等每个环节都认真负责;我时不时也要“装”得像回事似的,到田头看看长势,与他们唠唠生产,对合理化建议给予支持,也了解了不少农业知识。老农告诉我:今年生产队安排知青戈榕养了十几箱蜜蜂,这小蜜蜂也帮着传授不少花粉,今年倭瓜指定能丰收。
到了上秋瓜熟蒂落时,只见地里青中夾红一大片倭瓜。原先估产能有十五万市斤,没呈想实际二十万市斤也不止。这分倭瓜可犯了愁了,如照以往分给社员按2分钱/斤扣款倒也省心。可这倭瓜籽当时是国家外贸收购的重要农副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香港换取外汇(日本点名要黑龙江爱辉的白瓜籽)。往年,那个头不高、干练而负责的三好供销社主任徐荣旺背着麻袋提着称的挨户上门收购,因群众自主处理,资源流失不少,费劲巴拉也划拉不到多少。为了支援国家外贸出口,队委会决定倭瓜分到各户,籽儿按一等品上交供销社,只要缴足任务,多余的瓜籽归己,倭瓜自留不收钱;不能按数缴籽,三倍扣款。但倭瓜出籽率多少以前谁也没谱。我随机称了三堆各100斤倭瓜,开瓜、掏瓤、洗籽,二堆瓜籽放在河南猪号由魏学芝、徐荣银两位很踏实的社员负责炕干,另一堆放在学校宿住的五保户(名记不上了)处。结果平均出籽率3.12%,即100斤倭瓜出瓜籽3.12市斤。做事要留有余地,决定分给社员100斤倭瓜按3斤籽缴供销社,余者归己。按每个家庭的每个劳力分200斤,非劳力100斤;倭瓜还是好的猪饲料,各户养的老母猪按300斤/头,肉猪200斤/头,仔猪100斤/头;这样各户都分到少者上千斤,多者数千斤。
倭瓜分到各户后,把大伙儿忙得屁颠屁颠的,紧着掏籽、洗净炕干后送三好供销社。供销社设在三好四队,也是三好大队所在地;往东三华里是一队高岗屯,往西四华里是二队西三道沟,往北过一片桦树林即三队北新村;四队在居中,也称腰屯。供销社原是间茅草顶的土坯子房,每年秋天都要抹一遍泥,否则墙缝里针尖大的眼会漏进斗大的风。1974年在原址西边新盖了砖垒的供销社,当时在屯子里看上去是座挺有派也挺扎眼的建筑。12月中旬已冰封下雪两月,快近年底结算,我到供销社一统计,全村80多户基本完成缴籽计划;当时有2户略欠点,以后也完成了。往年供销社在所属的四个生产队能收20来麻袋白瓜籽就不错了(一袋130市斤左右),这年光咱西三道沟送缴的就有40多麻袋,还全是一等品。这把徐荣旺主任乐得嘴巴像开瓢,看到我说,这几天二队社员拉着装瓜籽的小爬犁,像穿梭似的“嗖嗖”往这送,合着咱这新盖的供销社要兴旺。可别说,徐主任真获得那年度省劳模称号,还出席过全国财贸战线代表大会,记得1975年底升调到公社供销社去当主任了。
社员们也高兴得直蹦高。大部分社员不仅完成而且超额,超额部分供销社当场按质论价兑现(每斤一等0.59元、二等0.54元),或兑换些酱醋盐等生活日用品;不少社员除了留足自用外还加工成倭瓜条,当时这是备战备荒物资,晾干后供销社收购价0.26元/斤。记得木匠张庆元告诉我,他家共分3700斤,应缴111斤,实出籽120斤;不仅多了9斤籽的收入,还卖了200斤倭瓜条,一冬猪饲料也有了保障(倭瓜加豆粕杂粮煮的猪饲料,猪肉忒香)。这从大而言是支援了国家建设,从个人而言对社员又增加了收益。生产队出纳员张立建把缴售的瓜籽款从供销社算回来,一核算,扣除各项生产费用不仅略有盈余,还留有上万斤的猪饲料。应着当时的进步话一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都兼顾,尤其还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把邻村的社员羡慕得,在供销社看见我使劲地“忽悠”,道:还是你们西三道沟啊,路线正确!五十年前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当时,腰屯的生产队长是上海知青杨晓沪,他闻讯后特意找我了解这措施,后来也“比着葫芦画瓢”运用了这个定额管理的方法。
现今南瓜的作用正在被积极开发,有说是绿色健康食品,有说是可以防止糖尿病;南瓜子也铺天盖地哪个超市都有卖。可我总也忘不了当年那粉绵绵的老倭瓜,和现在南瓜籽没法比的个儿大肉儿香的倭瓜籽。
“种瓜得瓜”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成语体现了生物学的自然规律,即种什么籽种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层面,它也提醒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最终会导致相应的结果。
知青马苏龙
原撰于 2011—04—07
2024—09—10又改之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