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与整理——一个民国文献工作者的一些零碎感想
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刘福春 时间:2024-07-23 点击:

民国文学(主要指1949年前的文学,也称现代文学或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近些年,诗歌界又在迎接新诗百年的到来,出书、研讨,一个接着一个,热闹空前。一百年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讲可能是个节日,可对我们文学史研究者,特别是民国文献工作者来说,恐怕并不值得那么兴奋。一百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一、我们赖以生存的书报刊这些纸质文本,因为纸张酸性强,脆化、老化加剧,已经基本临近阅读、使用的极限;第二、随着一批批老作家和老文学工作者的故去,那些存活在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头脑中的鲜活的历史永远无法打捞。
2005年2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目前中度以上破损已达90%以上,民国初年的文献已100%破损,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一触即破,濒于毁灭。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讲:“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许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遗书,却看不到民国的书刊”。
近些年各地不断举行作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及以前从事文学工作的前辈均已超过了100岁,基本都已离我们而去。鲁迅生于1881年,今年应举行诞辰135周年的纪念会;胡适生于1891年,今年该纪念他诞辰125周年。那些长寿老人,冰心生于1900年,卒于1999年,离世已经17年;臧克家1905年生,2004年逝世,已经告别12年;最长寿的章克标,1900年生,108岁过世,也已经走了8年。到现在,1940年代的作家还有一些健在,但也不是很多。有影响的“九叶”诗人中健在的只有一叶,郑敏先生也已96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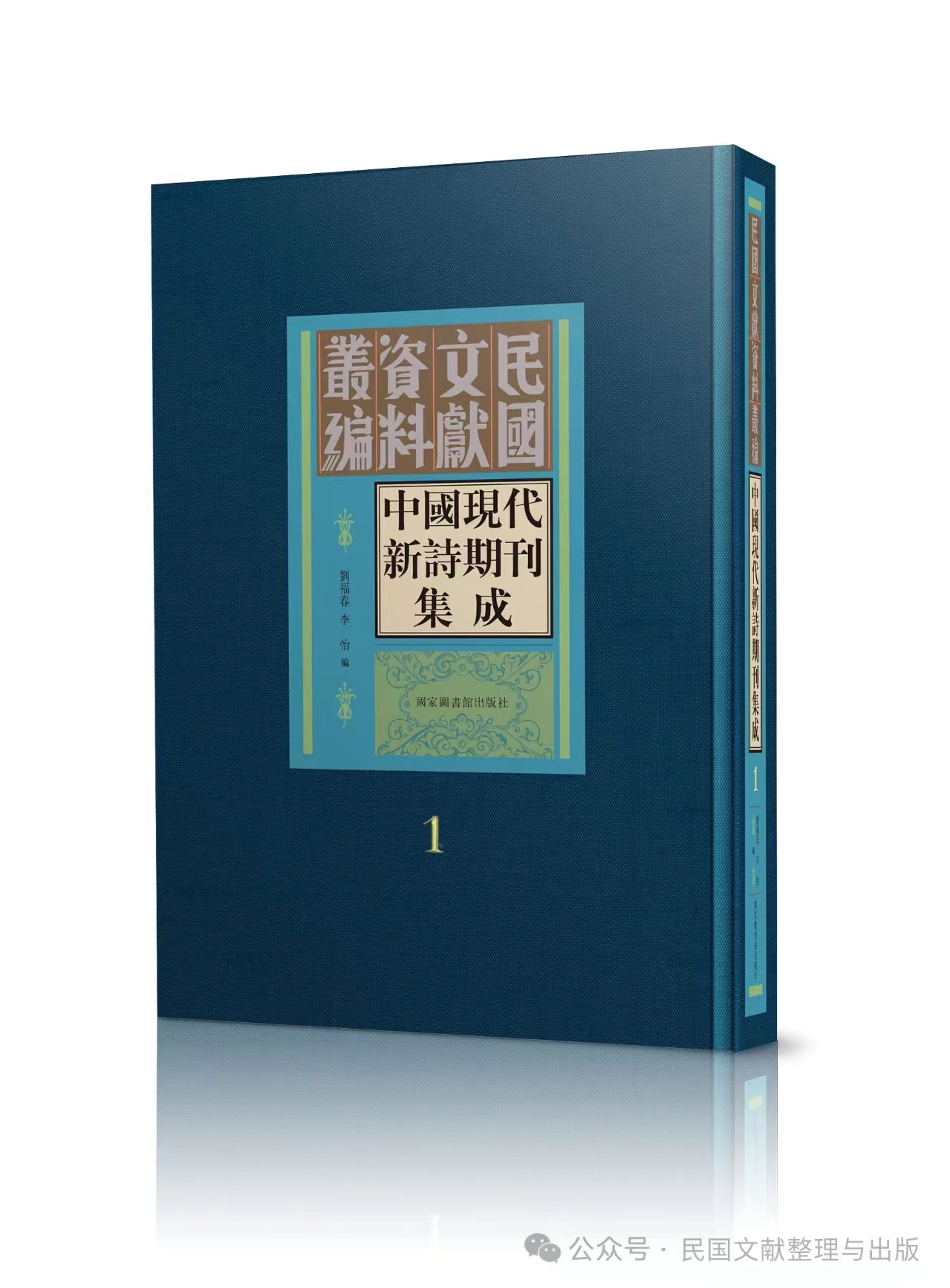
《诗歌与木刻》第九期,选自《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第二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有一事感受很深,以前专门写过文章,这次还要提起。二十几年前,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署名李邨哲的新诗集《黑人》。“李邨哲”是舒群用过的名字,而“黑人”也是他用过的一个笔名,于是我推测这是舒群的诗集。但从所见到的舒群研究资料来看,似乎从没有提到过他有诗集出版,于是我作了详细的笔记,准备当面向舒群请教。可是当我敲开舒群的家门时,舒群刚刚去世,问其亲属,都不很清楚。后来我写了《〈黑人〉——舒群的一本轶诗集》一文,考证出这确是舒群所作,但仍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如果稍早一点去见舒群可能问题就都能解决,只晚一点这些问题也许就成了永远的谜。
历史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
保护与使用
历史正在消失,文献的抢救迫在眉睫。
早在19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就提出“抢救”问题,针对的主要是健在的老作家、老文学工作者,而对损坏越来越严重的民国文献进行原生性保护与抢救的重视则是进入本世纪之后。
2005年2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67万件民国文献亟待保护》,同年7月14日《重庆商报》刊文《重庆图书馆民国文献损毁过半》,2007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告急《南图馆藏民国文献急需抢救》,2011年5月19日《光明日报》呼吁《快!抢救保护民国时期文献》。终于,“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省公共图书馆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得到中央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得到财政部2012和2013年度经费支持。”
对于亟待保护的民国文献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也使民国文献的使用者遇到了更大的困难。2011年9月1日《北京日报》刊文《民国文献:使用与保护的博弈》,文章讲:
南京图书馆也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5年前,那里只对那些有副本、目前保存条件还不错的文献提供阅览。然而,符合这样条件的文献微乎其微。而且,民国图书一般只对特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有限开放,且需要分管主任严格审批。如今,此类限制倒是取消了,“图书馆也免费开放了,可他们依然没有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为什么不能多投入一些人力物力改善书籍状况,而且也不是所有资料都进行了数字化。”网友“清风不识字”在“图书馆之家”论坛的发言引来众多跟帖,不少网友认为,公共服务型图书馆之路还很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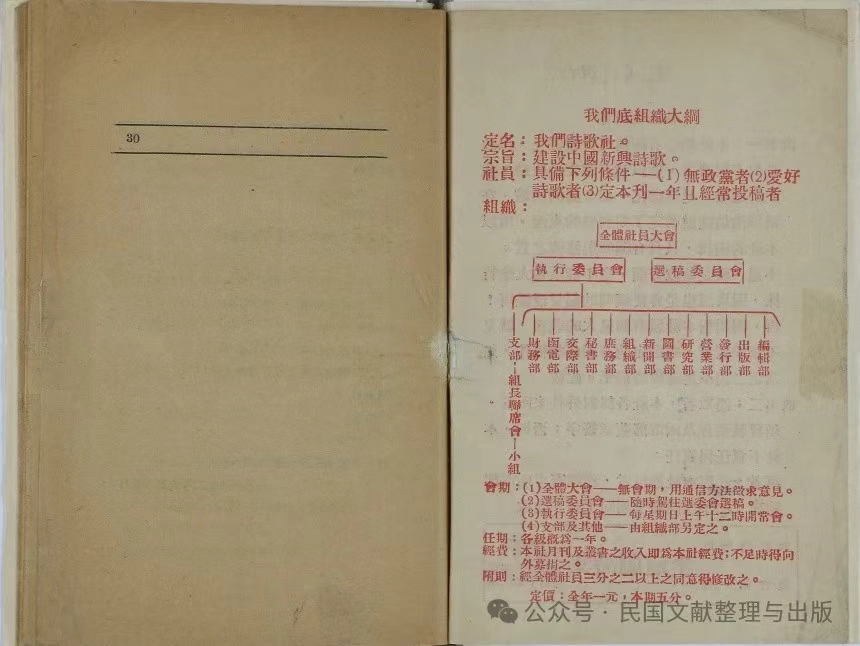
保护与使用的矛盾本来一直就存在,现今显得的更为突出。
更让人纠结的是,“抢救”和“整理”这一相关联的话题,却又显得十分矛盾,对于弱不禁风的民国文献来说,“整理”也是一次“损坏”。
好在图书馆在重视民国文献“原生性保护”的同时,还进行了“再生性保护”,主要是民国文献的缩微化或数字化。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Associative Library,CADAL),项目2002年开始建设,项目一期建设100 万册(件)数字资源,2009年8月项目二期正式立项,历经三年,新增数字资源150 万册(件)。
《诗前哨丛刊》第二辑,选自《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第二十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这些缩微化或数字化的民国文献,无疑为我们民国文学文献的整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还存在着多种不足。问题是,缩微化或数字化是否能完全代替纸质文本,怕的是这仿佛一座旋转的门,一面打开又一定是另一面的关闭,其结果可能是通向阅读原始文献的门以后很难再打开。
文献的热与冷
对于民国文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得还是比较早,并在1980 年代形成了热潮。
现在看来,1980 年代果真是民国文学文献收集整理的最辉煌时期,一大批现代文学研究者参与了这一工作,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79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并组织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加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乙丙三种。1978 年还创刊了《新文学史料》,专门刊登文学史料。
《诗号角》第五期,选自《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第三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北风诗刊》第一号,选自《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第二十九册
然而,1980年代后期和进入1990年代后这一热情渐渐变冷。
首先遇到的是出版困难。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例,这套资料汇编原计划有二百多种,实际出版不到100种,印数也不断下滑,《柯仲平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才印500册。有些资料已经编辑完成交给了出版社,但至今未能出书,其下落令人担忧。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参与者的减员。应该讲,对大多数原本重心就在“研究”的参与者来说,从未将所参与的史料整理工作当作主业,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编后记》就说,“这本《冰心研究资料》可算是我们写作《冰心评传》的副产品。”(《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观念”的不断强化,“不务正业”者越来越少。
进入本世纪,随着“学术规范”的强调,对民国文献史料的重视度大大提高,似乎文献史料导致了“学术的转向”并使之回到了中心。但粗略地考查可以看出,重视文献、利用文献者多,而具体做基础文献整理者少之又少。几年前,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料全编·现代卷》,我是组织者之一,特别想组织编辑出版一些新资料,结果只出了一种李怡、易彬编的《穆旦研究资料》,其他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重印。
当然这与我们组织不利有关系,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现今以论文为中心,不断量化的科研管理制度下,如果让一位研究者拿出几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文献的整理,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有人想做,现行的学术制度似乎也不允许。
尴尬的学术地位
经常会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从事文献整理并坚持到如今。我想来想去,只能回答是兴趣。也许这回答不够全面,但事实上并无大错,除了兴趣的满足,从事这一工作在学术方面还能得到什么呢
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面,民国基础文献史料成果学术地位不高或没有学术地位。在一般的观念中,民国文献工作还多作为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来对待。史料工作只是一般性的资料工作,没有进入学术研究范畴;成果一直属于一般性资料,不是研究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连工作量都不算。更加奇怪的,好像是此类工作越多离“研究”就越远,因此常常有人善意地劝我写文章,似乎只有写成文章我所做的工作才能提升到学术。
民国文献的重要性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文献整理工作的学术地位很低,根本无法与古典文献学科的地位相比。一般看来,民国文献工作只是服务于研究工作,本身还不构成研究,文献工作是简单而费力,有用而不讨好的不用脑的脑力劳动。因此,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都属于“著”,像孙楷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而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书目、年表之类则多为“编”,连“编著”都不敢署。
《不凋的花》,选自《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第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民国文献整理不能只靠兴趣来支撑,更要靠制度的保障。所以我一直呼吁,像古典文献学科那样,建立现当代文献学科。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障,才能使民国文献整理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和健康地发展。民国文献或现代文献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应该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史料工作已经能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且确有自己的研究范围、自己的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作为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而对于文献工作却未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理论的、思辨的、抽象的、概括的)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就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如果说研究工作是总结,是创新,文献工作则是发掘,是求真。研究工作与文献工作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没有文献工作,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和深入;没有研究工作的带动,文献工作也失去了最终意义。或者将文献工作称之为基础研究可能更合适一些。
从某种意义讲,文献工作标志着一个研究学科的成熟。这话听起来也许不够严密,我这里想讲的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对文献的强调。比如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成熟学科,它的研究要求基本上不能有文献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说的“硬伤”;而在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篇论文、一本研究著作有几条或者十几条文献史料错误是常见的,也并不因此妨碍其成为有影响的著作。
在很多领域已经难于达到“真实”的高度的时候,而“真实”对文献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底线。在现今信誉普遍缺失的年代,文献工作从事的是可信的工作。
文献工作也是一种学术品格的表现。收集文献要锲而不舍,整理史料又要耐心细致。从事这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一坐就要几年、十几年或更多,这在现今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是一种学术品格的修炼。这工作是成书难、出版难,而出版了学术评价又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辛勤的开垦者,没有一份热爱之心是坚持不住的。但愿民国文献的整理工作能够吸引来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做,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作者刘福春简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任韩国东亚大学招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史研究和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收藏有大量诗集、诗刊、书信等新诗文献。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寻诗散录》《中国新诗编年史》等学术著作,编有《中国现代诗论》《新诗名家手稿》《冯至全集(诗歌卷)》《红卫兵诗选》《牛汉诗文集》《曹辛之集》《谢冕编年文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等。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