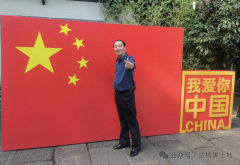我心永恒
来源:古城旧梦 作者:徐明华 时间:2023-08-07 点击:

今夜无眠。
白昼的喧嚣潮水般退去。夜静如水,夜是沉思的摇篮。灯光如雪,我凝眸着一张发黄而褪色的照片,是找回那尘封的记忆么?
这是一张 50多年前的照片。在层峦叠嶂、茅舍草房的背景下,是我与所在的五七连五好战士的合影。51个从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识青年,像我一样青春年少,稚嫩嫩的脸,稚嫩嫩的身骨……
凝注这一张照片,我能感受到当年下放的知青彼此的呼吸与心语,还有那昨日溅落的风雨,流洒的汗水与咸湿的泥土芳香;从生命的源头,探寻到我们的青春与事业的活水激流,从氤氲着的苦涩与凄美,庄严与鲜活之中,看见了张扬在人生之旅的血与魂,力与魄。

“东方红406号”一艘巨大的客轮,缓缓驶离了黄浦江畔。于是最初的失落与困惑也就伴随而生。船上有千余名上海籍下放江西的知青,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曾吟哦过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也高呼过“上山下乡,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当在熟悉的这块土地与亲人分别,就在那一瞬间,船上的人与岸上的人,有的掩面而泣,有的眼含泪水,有的默然伫立。
此一去山高路远,彼此何时才能相见?
这是1970年4月6日。这一年我17岁。
沿途旖旎的风光,我无心观赏,只有大江的波涛在撞击我的心。船逆水而上,艰难的行驶,好不容易到了九江。然后,我们坐上解放牌货车,一路在山间颠簸。大山,青黛如染,蜿蜒起伏,我第一次看见大山的雄伟与险峻。山雨倾盆而下,扑打着车篷,发出一阵阵钝响,我的心仿佛被雨打湿了。
与我同车的知青,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睁大吃惊的眼睛,加上一路颠簸,晕车了,我们难受地呕吐,翻江倒海般的呕吐。紧接着,更大的磨难在考验我们——车经过武宁,谁知桥被山洪冲断,我们只有等人来接。天色已暗,大山沟里春寒料峭,风呜呜地叫,还有野兽蹲在暗处干号,令人毛骨悚然。又冷又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艰辛和危难。

突然,我望见了河上的灯光在夜海沉浮,紧接着听见一阵“咿咿呀呀”的桨声。当地乡亲穿着蓑衣、划着船,提着马灯来接我们了,他们的全身被雨水打得精湿。我望着他们,生命的感动油然而生。
我们20个知青分在修水县马坳公社三忠(现为马桥)大队的雷峰尖村,这里的大山绵延仿佛没有尽头,树木翠盖倚云。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财富,全村都穷,土砖房又矮又潮湿,我就住在一个姓阮的老人家里。他空出两间房,没有床,没有凳,我内心如泼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当面前所发生的一切,令我困扰外,更多的是深深的感动和敬仰。仿佛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世间的许多道理。我的房东,叫来几个人,把几截粗大的寿木抬出门外,拉动锯子,一会儿简易的床和凳子做好了,我忍不住心头一热,两行热泪滚滚而出。根据当地习俗,这里的人一到45岁就添置寿木,寿木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闻着床上散发出木质的香味,我懂得了什么是人间的真情真爱。这种情爱不经雕琢,质朴、纯洁、自然。

我的疾苦,与农民相比,又算什么?
赤日炎炎,下到水田割禾打禾,仿佛在经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水田被烈日晒得冒出热泡,烫得脚揪心的难受;头上就像顶着一个大火炉,热得汗水淋淋。割禾割得手指流血,打禾打得手指充血全烂了,汗水、泥水、血水流在一起,依然要挺起腰杆,不能趴下。更可怕的是水蚂蟥,这家伙一听到水响就游将过来,叮住人的皮肤吸血,恐怖极了。
我本来就单瘦,也从未经受过这种苦役,加上水田不服,腿烂了,溃疡红肿。乡亲们知道后,采来草药。精心给我治疗。至今还留下了疤痕。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早春。天下着连绵细雨,无休无止,料峭的寒风侵人肌骨。我又累又饿又冷,病倒在床,发着高烧。我这时的房东是位70多岁的大娘,她颤巍巍来到我的床边,拿着一个白生生的红薯说,孩子你吃吧,吃了红薯病就会好起来的。

二
我站在这块土地上,仿佛像我的祖祖辈辈一样,生存了几万万年。我感受到土地的博大、坚实和厚重,更感受到父老兄弟的无私、淳朴和慈祥。
这种生命的体验,从我到大山砍柴迷路开始的。
天未亮,我与几个知青到雷峰尖砍柴。这是一座大山,高而陡,险而峻,丛林莽莽,幽谷深深。爬了几十里山路,累得精疲力竭,还不能歇下来。来回路途远而险,一耽误时辰,天黑一迷路,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然而,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们在棘莽杂木间砍伐,好不容易每人砍了一担柴,返回时迷路了。我们东转西转,总也转不出丛林。天色昏暗下来,我的肩膀被沉甸甸的柴担压出了斑斑血迹,能见度极低,到处是黑压压一片。不远处,野兽的嚎叫极为恐怖,我们已经虚汗淋淋。
我们惟一的希望是走出大山,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我睁大一双惊悸的眼睛,往返逡巡,心跳加快,我不敢想像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仿佛觉得生命之弦脆弱得一下子会绷断。
忽然,我们听到了一阵“呜——”的声音,就像从天外传来,在山间回响。我太熟悉这种以呼声唤人的声音,那么亲切、浑厚,在静夜里穿透力极强,渗透了人间的真情厚爱。于是,我们也喊出一阵“呜——”的声音,声音相接,愈来愈近,终于我们看见了父老乡亲一路跑来,我们紧紧抱住他们,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块土地的人哺育了我,教会了我,启迪了我。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其残酷程度,却远远超乎我的想像。
那是1970年的冬天,也是我下放的第一年。山上的风奇冷奇大,整日里呼啸如鬼喊狼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火辣辣疼痛。嘴唇干裂,皮肤粗糙,还要挑着沉甸甸的土来回奔跑,肩膀上血肉模糊,又红又肿,直痛得钻心的难受。每挑一担土,就像在挑一座大山;每走一步,就像在爬一座高坡。我知道,一旦停下来,就会寸步难行,自己也将会被自己击垮。
一到晚上,总希望漫漫长夜早点过去。我们栖身的工棚,是用冬茅草盖起来的,百孔千疮,怎能抵御住料峭寒风寒流侵人?几十个人住在一个茅棚里,奇冷,相互身挨着身取暖。我们吃的是南瓜饭,肚子常饿得咕咕直叫,实在不行了,就喝点凉水填饱肚子。我就这样在工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夜。
春节到了,我与工地上的知青真想回去与亲人团聚。然而,工地正在修建的节骨眼上,我们的奢望难以实现。这里没有除旧布迎新热闹的鞭炮声,也没有鸡鸭鱼肉的一饱口福,有的是忆苦餐,有的是豪言壮语。
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浮动着一层层野菜,野菜生涩,绿汁苦如黄连。我们连菜带汁吞下,然后表决心,诉衷肠,大有一副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然而,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和其他的知识青年一样,一想到家中的亲人,不免眼圈一红;但看到堤坝一层层在加高,又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种朴质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毕竟,我们付出过,奋斗过,把血和汗洒在这块土地上,以回报这块土地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
三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我选择了修水;那么90代修水选择了我。20年后,与我一道下放到修水县的知识青年,一个个都走了,而我却留下来了,后来担任了修水县县委书记。
我的生命在这一片红土地浸泡过,我与父老乡亲有一种血肉之情。他们就像一轮明月、一轮太阳,照亮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
我再一次来到了雷峰尖村。20年后,我的老房东已经作古,坟上长满萋萋青草。我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虽然是那饱经风霜的脸,虽然住的是那简陋的土砖房,但是谈吐之中,他们频频流露出自信的笑靥。我明白了,这笑靥已表明乡亲们正在向困惑了这块土地多少年、多少代的一个“穷”字挑战。
这一回,乡亲们在饭甑中蒸了米饭,还有鲜香的小虾下饭。我看见几个孩子吃着热腾腾白花花的米饭,笑得像蜜一样甜。我的脸上也溢出甜甜的笑,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回响:农民,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他们是那么朴质,仿佛能够有饭吃,有衣穿就满足了。他们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感召了我。
我愧疚于这块土地,我欠了一笔巨大的感情债,他们是我们头上的天,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只是他们的“公仆”,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以回报这块土地。
我在沉思,我在扪心自问。

这时,乡亲们向我围了过来,指着面前的一条无名小溪,向我欲言突止。这条小溪,距我原来住的地方20多米,我曾在小溪洗澡洗衣服摸鱼虾,这里有过我的忧愁和欢笑。
最后,我才知道,他们向我提出修一座石桥。紧接着,我从他们的言辞和眼光中读到了一个久蓄的愿望:以前太穷,现在有了变化,你是县委书记,带领我们在这块红土地上富起来。
我的心里产生巨大的共鸣,压力很大。我在修水24年,红土地的每一点变化牵动我的心,红土地的情结已融人到我的血液之中,我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这是他们久蓄的愿望,我默然同意,我不但要修一座石桥,还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我要为这块土地修一条通向致富的五彩路。否则,我的灵魂一辈子不能安宁。
我带着深情和希望回到了县委机关。
坐在办公室,我处理一封封群众来信,这是我当书记以来多年的习惯。至今,经我之手处理的群众来信成千上万,我以为这样才能直接了解百姓所急所需所苦。农民的一些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是小事,对他们可就是大事。我感受到,总有一双双深情的眼睛在望着我,我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我以热情与理智审视这块红土地。于是我带领县委一班人,走村串户,脚步踏遍山山水水,广泛地调查研究,探索着一条致富之路。
就在我们来到山村时,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们。
一家家农户,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地握住一个个木槌,来回而艰难地舂米,额上的汗水涔涔,沉重的春米声重锤般在锤打着我的心。一到夜晚,农家以松树片插在墙上作照明用,昏暗的光在摇曳,油烟味呛得人咳嗽不已,我的心被灼痛了。
解决缺电少电,乃是当务之急。
于是,我与县委一班人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决定水电工程重新上马。同时,我们采用了东电西送的方案。修水县面积4500 平方公里,是江西最大的县,我们筹措资金上千万元,三年后解决了贫困山区30多万人的生活用电;我们还提出了“四个一”工程,即一根丝、一杯茶、一把土、一棵树。
一根丝:发展蚕桑缫丝,使修水县成为江西最大的蚕桑和缫丝基地;
一杯茶:根据山多茶叶多的特点,发展特种茶,从而使生产保健茶的宁红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保健茶基地;
一把土:充分利用磁泥的自然资源,生产和发展高温瓷产品;
一棵树:发展板栗树这一独具地方特色的经济果林。
当我又一次来到下放的地方,乡亲们亲热地叫我“徐家崽”,他们视我为贵宾,用“哨子”来招待我。这“哨子”用红薯粉或包腊肉,或包冬笋、大蒜,或包红糖芝麻。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苦涩的痕迹,目光里溢满着幸福和欢乐。
我听见了他们告别贫穷,走向富裕的大踏步前进的步伐声。
我看见了一条条平坦的油路纵横交错,红砖楼房鳞次栉比,山青了,水秀了,人欢
我知道,这块渗透革命先烈鲜血和乡亲们汗水的红土地,像一只火凤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涅槃。
还有什么比这使我更引以欣慰的呢?
近代学者王国维对做学问提出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进入这三种境界,学业有成;做人干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命的体验告诉我,只要你身系红土地,与父老乡亲真情相对,苦乐共享,你的生命之光才会辉煌灿烂。无论你在任何时候,无论你的官职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要始终不渝地奉守这一信条:当官为了百姓谋福利,干事不是为了当官,做一个人民的“公仆”,我心永恒。
今夜无眠。
回忆是苦涩的,也是甜蜜的。我眼前这一张发黄而褪色的照片,就像一叶赭色的风帆;我和其他的知识青年一样,走过风雨走过苦涩走向欢乐走向未来,照片上的人现在有的成了干部、医生、学者、教授、企业家等等,我成了一个领导干部。
我在湘南的这座“雁城”极目远望,目光游弋于八方四面,神思翱翔于天地之间,我灵魂的一羽依然栖息在那一片红土地上,我永远拥有对红土地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我真诚为父老乡亲祈祷,祝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鼎新革旧,扬清涤浊,走向明天。
明天会美好而灿烂。

晓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