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逝世30周年祭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葛维樱 时间:2022-11-18 点击:

路遥的作品历经数十年依然能够感动中国人,但43岁英年早逝,他本人的人生和世界却始终呈现出“谜”的状态。我们尽力在解谜的路径中,理解路遥。
“强人”生长
在曹谷溪心里,路遥永远是1970年盛夏的样子。“我29岁,他21岁,一起骑一辆再少一个零件就没法走的破车,去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两个人站在黄河边上笑得咧开大嘴,戴白帽子的路遥扶着刚跳过来的曹谷溪的肩膀,三脚架上的相机帮他们自动合影一张。
在路遥生命最后的71天,他要曹谷溪把这张照片放大,带去了西京医院相伴。今年75岁的曹谷溪要喜欢路遥的人去延川县那个2排18号窑洞看一看,并说“我给你报销路费”。他有事没事就去延安大学在文汇山给路遥建的墓地,点两根红塔山烟,对故人说“你一根,我一根”。
拍摄路遥长篇纪录片的导演田波也是陕北人,他对我说:路遥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他始终留着回家种庄稼的念想。路遥身世被渲染得过于苦难凄凉,往往忽略了他童话般瑰丽描写背后,实际上拥有童年快乐和家庭温情。他的生母马芝兰一生务农,2011年去世,不少人看望老人时都会留下一点慰问金。他的养母也就是大伯母叫李桂英,2004年2月去世,此前不到一年,延川县决定给李桂英每月补助150余元。这些细节往往令人感慨于路遥的文学成就没有太大地改善他的家庭境遇。80年代曹谷溪对路遥的“不孝”颇有指责之意。“我只对你说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说。我爱我的母亲,从内心到外在不比你少。”路遥写于1980年的长信里讲述了母亲的苦恼,也流露了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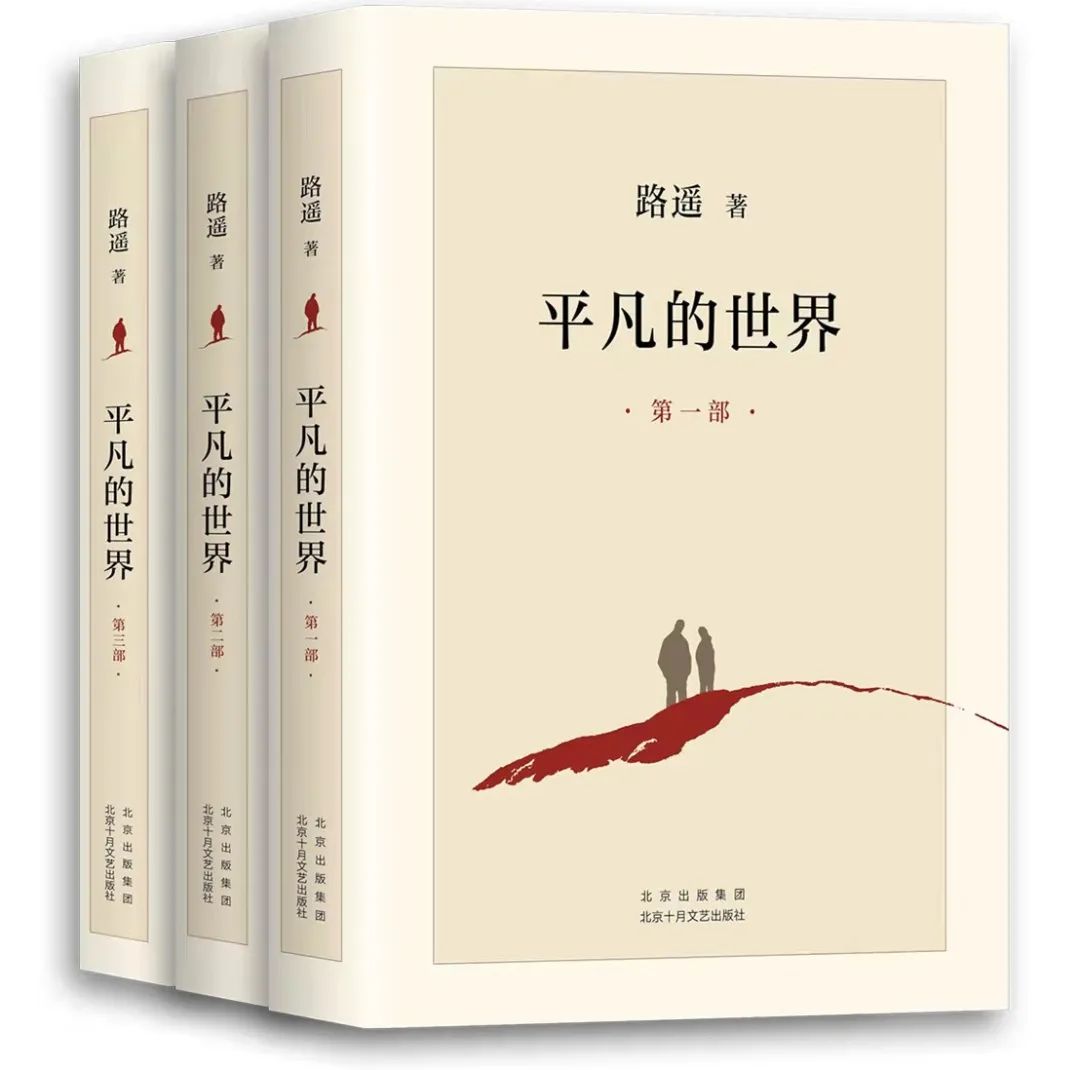
人人都知道路遥在8岁时被过继给了大伯家。路遥自己的文字描述得细密而痛苦。“母亲给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8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我一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溜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关于这段过继往事,他的小学同学海波讲得更客观,陕北民谚有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路遥作为长子在家庭中能够承担割草、放羊等劳动,被过继给大伯,无论感情还是理性,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路遥的亲生父母是清涧农民,家里孩子多,路遥后面活下来的有四个弟弟。生活贫困使亲生父亲一再要终止路遥上学,但路遥成年后却不忘父亲的能干,说是远远一看山坡,就知道哪片庄稼是父亲的杰作。但当时,“自己下地干活,看见同龄人上学就难过得想哭”。大伯一家没有生育,与奶奶住在延川县,虽然也是农民,让过继来的路遥上学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在朋友印象里,少年时的王卫国(路遥)虽然是“黄土坡上穿着个翻了毛的破棉袄一高一低走路”的样子,但他的强烈个性却是公认的。“他是孩子王。”海波说,而且他想当孩子王。路遥成名后曾带着贾平凹站在延川的一个山头上。“他指着山下的县城说:当年我穿着件破棉袄,但我在这里翻江倒海过,你信不!他把一块石头使劲向沟里扔去,沟畔里一群鸟便轰然而起。”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路遥的过继实现了他从农村到县城来上学的第一个人生转折。延川对于他出生的清涧,俨然已是一个县城。口音和外来移民的身份首先被嘲笑。从一开始路遥被欺负,大伯和大伯母还要拿着洋芋、萝卜去人家家里道歉,到路遥把村里的孩子全都收服了,只用了很短时间。路遥就此脱离了家庭的保护,开始用自己的能力生存。
路遥自己对于食物的贪婪描写有真实的自传性质。食堂如何分为甲乙丙三种饭,他为了吃一口白馍,曾在同学的欺辱中学狗叫。海波说,路遥属于延川小学的“半灶生”,住在学校,每周两次可以回家拿粮,喝熬锅水。带糠的食物进入热饭菜的大蒸笼后,要在饭铃打响时首先冲出去,才能确保自己拿得到食物,要不然“团粒结构”太松散,会污染其他人的细粮,再碰两下,拿都拿不住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饿并不只是路遥一个人的经验。他曾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里,描写马建强在县高中读书时饥饿贫困的生活,遭受的屈辱和自尊、自强的性格。日本研究者安本实认为这个人物能够折射路遥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这样写。
那不是一个物质匮乏击垮人的时代。贾平凹觉得路遥童年的贫困被过度解读,他说“那个时代人人都穷,也都不当一回事”。路遥去世时还留了1万块的外债,但这也不妨碍他到西安当时最好的凯悦酒店给女儿买60块钱的三明治。“他是一个强人。”少年时代的路遥已经有自己的取胜方式,他常到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去翻阅最新的报纸杂志,海波经常跟着路遥一起去。精神的匮乏导致延川中心小学里最有话语权的,都是常看电影的干部子女。一张一毛钱的电影票,普通干部的月薪大约30元,而一个农民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一毛钱。在人人羡慕电影的音乐、服饰和台词时,路遥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也看到了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后来有了他创作的主人公的“高加林”。这些新词汇、新理想让他很快就战胜了那个小学里的普遍价值观,不仅受到老师刮目相看,很多大人甚至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所以路遥后来每次快要失学,总有同学的家长拿出学费来资助他。他小学毕业时,大伯当时已经40多岁,作为最传统的农民,只想给14岁的路遥赶紧定亲,拒绝让他继续升中学。大伯觉得路遥“说起来精着哩,其实憨得什么也不懂”。路遥深信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到处寻求帮助,依靠村里书记刘俊宽给的两升黑豆,升入了延川县唯一的中学延川中学。
一种奋斗
安本实认为,路遥一生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转换为非农身份,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里奋斗。
1966年路遥初中毕业,考上西安石油化工学校,这原本是他终于以读书方式脱离农村的正路。当时人才紧缺,这个中专学校不仅会让他得到城镇户口,每个月还有补助,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然而,暑假“文革”开始,所有的初中生都回到原学校去参加,路遥回到延川中学。他从外地串联回来以后写大字报,其中有“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因为很欣赏这两句话,他一度将“冲天笑”作为自己的化名。他的三、四、五弟分别被他改名为王天云、王天乐、王天笑。在那个时代里,路遥的文采、出身和性格都促成他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也很快就下台了。“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埋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文革”中他还叫王卫国,作为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他出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所谓的“19岁就成了县团级”。另外“文革”中牵连他的武斗案,在32个证人的证实下,1969年查清与他无关。“‘文化大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斗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本和他分属两派,又化敌为友的曹谷溪,传说“文革”中得到了路遥的保护。“太夸张了。”曹谷溪对我说,“反正他没保护过我,有没有保护班主任、老师,我不知道。”曹谷溪和路遥相识在1969年。“1969年我刚从公社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当通讯干事。那一天他正好在我的房间里,军代表当着我的面宣布了路遥被免职的决定。”曹谷溪说。路遥回马泉营小学教了几个月语文,又被曹谷溪叫回延川县委。尽管受武斗案牵连,他从组织上还是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去“铜川二号信箱”,也就是保密工厂工作。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初恋林红。
路遥与林红
林红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关庄公社的前卢沟村插队。据回忆者介绍,她能歌善舞,小巧玲珑。林红第一次见到路遥,是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发言,她在台角喊口号,并没有后来人臆断的白富美和穷小子的地位差距。路遥喜欢下雪天沿河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喜欢大红衣服,都和林红有关。去了工厂的林红很快通过一个在内蒙古的朋友给路遥寄信,转达了分手之意。曹谷溪一辈子只见过路遥两次痛哭,一次就是这一天。海波说:“我11岁认识路遥,他是个多么骄傲、有个性的人。”海波和曹谷溪都对我说,很多年里,连林红这个名字都没有从路遥嘴里说过。

路遥与林达
养母李桂英曾说:“路遥上大学以后,完全是林达供着的。”1973年被延川县委书记申易推荐,路遥上了延安大学。林达是“很有才气的北京知青”,父亲曾担任廖承志的秘书,插队期间林达回厦门父母身边,报告了与路遥的恋爱情况。后来她在西安、北京工作,无论路遥生前身后,都尽量避开“路遥夫人”、“路遥遗孀”之类的名号。路遥去世后她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始终未曾辩白一句。这使真正亲近他们的朋友都对她非常尊重,多年前她已回到北京工作,和女儿路远(路茗茗)稳定生活。除了曾经与出版社打官司,希望纠正路遥生前签下的不合理合约,把稿费收入改为版税收入,这对母女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
林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曹谷溪手下做延川县委宣传部干事。“林达是参加知青招干考来的,路遥是农民身份,那几年我给他安排了在宣传部写文章的临时工作,可以拿误工补贴,一个月18.5元,但给林达开的工资和我自己一样高,都是38.85元。”曹谷溪本希望让路遥与林红重归于好,所以才把林红的同学、一样来自清华附中的林达调到了县革委会,让林达去做林红的工作,告诉她路遥多么好。结果曹谷溪却成就了这一对恋人,延川县委2号18排宿办合一的宿舍,见证了这段甜蜜的岁月。林达一件衣服几个季节都穿,却给路遥尽量穿得体面。俩人于1978年1月25日在延川县招待所结婚。“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18号这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他自己家。初一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曹谷溪说。

1975年路遥在延安大学读书期间,被抽调到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叶永梅在陕北插队后当兵,接的就是路遥的实习岗。同一时期的同事还有白描。1976年路遥正式调入西安任职编辑,但是他一生从未写过任何一篇以城市为背景的文章。他以一个农民视角,见证了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进程。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不仅没有走入1978到1980年的“伤痕”潮流,甚至不是以批判为主的。得了奖的路遥据说是“悄悄回到西安”,他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获得中国文学界的认可。
《人生》之后
1981年夏天的甘泉县招待所唯一的一间两个窑洞组成的套房,成了路遥用21天创作《人生》的地方。原来的题目叫《你得到了什么?》,而《人生》这个题目,是他和约稿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共同商量确定的。他著名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生活方式,几乎脱胎于此时。他喜欢投入沉重的劳动,觉得那21天是最美好的时光。每天18个小时的写作,小屋子烟雾弥漫,房门后簸箕里盛满烟头,桌上扔着硬馒头、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他头发蓬乱,眼角黏红。白描去看他时,他牙关紧咬地说自己是憋着劲来写的,“好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拼命”。路遥自述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很多当时见过他的人,都留下了他刷牙刷得“满嘴冒着血糊子”的印象,结果这个印象也成了他写的《人生》里刘巧珍为了让心上人喜欢,特意站在崖畔刷牙的情景,也同样是“满嘴血糊子”。
陈忠实曾经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前看到了《人生》,他说:“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人生》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
《人生》以最快速度改编为电影剧本,路遥成了最红火的文学明星。“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贾平凹回忆,1985年路遥担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月薪120元,已经不低。他的弟弟王天乐曾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当一个“白白胖胖”的文学编辑。他自述在家乡人眼中,官熬大了,地毯从家一直铺到机关门口,甚至用上了刻名字的金碗。“即使土地给了高加林痛苦,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他爱的人。”路遥让高加林回到土地,却并没有说要继续当一辈子农民。“即使想远走高飞不成,为什么一定要诅咒土地?”
“路遥这个人本身是复杂的。他的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在精神层面,他追求崇高、有理想的生活。但现实却不得不经历苦难的人生、纠结和痛苦,他挣的稿费都不够那些穷亲戚瓜分的。他的整个人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后来担任央广编辑的叶永梅,曾在1983年《人生》广播剧播出时到西安拜访路遥。路遥说自己要应对无数亲戚朋友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比如他的亲生父亲带来一堆乡亲要他解决的各种乡村问题。“亲戚,这个词至今一提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我曾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的口评论道:‘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结果“六亲不认,事也不办”就是他得到的评价。此外,他有四个弟弟,除去80年代初迁到延川替自己照顾大伯的三弟外,另外三个都被他帮助安排了工作。二弟招工,四弟做了记者,五弟比他小整整20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路遥还为五弟的工作到处求人。海波愤慨又伤感地对我说:“说路遥不帮人简直是……他连我都帮。”海波自己就是路遥一直帮助着走上了职业作家之路。
在经历社会开放的过程里,路遥敏感地感到了新时代的到来。很多人评价他用文学来实现政治抱负,实际上指的是《人生》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政策改变的政治背景中。在这一点上,路遥的志向是像柳青那样,写《创业史》的同时还写出来陕北山区农业经济的论文。高加林居住的村庄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由于“鸿沟”的阻碍,他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别一个世界上。和路遥一样,高加林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抱负跨越封闭的社会结构的壁垒。1976年拥有了城市身份后,路遥的写作目的更明确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写作野心。他拉贾平凹去家吃烩面片。“他削土豆皮很狠,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他的同事张艳茜回忆,1982年路遥开始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列了100多部的书单,用了一整年时间翻阅了近10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和《榆林报》,笔记做了几十本。曾任《陕西日报》记者的四弟王天乐是《平凡的世界》写作时期路遥最忠实的助手,他的回忆更生动:“第一个晚上,我们绘制了小说的地貌草图。从我的家乡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一直沿线绘制到西安钟楼。把这一线的山川河流,机场公路重要建筑等等全部描绘出来。我们的美术学的不好,画的图只有自己能看懂。路遥说,第一步工作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人物都要反复在这一地带走动。如果你不熟悉地形,你的人物一旦走动起来,作家的描写就十分困难。第二天晚上,列出人物表和地名表。为人物起名字,就把俩人难死了。把记忆中的名字讨论了无数遍。孙少平、孙少安、田福军、金光亮、金俊武,双水村、黄原地区、铜城等等人名和地名才写在纸上。剩下的时间就是讨论主人公在事件中怎样先进的问题。每一年、每一次发生了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一切工作都在万分激动的情绪中展开。每天只上街买一次吃的、喝的东西,一天就不出房门了。服务员看我们形迹可疑,五六人一起进来查了一回房间,一看没什么‘凶器’,也就放心了。真的,一个人假如真正地投入到你热爱的工作中,那是非常美好的。”后来路遥说自己写作以外的生活机能退化,像孩子一样,几乎完全靠弟弟长年的陪伴。
《平凡的世界》6年写作,基本都在陕北。他最重要作品都是脱胎于他自己生长的土地,曹谷溪和海波说并不仅仅因为那是崇尚文学的年代。从准备到写作到每一个人物原型,路遥与陕北的联系更像柳青说的:“咱们这个地方,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一天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题材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代的。”路遥开始了连家里出事都不会抽身的日子。“1975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时期的变化”是他的背景。“某一天半夜,我突然在床上想到了一个办法,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拉亮灯,只在床头边的纸上写了三个字:老鼠药。利用王满银贩老鼠药的事件解决了这一难题。大约用了7万字的篇幅,使全部主要的人物和全书近百个人物中的70多个人物都出现在读者面前。”而这件事据王天乐回忆,完全脱胎于他的亲生父亲因为砍树被捕的事件。
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被“新闻联播”要求播出3分钟的片子,他请记者到了长安县的柳青墓前,当时记者还为了不是黄土高坡而苦恼。“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舔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在感情上,他真心理解农民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指责、嘲笑甚至丑化他们”。1983年,路遥和王天乐到工地上打短工。“我和路遥一起来到延安东关,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扮成我当年揽工的样子,很快就被延安沟门的一个工头招去了。因为我当年揽工能吃苦,名声很好,所以工头一下就认出了我。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遥因干活不行,一共30元工钱,扣了路遥10元。我俩一共挣了50钱,跑到宾馆洗了个澡,赶快把衣服换过来,因为延安人熟,怕碰上熟人不好向人家解释。50元钱很有纪念意义,路遥说咱俩一起到邮局,把它寄给父亲。这时延川县来电报,说路遥的养父病重,可能不行了。养父就是我的大伯。路遥说,‘你回延川全权代我处理一切后事’。事实上后来养父逝世的前后,路遥一直没有见他。”此后他又去铜川鸭口煤矿、陈家山煤矿体验生活,和矿工同吃同住。一遍一遍地下井,而且要下到很深、很潮湿的地方去体验生活,有时他会堵住几个刚刚升井的矿工,为他们递上烟,点燃火,一起坐在阳光下闲聊,他必须熟悉煤矿井下井上的情况、矿工生活的习惯,以及矿工经常用的一些语言,甚至被熟人带着“惊险”地参观了当时省委书记的家。
白描和路遥一起带着稿子进京。“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当时路遥已经几年不读当代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成了主流。“洪子诚所著当代文学史里只字未提路遥作品,陈思和写的当代文学史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笔带过。”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梁向阳说。很多评论家对路遥说,《平凡的世界》相较《人生》而言,是个很大的倒退。贾平凹回忆:“想起他从陕北写作回来,人瘦了一圈儿,我问写作咋样,他说:这回吃了大苦咧,稿子一写完,你要抽好烟哩!《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都不懂文学!”路遥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
最后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的传播路径彻底颠覆了文学作品发表、获奖、传播这个既定流程。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编辑的叶永梅是关键人物。1987年春天,路遥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西德访问前夕,两人在北京的电车上偶遇。叶咏梅一下子认出路遥,并仓促间获得了他刚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第一部只印了3000册。“书里的一群普通人,把我带回到自己曾经插过两年队、当过六年兵,并深情眷恋着的黄土地。书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熟悉、亲切,我仿佛就生活在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人当中,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与喜怒哀乐。”叶永梅决定把路遥的新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路遥后来自述,说自己是一边听着节目播出,一边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委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众正在等待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同时出版社开始不断加印,带动了纸质图书的销量。
1988年3月27日开始,130天的连续播放,《平凡的世界》直接受众达3亿之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播放《平凡的世界》而收到的听众来信,也创了数量之最。广播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传媒,小说连播是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通道的情况下,《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效应可想而知。开播前,叶咏梅专程赶到西安采访了路遥。路遥穿上一件新潮派的石磨水洗牛仔服,说请叶喝咖啡,最后还是在办公室喝了茶。“我从小就想,要在我40岁的时候一定要写出一部长篇,要写我的家乡。”路遥对叶咏梅说,自己正是因为喜欢笔下的人物,所以才去写的,“他们中间有我的影子,可以说像我又不像我,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
与此同时,路遥的肝病在写作时发作越来越重。他甚至明白“在死亡和完成这部作品之间选择了什么”。开播时第一部是成书,第二部是校样,第三部直接就是手稿。路遥在身体快要崩溃的情况下,于1988年5月25日咬牙最后完成,从榆林写到甘泉,“6年奔跑终于撞线”。他立刻抄近路过黄河前往北京送稿。“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路遥最早显现出肝部的病象,在海波记忆中是1986年。海波1985年搬到了西安,又和路遥成了邻居。在海波眼中,路遥年轻时最爱吃的就是回锅肉。“小时候整点钱,就在延川县国营食堂买一盘,就着‘两面馍’吃。”期待、贪婪、满足和痛快,是海波对路遥吃相的记忆。但海波爱人几次给路遥做陕北特色的揪面片,他一尝有猪油就不再下筷子,闻也不行。路遥非常在意自己的传染病,几乎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被他警告过。两人一起去黄陵附近的餐厅吃饭,不断有人来打招呼,但路遥拒绝与别人并桌,自称吃清真,不愿意点任何荤菜,最后打发点馒头咸菜了事。有传言说路遥架子大,其实是由他这样不与人同桌吃饭的习惯生发出来的。实际上他的人缘好到什么程度?王安忆去陕北,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就行。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
《平凡的世界》创作将告尾声时,路遥写道:“心脏在骤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立刻抓住笔。飞快地往下写。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1988年底路遥得了陕西省劳模称号,《平凡的世界》不仅三部都出版了,还改编成了电视剧。1991年3月,路遥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是路遥亲口向贾平凹吐露的真实想法。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写道:“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你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在这样一种机关……最不忙的就是文人先生,可以一杯清茶从早喝到晚。……这些地方虽然听不见枪炮之声,且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远村在《路遥二三事》中写道:“路遥曾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政治,但政治又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文学与政治从来未分过家。他病情十分严重,几乎看不清东西,还坚持看报、看电视,关心‘十四大’的人事安排,还说等他病好了,要把作协搞好。”
尽管雄心勃勃,此时的路遥已经陷入了多重困境。家族肝病在路遥去世后,肝病又夺去了父亲和两个弟弟王卫军和王天乐的生命。后来陕西省作协在贾平凹、陈忠实倡议下曾经为他的家人募款,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也患上肝硬化并出现轻度腹水,父母姐妹全都是一样的病。女儿路远长大后曾经在打官司时表示,父亲的文学成就并没有给家庭带来收入。这个情况到2003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路远重新签订了版税合同。他过世后留下万元的外债,曹谷溪记得,路遥曾经向朋友张晓光求助:“我实在穷得可怕,你认识那么多企业家,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经理厂长,我给人家写篇报告文学,给我挣几个钱。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张晓光问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要多少钱,路遥伸出五个手指:“5000吧!这是我第一次卖自己的名字给别人……”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很快他被转回西安西京医院。他无比思念女儿,看到五弟在旁边,突然对海波说如果自己的人生听老人的话,早结婚生子,孩子也该大了。“更想念老人,父亲、母亲、奶奶和大爹、大妈。这些人虽然没文化,但在人生的总体把握上比我们强啊。”路遥越来越觉得自己写稿,和父亲种地没什么区别。他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同样身体不好的贾平凹去医院最后一次看他,路遥说:“等出院了,你和我到陕北去,寻个山圪崂住下,咱一边放羊一边养身子。”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年仅42岁的路遥因肝硬化,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走完了他平凡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
我们不会忘记路遥。苦难的人生旅程,诠释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不由让我们想起鲁讯先生的一句话,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血、是牛奶。这也正是路遥平凡而又短暂一生的写照。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平凡的人们。他和他的作品奉献出的精神食粮,激励了和正在激励着平凡世界里的人们于逆境中自强不息,在苦难中搏击人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还活着!
责编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