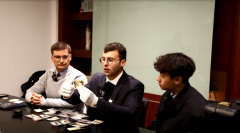别无选择

(上面照片中左是高美娟)
备战备荒风云起,
好儿女齐聚武装连,
打靶种地两不误,
黄蒿沟涛声伴我眠。
男子个个逞英豪,
女生人人来争先,
军号声声震兵营,
紧急集合去拉练。
这是我创作的快板表演唱《魂牵梦绕查哈阳》的片段。1969年5月,我不满17岁去了兵团,在查哈阳度过了青春时代最美好的十年。曾分别在连队、宣传队、团机关工作。其中最艰苦、最刻骨铭心的当属武装连的生活,我和100多名知青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的青春之歌。
一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令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备战。处于祖国北疆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不例外。五十团各营成立了武装连,二营的武装连就设在12连。
知青都是怀揣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使命来到边疆的,听说要组建武装连,大家都热血沸腾,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有的甚至写下血书,表达视死如归的决心。我自然也首当其冲,但连队要保留部分骨干,没有批准。我只能羡慕地看着我的同班同学杨晓敏、张佩丽、陆福娣、张桂英和其他战友们光荣地成为武装连战士。武装连由各连队根红苗壮的知青骨干组成,全连一百多人,设置了4个排。其中一排、二排、机枪排是男排,仅有一个女排。
武装连成立初期,并没有发枪,直到70年6月18日,兵团组建纪念日才发放武器。在发武器的前一天,突然通知我到武装女排任排长。女排前两任排长都是德高望重的高中生,是受人尊敬的大姐式人物。我刚过17岁,初中才上一年,何德何能领导30多名来自各地、性格迥异的知青?如何管理好她们的吃喝拉撒睡?接到调令以后,我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但军令如山倒,别无选择,只能鼓足勇气到武装连报到。
在武装连隆重的发枪仪式上,我连日的焦虑和疲劳终于爆发了。当时指导员刘俊生在队伍前面慷慨激昂地做动员,我扛着冲锋枪站在女排的第一排,突然眼前的影像模糊起来,眼前一黑,恰如掉入万丈深渊,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不省人事、晕倒在地。战友们掐我人中,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慢慢苏醒过来,只听指导员说:“她太激动了”。我心里很清楚,我本懦弱,吃苦受累并不惧怕,但对带领33名武装女排战士毫无把握,我惧怕今后的命运。
这一昏厥一发不可收拾,为以后习惯性昏厥埋下了隐患。在田间地头、在团部会议室、在探亲回家的途中,我一次又一次晕倒。当繁重劳作与精神压力超越了身体的极限,体能拉响了警报,各种器官开始罢工,我并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用狂热的精神支起疲倦不堪的身体,去迎接炼狱般的挑战。
二
武装连设在离12连三、四里地的窑地,周围荒无人烟,仅有一座砖窑和一排砖房,紧靠着西黄蒿沟,夜静人深时西黄蒿沟桥下落差时产生的波涛声分外清晰。女排共有33名战友,来自二营各个连队,有京、津、沪、齐市、鸡西知青组成。女宿舍尚未建成,30多人都住在帐篷里,搭起的木板床离地面不到二尺,帐篷里面又潮又热。蚊子、跳蚤更是猖獗,很多战友腿上、身上被咬了无数包,我的同学陆福娣腿被咬的像个赤豆粽。帐篷的门就是一条布帘子,有时我们出工回来,狗啊、猪啊就到我们帐篷里串门,一通折腾,将我们吃的,用的、穿的糟蹋个够。听说附近还有野狼出没。女孩子们都很害怕,每天晚上在帐篷门口堆放了好多脸盆,如有动静脸盆相碰的声音就能把大家惊醒。
武装连一切行动军事化。清晨,司号员上海知青王云龙吹响了嘹亮的起床号,听着集合号去操练出工,晚上在熄灯号后休息。整队唱歌开饭、下地。女排没有副排长,一班长是天津知青赵新月,后来新月调走以后是上海知青何国英;二班长是我的同学好友陆福娣;三班长是纤细瘦小的天津知青王为,枪炮班是泼辣干练的富拉尔基知青赵淑连。
武装连成立初期,我们日常进行军事训练、队列、打靶。“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口号声响彻窑地上空。枪架就支在帐篷里。晚上还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半夜还要起来轮流站岗放哨。2人一组,一小时一班,每天晚上就要十几人值班,全排三、四天就轮流一遍。基本睡不了囫囵觉。在漆黑的夜晚,战士们背枪站岗。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为了适应紧急情况,连队经常突然袭击搞紧急集合。武装连连长是复员军人姜文,身材魁梧,眼如铜铃,声如洪钟,他基本不下地,有足够的精力搞军事演习。战友们白天劳累一天,经常睡到半夜,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响起,从穿衣打背包、带上各种武装,不到三分钟就整装待命。有一次,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大家都在擦身,紧急集合号又吹响,女排战友身上肥皂沫都未擦净,就穿上衣服紧急集合。搞的大家都紧张兮兮的,有的恐怕紧急集合来不及打包,就合衣睡觉,时刻准备去战斗。几番折腾,大家都累得不愿起床,我每天听到起床号第一个起来,喊着“起床啦、起床啦……”除了一班长外,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多少年以后,大家说,你喊完以后自己又睡着了,是否事实已无从考证,但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好睡的年龄是不争的事实。我白天带着大家出工,晚上还有开不完的会议,从来没有休息和病假。
70年麦收,查哈阳遭受了巨大的水灾,麦子都泡在水里,康拜因收割机下不了地,五十团提出龙口夺粮,不能将麦子烂在地里,要在齐膝深的水里捞麦子。秋收开始了,一场大战役就要打响。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但马上就要开镰了,女排镰刀还未落实。我万分焦急,连队领导告知我到铁匠王瘸子那儿领。连队盛传歌谣“王瘸子的刀,割地用不着,一根一根往下蒿”,可见镰刀的质量,但是这样还是紧缺商品。为了抢到麦收工具,在开镰那天我早上4点起来,摸黑到连队铁匠铺,等着王瘸子将镰刀一把把磨出来,出工时发到大家手里。这样的镰刀使用起来别提多费劲了,当天很多战友手掌就磨起了血泡。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白天我们没有穿过干衣裤。早上穿着湿裤子、湿鞋出工,下班回来晾在绳子上,换上干裤子,第二天又穿上湿裤湿鞋出工。很多战友的腿在水下长时间浸泡,皮肤过敏,瘙痒糜烂。到女同志特殊例假来时,谁也不提休息。
“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有一天连续下大雨,刚放晴我们就出工,顷刻间来一场倾盆大雨,把我们浇了回来;回到帐篷,换了干净衣服,老天爷捉弄我们,天又放晴了,我们又得出工,结果又是一场倾盆大雨。连续出工三次,战友们仅有的三套衣裤全湿了,只能躺进被窝里,班长从食堂打来能照见人影的小米粥和黑黑的馒头,但谁也不愿吃, 很多战友在被窝里偷偷哭泣。
潮湿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和训练使许多战友得了肠胃病,有的拉痢疾,最严重的是上海知青吴小堤,因为没有特效药,每天拉二十多次,人已虚脱了,每次上厕所都要两名战友架着她,后来她在二军医大学任军医的母亲不得不来连队接她回城。
冬天以前,我们女排总算搬到了新宿舍。冬天主要是修水利,在生产排时女知青就干些下手活。但在无一男子的女排,重体力活都要自己来,我们抡起了铁镐。冰冻三尺,三镐下去,纹丝不动。一冬天下来,人人成了挥镐自如的大力士。我的脚步就是丈量器,一步为一米,按照人头给各班分任务。水利工地离连队步行要走一个来小时,中午送来午饭就合着风雪吃。累了就蒙着大衣靠着堤坝睡着了。武装连和以后八九年北大荒寒冷艰苦的生活,使女排战友无不患有关节炎。男排很多战友得了腰肌劳损。一排排长张春发后转为肾病,不到30岁就英年早逝。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30多名来自各地的年轻姑娘,上海女生细腻;北京女生傲气;齐市女生豪放;天津女生爽气;鸡西女生稚气;这些特性交织在一起,就像锅碗瓢盆交响曲,矛盾摩擦少不了,我是按了葫芦起来瓢,难以招架。女排常被连领导批评如一盘散沙。好在能干的班长们承担了许多思想和管理工作,女排慢慢走上了正轨,并以不屈不饶、坚韧不拔的精神赢得全连好评,在年底评比时被评为先进排。
三
爱美之心人兼有之,何况是十七、八岁的花季年龄,可我们头脑里根深蒂固地打上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烙印,与美丽、漂亮无缘。一年四季穿着破旧的工作服。从来不懂得保护头发,没有洗头水、护发素,就用洗衣粉洗头,头发干枯、变黄。我脸上没有使用任何化妆品,从家中带来的雪花膏早已用完,再加上每日太阳地下的暴晒,脸上开始脱皮,活像一只脱了皮的洋葱,一班长新月实在看不下去,在田间休息时,把我脸上的脱皮一片片地撕下来,疼痛难忍。
武装连的作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00多名少男少女在一个武装连一年多,没有爱情,没有绯闻;但也有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淘气事。如71年夏季流行红眼病,有些男生故意在一个脸盆里洗脸,传染上红眼病能休息半个月。但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冲锋陷阵时,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奉献和牺牲。
一天晚上,一名老职工妻子产后大出血,生命垂危。消息传来,武装连蜂拥而动,许多战友跑步到营部医院,争先恐后挽起袖子抢着献血。验血以后有几名战士合格,他们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抽血。产妇转危为安。献血战友都没休息,二排排长富拉尔基知青王家辉献了200cc鲜血,第二天早上,他脸上毫无血色,但又出现在出工的队伍中。
奚顺定是上海知青,个头不高,身体瘦弱,大大的双眼总是带着甜蜜的微笑。她是位倔强、不服输的姑娘。虽然是68届知青,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66、67届下乡时她就积极报名,作为第一批知青踏上了北大荒。农村艰苦的劳动使她患上罕见的肌肉营养缺乏症,多次瘫倒在地头,但稍加好转她就坚持出工,最严重时跪在陇上铲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背她回宿舍。最后终于瘫痪,病退回上海,多年以后才治愈。
最令人感动的是男排风雨护砖窑。那时窑里已码放了一窑砖坯,窑顶上盖着苫布。一天,突然刮起狂风,将苫布刮起,一场倾盆大雨降临,眼看一窑的砖坯就要化为泥浆。男排很多战友都冲出宿舍,爬上窑顶,用身体压着苫布,任凭豆大的雨点和疾风扬起的沙土打在他们的身上和脸上,大雨以后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但一窑的砖坯丝毫未损。
我被这些生动、感人的人物和事物所感染,迸发出强烈的创作热情,经常写到深夜,根据这些事迹,创作了对口词《阶级情谊深似海》、《红色连队开红花》、诗表演《风雨护砖窑》等节目。当时我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现在看来这些作品非常稚嫩、直白,当然也不可置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不乏真实、单纯,反映了当时知青之间、知青和老乡之间淳朴的友情和知青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献身精神。连队组织了演出队,排练了一台自创自演的节目。演出后在连队和二营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又带着这些节目参加了团部的文艺汇演,被评为优秀连队宣传队。
武装连在一年多以后解散,女排分到各生产排,一班成立了积肥班,后来成了全团学大寨先进集体。我被调到了团宣传队。
我的习惯性昏厥多次回沪治疗,查不出病因,78年回城以后不治自愈。
下乡十年是别无选择的十年,我们的个人理想、兴趣、爱好、价值无条件服从于党和人民的需要,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凌云壮志。那时候我们充满激情,充满梦想,同时也怀揣不安,怀揣忐忑。每一名知青在那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正在被社会淡忘,知青的故事被掩入了历史的尘埃。知青岁月使我们饱受磨难,我们抱怨过、嫉恨过、诅咒过,但一旦国家有难,社会需要,我们仍将义无反顾地选择挺身而出。
(作者系原黑龙江兵团50团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