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新元文章选登:难忘你,鲜血染过的黄土地
来源:《黑土情》杂志 作者:聂新元 时间:2018-01-27 点击:

记得有一幅在全国美展上获奖的油画作品《父亲》,画的是一位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老农的头像,画面上那被高原上强烈的阳光晒成古铜色的脸庞上,刻满了北方的强风暴雨和时光岁月留下的皱纹,就像广袤的黄土高原的缩影;刚毅的眼睛在阳光下眯缝着,透射出一股豪爽,不屈地凝望着远方。看到这幅画,我思绪万千,在延安生活时接触过的那许许多多的农村干部、老汉、婆姨、女子、小伙儿们竟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脑海,他们的风度、气质竟那样酷似眼前的这幅画。《父亲》,画家给这幅画的命名简直是太贴切了。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到离县城七十多里的一个村子,村子坐落在两条川道交汇的岔口上,四周山上都是茂密的森林,村里约百十号人,错错落落居住在因地势而挖出的土窑洞和搭盖的石窑里。几百亩川地里长着一人高的玉米。一天早上,我在村口看到生产队的五保户王老汉正在路边抽烟,就走过去和老汉聊了起来。老汉的四川口音引起了我的好奇,便问老汉是哪里人,怎么会到这里落户。
王老汉是四川人,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路过他的家乡,当时年仅17岁的他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扛起一根扁担,就跟着红军走了。
“当红军了吗?”我问。
“没有,给红军当挑夫。”
“从四川一直挑到陕北?”
“是的,一直到了延安。”
“爬雪山、过草地了吗?”
“那当然。”
我不禁对这瘦小的老人肃然起敬了。
“长征路上是不是像电影和书上写的那么苦?”
“比那还苦,十个人里也就剩了两三个人。”
“那您是位长征过的老红军啦!”
“不,我只是个红军的挑夫。”
“那您怎么到这儿的?”
“红军到了延安,不用挑夫了,我就在陕北住下了。”
“您怎么不回老家?”
“我离不开红军,自己又没个家,就住下了。”
“您怎么不成个家?”
“谁家的姑娘找我这么个回不了老家的南方人。”
“那您一直种地吗?”
“不,我一直跑山(当地人管钻山林采山货、打猎为生的人叫跑山),有时红军派我到白区办点事,办完我又跑山。五几年合作化的时候才到这里落户。”
“那您算不算老红军?国家给什么照顾吗?”
“没有,我就是个五保户,咱没文化,干不了什么事,就会跑山,当不了红军!”
我黯然了。半晌,我问王老汉:“您跑了几十年山,这一片的山林都跑遍了吗?”“那可不,1948年打瓦子街(即宜川战役)时,八路军(即西北野战军,当地老百姓在解放战争初期还习惯地称之为八路军,下同。)还派人找到我给彭老总当向导呢!”“什么?打瓦子街战役您也参加了?”“从部队开始埋伏到转移我都跟着彭老总。”“就在那边,”老汉手向南一指,“翻过这架山那边的川里就是当年打仗的地方。你今天没事吧,我引你去看看。”没有犹豫,我立刻答应了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老人的邀请。
跟着老人,涉过清凉的小河,走进村对面的一条山沟,老人一路讲着怎样寻野蜂蜜,怎样套羊鹿子,怎样挖獾,怎样打狐子、打野鸡,怎样扳木耳,滔滔不绝,仿佛整个大自然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那苍老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一双结满厚皮老茧、骨节粗大的手不时挥动着,指点着那些他十分熟悉的山崖、大树。那神态,那语气,完全没有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在“公家人”面前那种猥琐的神情。他,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架山,每一条河流小溪,石头窝里的一个泉眼,山上的一草一木,每一样都是他亲手侍弄过的。眼睛看到什么,嘴里就讲起什么,如数家珍,一种对这黄土地的崇敬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由自主,也沉醉在这美丽神奇的山川中。约十里长的山沟走到尽头,顺着背阴山坡上密林中一条蜿蜒的小路爬上山顶,一条东西向的川道展现在眼前。“这就是打刘戡的地方。”王老汉对我说。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宜川战役消灭的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胡宗南手下的得力战将刘戡率领的国民党29军。
仲夏的骄阳照耀着川道两侧的青山,背阴的山坡上浓荫蔽日、郁郁葱葱。向阳面的山坡上树木没有那么茂盛,绿荫中露出片片山崖,有的山脊干脆就裸露着,在阳光下泛出黄土高原的本色。一条土黄色的公路从西向东,分割开绿油油的农田顺川而下。“刘戡的29军就是在这条公路上被我们消灭的。”王老汉说着,神情分明严肃起来,刚才眼睛里那热情的光亮消失了,一双眼睛顺着公路向东望着。“那仗打得激烈,刘戡的队伍两万多人,拉了十几里地长,被八路军六万人围住打了三天三夜,战后死人死马把路两边的沟都填平了。”老汉指着前面不远的山坡上一条依稀可辨的、几乎被雨水淤平了的沟说:“这就是当年挖的战壕。”他指着悬崖边一个土坑说:“仗打完了,老百姓来捡东西,每一个机枪工事旁边都能捡几麻袋子弹壳。”“这仗是怎么打的?”我问他,王老汉扭过脸指着西边说:“刘戡的29军是从富县那边来的。”
“那是1948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已经吃了几个败仗了,八路军(即西北野战军,下同)开始反攻,第一仗就是这宜川战役。那时候八路军把宜川县城围住不打,胡宗南怕丢了从东路进攻延安的这个基地,就派刘戡来增援。彭老总那时候早就估计到刘戡会走这条路来,就提前埋伏在两边的山上。真是老天有眼,就该共产党赢,队伍刚埋伏好,天就下雪了,山上川里一片雪白,把八路军修的战壕、工事埋得严严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八路军就在雪里埋伏了六天六夜呀!到第七天,刘戡的队伍来了,钻进了彭老总的口袋阵,彭老总一声令下,东西两边一封口,南北两面一起向下压,刘戡的29军就被堵在十几里长的公路上挨打。那仗打的,刘戡指挥队伍突围,有的山头反复冲锋十几次,八路军也反冲锋。离得近了,拼刺刀,山坡上、河沟里到处是尸体,雪地也被染红了。”“您那时候在哪儿?”“就在那边!”我顺着王老汉的手望去,只见东南面有一座林木茂密的山头,“那山顶上林子里有一片空地,彭老总的指挥部就在那里。”“您在那里干啥?”“我当向导,彭老总安排队伍埋伏的时候,就坐在地图边上,边看边问,这条山沟多长,那条沟伸向什么方向,一边问,一边就给部队下命令。”“仗打起来的时候您也在吗?”“在!炮一响,我有点儿慌,彭老总看出来了,大声说:“跟着我你还怕什么!有我在就有你在!”说完叫过一个警卫战士,让他负责我的安全。仗一打起来,彭老总周围的十几个电话机和十几个参谋就忙起来了,彭老总不停地下着命令,参谋和传令兵进进出出,遇到地图上没标清的地方,彭老总就把我叫去,详详细细问一遍,然后又下命令。”“那仗打了三天三夜,彭老总就干了三天三夜吗?”“我没有看见他睡觉。”“吃饭呢?”“吃饭就是参谋拿个饼子给他,再拿个缸子喝点水。”王老汉的这些话,在彭老总蒙冤受屈的那个年代里,说的那样直率、坦白,明显地透露出对彭老总的敬重和由衷的热爱,是战士对指挥员的热爱之情,还是战友之间的手足之情,我说不清。
“仗打完了呢?”我问,“仗打完了,彭老总下令打扫战场,八路军连夜撤到河东(黄河以东)去了。”“你还不知道撤退时的事呢!连天的打仗行军,战士们的鞋都磨烂了,很多战士用破布、烂羊皮包着脚在雪地里行军,有不少营长团长到上级来要军鞋,一个师长跳下马,脱下自己的鞋,给了一位光脚的战士,自己就穿了一双旧布袜子和战士们一起在雪地上走起来,营团长们见了,二话不说,回到自己的部队照样干,队伍很快就开走了。”说着说着,王老汉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似乎舒展开了,在阳光下泛着古铜色的光。“你看那边,”王老汉指着远处公路边一座隐隐约约可见的小村落说:“那就是瓦子街,刘戡最后就被打死在那儿。八路军也牺牲了不少人,最大的官是个师参谋长呢!今天不早了,咱们回吧!”我默默地随老汉回到了村里。
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离开延安也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可这件事却那样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以自己的鲜血和乳汁哺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我是那样恋着你!
(作者系北京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逥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工作。)
网友评论
相关内容
您从韶山走来
您从韶山走来 步伐是那么豪迈 一篇大联合的文章 青春的宣言是如此激昂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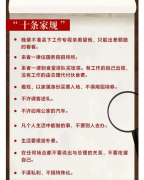
周恩来:“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以下文章来源于钧正平工作室,作者刘忠宇、李约铃 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好...
纪念 《为人民服务》发表80周年征文选登45(余鹤元)
题目:中共党建史上的一座丰碑 《为人民服务》发表八十周年时的阅读与思考 ...
纪念 《为人民服务》发表80周年征文选登44(易 澎)
题目《为人民服务,我牢记在心》 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
纪念 《为人民服务》发表80周年征文选登43(袁炳坤)
题目《不忘初心 为民服务》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其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