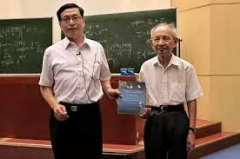硅谷的“乡村女教师”

(2013年马立平博士又一次重返曾经她插队的地方江西永丰鹿岗乡高坑村)
近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学生逐年增长。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统计,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人数达到历史峰值19.4万人,每4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名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教授默默耕耘在美国讲台前,将东方的教育观点,与西方的教育理念相结合,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西方的语言文字加以融合表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学生,既传授西方知识,又输出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人,甚至撼动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其意义恐怕不亚于姚明进入NBA。
马立平硅谷的"乡村女教师"
说起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中文学校,在硅谷的华人圈可谓无人不知。这个以传授中文和中国文化见长的周末学校,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华人家长。他们热衷于在双休日把子女送来,让这些自幼浸染在美国文化之中的黄皮肤小孩,有机会补习缺失的中国文化。这些年,学校越办越火,以至于和其他名校一样,斯坦福中文学校等候批准的申请人名单上,总是排着一长溜名字,这让学校创办人马立平十分欣喜。
马立平的故事,不只是中文学校人人皆知。她以一名仅仅受过中学教育的乡村民办教师,考取华东师大教育学研究生,一路赴美在斯坦福大学念完博士;她的博士论文《小学数学知识的掌握和教学——中美教师对基础数学的理解》出版后,一举成为美国数学教育界难得的畅销书,并且先后被翻译成朝鲜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中文出版,她以数学教育专家的身份接受美国联邦教育部长提名,入选美国总统数学决策顾问团……
从上海姑娘到乡村教师
1951年,马立平出生在上海。在上外附中念完初二后,1969年到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村前大队(现高坑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种水稻、修铁路……干了几年活之后,马立平被指派到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一开始我就要带两个年级的复式班,那时真觉得非常困难,学生根本不听我的话,他们的考试成绩远远落在公社其他一些学校学生后面。"
不得已,她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强化"自己的教学能力,一边找些教育学的理论书来看,一边去母校听各科老师上课。也正是在这段"拜师学艺"的时间里,马立平有幸结识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刘佛年先生。"当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刘佛年先生’靠边’在家。我去他师大一村的家里拜访他,跟他说想学习教育理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不想当老师,但看得出老先生很欣慰,跟我聊到很晚。"
拜访之后一回到家,马立平赶忙拿出纸和笔,记录下刘佛年先生的重要嘱咐——"要有主见,认准了正确的目标,便尽量努力去达到,不要怕别人议论讥笑;要多看书,多实践;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籍,是否可自学英语?教育学的教科书,可以看,但要更多地读教育家的名著,包括杜威、赫尔巴特、蒙台梭利……"这张小纸条,她至今保留着。
回到江西,繁重的教学和劳动任务接踵而来:"那时候,暑假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双抢’,一边把田里的水稻收上来,一边又要把二季稻种下去,几乎天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平时在学校任教时,马立平照着小纸条上刘佛年先生的嘱咐抽时间学起了英语,啃起了"杜威"。
颇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马立平在农村当起老师,教育着当地农民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她又无时不受到"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的教育。"这些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不识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生病的时候,是他们告诫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开导我’人生难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有诸如’起家针挑土,败家水推沙’;’晴带雨伞,饱带饥粮’等等他们脱口而出的谚语,对于不谙世事的我不啻震耳发聩。他们口耳相传的山歌、谜语等等,音调或铿锵、或委婉,用字生动、巧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文学滋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用数学题考过我,比如’一百个和尚一百个馍,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一个,一共有几个大和尚、几个小和尚?’前几年,我为了做数学教育研究接触到《九章算术》,惊喜地在里面发现了农民们考过我的那些题目。我给美国数学老师做报告时,常常说起这些流传在中国农民中的数学题,我的听众总是吃惊不已。"
"文革"结束后,马立平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正式成为刘佛年的学生。
1989年,马立平踏上了留美之路。
给美国数学教育"把把脉"
到美国后马立平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密执安州立大学。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她口袋里只有当时政府允许兑换的30多美元:"美国的大学如果学生想跨州就读是要支付一笔额外学费的,当时学校免了我州外学费,但基本的学费其实还是要付的。如果早知道这样,我都未必敢来。"
起先马立平与人合住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每月连租金带伙食只要186美元:"房间比上海以前的’亭子间’还小,从门到窗三分之二的面积用板水平方向隔开,板上面放个写字台,板下面睡人。"那间小屋里常常弥漫着一股异味,初来乍到的马立平以为那是美国的味道,等自己的导师和师姐来探望她才知道,所谓的"美国味"原来竟是大麻的味道。
在导师和师姐的帮助下,马立平找到了一份分析研究资料的助研工作,告别了"大麻小屋",搬入普通研究生宿舍。
当时马立平所要分析的资料,是密执安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一个研究项目的调研数据,该项目用4个问题调查美国老师小学数学知识。初读这些数据,让马立平大为吃惊:“比如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小学老师算出7/4÷1/2=?的答案,并且编一道相应的应用题,你能想得到吗?接受调查的100多个老师统统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有一半人以上算不出答案,而能编出概念正确的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只有一个人。”随着调查的深入,马立平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美国并非偶然。学生们不会背乘法口诀,高年级学生做加减法还要扳手指。本来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理来美国,看到这些现象,真的让我非常困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发起并组织了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评(TIMSS),研究结果一公布,引起了美国数学教育界的争议。从60年代初算起30年内的3次测评,美国学生的表现都在平均水平之下,有人把责任归咎在测试工具上。当时马立平就想,是否可以用自己手上正在分析的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问题:“如果人们看到美国教师数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学生成绩之间存在差距的事实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指出了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通过改进教师的知识状况来改进美国数学教育现状呢。”
带着分数除法的问题,马立平回到国内,在自己的母校做了一个小型的实验性研究,结果所有的数学老师都答对了。做好这次实验性研究回到美国不久,马立平从密执安州立大学转学到了斯坦福大学,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导师一听说这个研究,马上兴奋地说:“这个课题不错,你应该就用它做博士论文!”
于是她回到中国,采访了不同水平的5所学校的老师——上海的一师附小等3所小学以及自己在江西下乡时工作的城镇小学和村小。马立平把中国老师对4个问题的回答和美国老师的数据相比较,写出了她的博士论文。
完成后的论文照例被印成红色的精装本,陈放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的书橱里。马立平不甘心让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成果躺在那儿不见天日,在申请到一笔博士后研究经费后,她来到了伯克利大学,最终把论文变成了书。这本紫色封面的小书面世以来共重版重印20余次,累计印数达8万余册,成为美国数学教育界难得一见的热门书。
“小紫书”的大获成功,并没让马立平停止对个中问题的思索。或许正是因为她这孜孜不倦的思索和探讨,让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相中她,把她纳入小布什总统的数学决策顾问团,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进一步献言献策。
华人后裔的“腰杆”
做研究的同时,马立平也没有忘记身为一个“老师”的天赋所在:“研究教育理论的人,一定要重视教育实践。刘佛年先生的这句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4年,马立平创办了斯坦福中文学校。初衷很简单,让当时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后代能够有地方学习中文。从最初只有9名学生到如今10个年级1300多位学生,身为校长的马立平没有做过一次广告,靠的仅仅是口耳相传。
美国的周末中文学校很多,但多半属金字塔形,低年级的学生多,高年级的学生少。马立平的学校不一样,一到五年级就有4个班,而目前六、七年级开到了5个班,呈圆柱形上升。
近20年的时间里,马立平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马立平笑称自己还像当年的乡村教师一样——既教语文又管数学。由她所编写的中文教材,如今已被美洲、欧洲、澳洲和亚洲的100多所中文学校采用。为什么会这么火?在马立平看来,这是因为自己的教材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改进的,相对来说可行性比较强。
记者翻开十年级教材《中华文化巡礼》,从地理到农业、从中医到书法,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马立平说,之所以让教材“包罗万象”,是为了让学生从各个面都了解一些自己祖先的国度,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一步学习:“我们的课程不需要应试,顾忌比较少。我经常会跟学生说,中国文化里的有些概念,你们可能现在不理解,也不一定同意,但一定要尊重它们,或许将来某一天,你们会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自然也就会理解了。”
在马立平编的八年级教材中,选了24句论语。学完之后她总是会问学生最喜欢哪一句?得票率最高的,常常是那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学生们流露出自豪、自信的眼神。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我们的学生多数出生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这些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会有不同程度的困惑。了解祖先伟大的文化,能帮助他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立足于美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