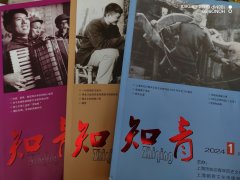满怀豪情屯垦成边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唐文青 时间:2025-04-01 点击:

1966年6月我们团支部五人集体带头报名支援新疆建设,前排左起:沈珏、王心安;后排左起:唐文青、何孝珍、李佳子(已故)。
当我打开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日记,翻阅陈旧的相册时,
岁月留痕,旧影重现。忘不了的那些战友,忘不了的那些故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电影《军垦战歌》《年轻的一 代》的感召下,决心要向电影中的肖继业、林岚学习,听从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在区委党校学习后,正在崇明参加劳动锻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团支部五个人积极带头集体报名支援新疆建设。我们立下誓言,要在叶尔羌河畔扎下粗壮的根,发出茁壮的芽,开出鲜艳的花,结出丰硕的果,把自己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新疆,神秘又陌生、遥远又荒凉,气候恶劣,环境艰苦。不少人嘴唇干裂流鼻血;因为用盐碱水和肥皂洗头,女青年的头发梳不开;交通不便,必须的生活用品很缺乏,就连女青年每月要用的卫生纸都难买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要半月才能收到;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苞谷糊和馍,粗细粮按比例搭配;没有新鲜的蔬菜,喝的是涝坝水。每天清晨哨子一响, 班排集合,肩扛坎土曼,有的拉架子车,有的推独轮车,有的挑柳条筐,下地劳动。顶风沙战严寒,冒烈日酷暑,把一个个像小山似的沙包平整成块块条田。接着又挖支渠、毛渠,引水灌溉治碱,耕耘播种。尽管狂沙如锉,恶风似刀,我们无所畏惧,用双手和汗水开垦万古荒原,屯垦戌边。寒冬腊月, 清晨醒来, 脸盆里的水结成了冰块。地窝子要烧火墙取暖,我们脚蹬齐膝高的大毡筒,

在“史无前例 ”的年代,我们身处戈壁滩,绝大部分青年仍然坚持就地抓革命、促生产,屯垦戌边。我们用青春和汗水在这亘古荒原上种上了防风林带――串天杨,盖起了学校、商店、医院、厂房。随着农场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中的不少青年有的调去当教师,有的当护士,有的开拖拉机,有的进了财会训练班学习。我们留给自己的是脸上岁月的印痕和黝黑的面孔,脱去了稚气,增添了坚毅和刚强,犹如新疆大漠上的“红柳树 ”顽强、挺拔、质朴、敦实。
我先后在男女混合班、种菜班当过班长,处处都要以身作则带头干。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劳累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连队卫生员挺关心, 通知伙房为我做病号饭,最好的病号饭就是面条。我们用苦涩的人生谱写了中国西部的开发史,造就 了千里麦海,万顷棉田。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书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也给曾经的青春留下了骄傲。经过两年的奋战,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农田、渠道、林带、瓜田都呈现在眼前,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拍下了这些照片。
1969年9月,小海子垦区并入新疆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农业第三师建制。1970年 3月,我那时所在的 45团八连奉命转战,集体调到 52 团七连。它离巴楚县城 70 多公里,是维吾尔族聚居之地,常驻人口中少数民族占 75%(如今的图木舒克市 所在地,是新开辟的垦区)。刚到那里时,我和统计员周锡惠一起,在戈壁滩上用红柳枝架起 棚子自建我们的“宿舍 ”。低矮的棚子只能爬进去,里边不能站起来,晚上钻进去睡觉,白天 在露天吃饭。夜晚,当我们躺在地铺上透过红柳枝缝隙,望着天上的星星时,就会情不自禁地 唱起沪剧:“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天是屋顶地是床,青枝绿叶作围墙,又高又大又宽敞,世界第一,哪个比得上…… ”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克服困难。我们一边风餐露宿,一边打土块垒房子,几个月后,全连一百多人都搬进了干打垒的土坯房。
(研究会责任编辑:林嗣丰)
晓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