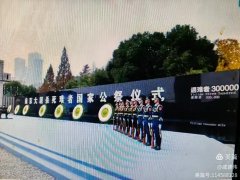父亲,好大一棵树……
来源:凡夫夕拾 作者:费凡平 时间:2023-06-19 点击:

(父亲在川沙外婆家)
父亲节,清晨,我便收到女儿的一个问候“老爸,父亲节快乐!”很是欣慰!
人生,仿佛就是一个个轮回,收到女儿的问候,我禁不住又想起已在天堂的老父亲。
在我的心中,父亲就像一棵充满绿荫的大树。
2000年8月29日10点30分,父亲因患癌症,离开了人间。
大树倒下了,这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不过,那最后的一刻,父亲是握住我的手,闭上眼睛的。父亲最后走的很平静,我亦每每因此而聊以自慰。
人死不能复生,我几次提笔想为父亲留点文字,可我实在怕写这样的文章,我更怕就此与我深受的父亲作如此的了结,为父亲,我绝不想再做一个守望的逃兵。
守望是痛苦的。可我却在守望中咀嚼到丝丝父爱的质感和凝重。
我父亲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邮差家庭,他只读完小学,因兄弟姐妹多,生活贫困,十六岁便问他叔叔借了一套长衫,独自到浦西学生意,仅凭父亲的一己之力,租房,结婚,生子,养活了一家四口人!
父亲一生平凡简朴,性格较内向,为这个家几乎操劳到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他还一次次叮咛我要照顾好母亲,并希望我能把他的遗体捐献给医院,角膜可移植给那些失明的患者……
这一声叮咛,一次次折射出父亲心灵的伟岸,并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情到深处,我常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面对着我珍藏的父亲慈祥的遗像,一次次翻看我为父亲所记的守望日记,一次次又回到了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
2000年8月15日夜
又是一个闷热的夏夜。我一离开报社,就直奔豫园街道医院的病房。
今天已是父亲住院第25天。早上我用救护车送父亲去中山医院作了最后一次核磁共振检查,结论是癌症全身转移,他双脚失去知觉也是癌细胞压迫下肢神经所致。
这种恶化的情况,我是瞒着父亲的,如同我的叔叔父亲的胞弟,才60岁因患肝癌,已于去年10月份去世的噩耗,我和母亲也都一直瞒着他一样。父亲偶尔也问起过他的胞弟,可我们都回答他挺好。
因此,在最后的日子,我也绝不想把如此恶化的真实病情告诉父亲了。
癌症晚期病人是十分疼痛的,也许是父亲刚刚打过杜冷汀,精神略有些好转,他朝我笑了笑:“凡平,你也不要瞒我了,我知道这次情况不好,可能也熬不过这个夏天了,你们已经尽力了,你身体也不好,今晚你不要陪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一个病重的老人,生命行将结束,仍在关心和体恤着小辈,这就是我父亲。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但关键时说上一二句顿会使你心明气畅。记得我被下放去北大荒的前一夜,我很伤感,这绝非是我愿意去的地方。
父亲一边在帮我打点行理,一边在安慰我:“这是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我这个父亲是没有能力去改变的,更没门路让你去当兵的,你要理解父亲,去了就好好干,我会想你的……”

(父亲出差在外留个影)
从不喝白酒的父亲,这临行的前夕,他为自己也为我倒上一杯白酒,一口喝下,为我壮行。这烈酒顿时灼烧我的嗓子,泪禁不住哗哗流淌。
很晚了,父亲却在一边一直沉默地喝酒,这一晚他整整喝了半瓶白酒。
第二天,我在彭浦货场坐上了北去的列车,这是一辆专送北大荒知青的专列,车窗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亲友,喊声哭声惊天震地,在车轮转动的一刹那,我发现父亲已不在窗前,而一个人独自站在远处,一边朝我挥手示别,一边用手在擦拭着自己湿润的眼眶。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汽笛声中,我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车轮转动了,我的心几乎要破碎,模糊的双眼望着那远去的父亲的背影,这背影像一尊雕塑刻在我的心上。
我成了一名知青,做知青总有种种心中的苦闷。
这种苦闷是不愿对自己的知青战友们倾吐的,但我这个远离城市被抛在爱辉边陲的儿子,又是多么需要一个耐心倾听的人啊!
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倾吐的方式就是给父亲写信,长长的信一写就是好几页,父亲收到我的信后,他会连夜当即提笔给我回信,信中每次还会夹上几枚邮票,他的信不长,却底蕴一种绵长的温情。
在我当知青的岁月里,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盼望早日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书。
有一年,我从北大荒逃回上海,因拒绝去用小镰刀割小麦,自残了自己的右手指,买了车票回到上海。
父亲见到我显得很生气,他希望我第二天买了车票立即返回北大荒。父亲不希望我成为一名被人耻笑的逃兵。这一次,我感到很失望,父亲为啥这样不理解我的苦处。
当晚,我独自离家,在黄浦江畔几乎想离开这个人世间。半夜了,是父亲找到了我,他紧紧地抱住了我,嘴里一个劲地说自己无能,但不希望我这样软弱,要活下去……
江水汩汩,一轮明月当空。我后悔自己的举动,但我无法理解父亲,他为什么要把我如此推回北大荒。
父命不敢违抗,回去后,不久我就当上了代课老师,可我有整整两个月没给父亲写信,急得父亲因此病倒,拍了一封加急电报后,我才回得信。
事后我是后悔的,事实证明父亲让我立即返回北大荒也是对的,要不然,我也绝非能当上一名代课老师,拾到这样一个可不下大田劳动的好岗位。
或许,当年我没养成给父亲写信宣泄情感的习惯,那么,今天也许不一定能揣上吃这一口文字的饭碗。
我从心底感激父亲!
2000年8月17日夜
夜是静静的,这天病房里的人都已熟睡。可父亲睁着眼睛望着在一边陪伴的我,怎么也闭不上眼睛。他说他刚才梦见了我的奶奶。
我从未见到奶奶一一父亲的生母,听父亲说,在我未出生的前,我的奶奶因患肝癌离开人世。父亲26岁就失去了母爱。
后来爷爷,便娶了这个奶奶,父亲的沉默,也就是从这开始的。
沉默,有时也往往是种爱。
记得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是在川沙外婆家度过的。
外婆和爷爷家同属一个费家宅,只不过隔一条小河。爷爷家的门前有一个硕大的打谷场,那里经常是我玩耍光顾的地方。
孩提时,我在川沙是出了名的调皮蛋,经常给外婆招惹是非。外婆家虽然与爷爷家只隔一条河,但我仍然很少去爷爷家。爷爷喜欢喝酒,后继的奶奶也不愿与人多打交道,父亲每星期回家看我,也只带我去爷爷家坐上一会儿,晚上也都住在外婆家。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在爷爷家住过一夜,过年了,带着我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时,才会在爷爷家吃上一顿团圆饭。父亲与后继的奶奶话语更少,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在文革初始,县城来的红卫兵在打谷场上批斗我的奶奶,说她曾在日本鬼子手下当过日语翻译,于是,仿佛在一夜之间后继的奶奶便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每天清晨,我这位后继的奶奶就必须要去清扫一遍打谷场。父亲回来了,天未亮总会去打谷场替后继的奶奶打扫上一遍,造反派也是宅上的熟人,看到了也从未说过什么,睁一眼闭一眼。我曾问父亲,“你怎么帮反革命的奶奶扫打谷场不怕红卫兵找你麻烦?”父亲回答:“我不怕,你奶奶年纪大了,不该受这种苦,能帮就帮帮她,奶奶对你爷爷还是不错的,我出身工人,别人也不敢拿我怎样的!”
有一天晚上,打谷场来了一群陌生的红卫兵,后继的奶奶被这帮红卫兵揪到了台上挂上牌子进行批判。这晚,我正好也在边上瞅热闹,一个大个子红卫兵凶狠狠地对我说:“你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要与你奶奶划清界线,你要喊打倒张继明!”张继明,是我后继我奶奶的大名,我才小学刚刚毕业,立刻一阵惊慌,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这群狂徒喊了起来。
站在台上的奶奶看到我也挤在呼喊打倒的人群里,气得当场晕了过去,我心里害怕极了。回到外婆家,立刻被外婆一阵痛骂,并准备要送我回上海。
想不到,第二天,我父亲回来了,外婆立刻告了我一状。父亲听了气得浑身直发抖,顿时抽了我一个巴掌,我连哭都不敢哭。
不一会,父亲领着我去了对岸的爷爷家。我只见父亲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奶奶的身前,并请求后继的奶奶原谅我的过错。
昏暗的小屋,只有天窗上投下一缕阳光,折射到奶奶苍白的脸上,奶奶两行热泪蓦地涌出了眼眶,她颤抖地弯下腰扶起了下跪的父亲:“我不会怪孙子凡平的,他还小,不懂,品义,你这样教子,我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父亲这一夜没有回外婆家睡,他就守护在奶奶的床边。

(父亲在外婆老屋家宰鸡)
父亲,他这一巴掌也把我打醒了,亲情是不能沾污的。哪怕她真是反革命,但她毕竟是我的长辈,我唯一的奶奶呀!
以后我去了北大荒爱辉,也有过一次机会被推荐去上黑河师范,可最后均因为政审没过关。原因就是我那曾给日本鬼子当过翻译的后继的奶奶。
满心的上学希望,就这样成了沼泽地里的一个泡影。我悔恨过,但随即便清醒,我的直系亲属关系是根本无法选择的,这不能怪罪我的奶奶。当我把这些思考写信告诉父亲后,父亲回信大大夸奖了我一番,说我真正成熟长大了。他后悔当年不该这样粗暴地打我一巴掌,请我能原谅他……
在病房的灯光下,往事是这样的清晰,父亲竟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他微微地说:“你小时,我曾打过你,现在我真后悔……”
不,父亲,我要告诉你,真正后悔的却是你的儿子,而不是你!
2000年8月25日夜
近一个月,父亲没进一粒米饭,浑身已瘦得皮包骨头。父亲的病情逐步恶化,疼痛使他杜冷汀只能维持两个小时就失效。
可临床的病友告诉我,你父亲很硬,从没哼过半声。我告诉父亲,真要忍不住就哼一声吧,这样人也许会好受些。父亲朝我摆了摆,又让我坐在他的床边。我这些天来一直有个心愿,很想接父亲去四川北路我家住到临终,因为这是父亲生活了近40年的老家,那里留有他人生足迹。当我把这个想法悄悄告诉父亲,父亲立刻摆手。他说,他心领了,现在哪个家都不想去,就在医院里挺好。
父亲一生没在单位分过房。我当时居住的四川北路永丰坊那一大一小两房间,还是他学生意时用一根金条问二房东租下的永乐坊调换过来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这房还算可以。
我下乡返城后,弟弟结婚苦于无房,最后弟弟单位分了一间婚房,这不足6平方米的亭子间才成了我的天地。父亲和母亲就住在前楼18平方米的房间里。
当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对象,又开始愁恼婚房,父亲看出了我的烦恼,他和父母商量决定让出大房间让我做结婚新房。不过父亲唯有一个要求,那套伴随着他一生的家俱不能丢弃,希望我油漆一下作结婚家具用。我能拥有这间婚房已高兴不已,家俱已是次要问题。
我如期成婚了,父母亲俩人就蜷缩在这间朝北的亭子间,这一住就是好几年,从没有怨言。
1995年,我单位终于增配我一间房,地段不错在淮海东路,可楼层太高是5楼。因为我要写作,要放一张写字的桌子,我很想让父母亲搬到那新增的楼上去住。我的想法首先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母亲希望我们搬到淮海东路去。
最后,我们准备搬向新居。在当我决定下星期搬家时,我父亲在饭桌上告诉我们,他们已决定搬去那里,为了我写作方便,他们也决定下星期日搬家,不过希望我们能经常去看望他们俩位老人。父亲轻轻的一声决定,竟然使我泪水直在眼眶打转。
这不眠之夜,我发现父亲一直坐在亭子间的椅子上,直到天亮,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近大半辈子的住处,说什么感情上也难以接受,但为了我住的宽畅,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又一次忍痛割爱,他们搬去了我增配的桃园新村一室户。
这一搬迁,又有几个年头,父亲很少来我住的地方,只是过年过节才来坐上一回,他仿佛在最短的时间里又接受了另一个短暂而陌生的家。
一天,我告诉父亲,我在鲁迅公园附近按揭购买了一套二居室期房,明年即可入住,到时,我一定接你们俩老去住。
父亲笑了,他说他恐怕住不上了,母亲也不会去住,她仍要回到四川北路永丰坊的老屋,希望我能理解。他们俩对永丰坊有着如此深的情结,是我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我领悟当初父亲搬家时,为何止不住一步一回头!
因为这老屋是父亲他一辈子的心血!这里的一门一窗可以见证父亲平凡的一生!
父亲,丢舍不下永丰坊的老屋,我如此真诚的相邀,让病重的父亲回到永丰坊哪怕住上一夜的愿望,最后又被仁慈的父亲婉言谢绝。
时至今日,我才真正后悔当初不该让年迈的父亲,搬去桃园新村的那间一居室。这无疑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弥补的过错!

(父亲与我女儿在老屋合影)
2000年8月28日夜
像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父亲的状况一天不如一日,时而昏迷中会说些糊话,时而清醒,但已难以有力气说话了。
白天,母亲去了教堂,让教堂里的神父特地来到医院的病床前,为弥留之际的父亲作了场弥撒。因此,晚上父亲显得安静了许多。
父亲什么时候成为天主教徒,我不清楚。但从我记事起,我很少见父亲去教堂做过礼拜。
自从得知自己身患肝癌后,父亲反而显得很平静,他说他年轻时得过伤寒差点送命,已算活过一回,对死已不再惧怕。
有一天,他曾这样对我说,他逝世后准备捐献遗体,追悼会都可以不开,挑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也不要一块墓地,只要种一棵树就满足了……
父亲有如此境界,也许是和他最后两年开始相信天主教有关。父亲告诉我,他的圣名叫“多默”。他还说,在我出生身时,他曾抱我在费家宅的教堂里接受过神父的洗礼,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也应该是一个天主教徒。
可我偏偏不相这些,父亲也从不和我争执。他说,慢慢你会相信的,相信天主不错,灵魂有着落,真的。
望着昏睡中的父亲,我似乎有些信服,在如此的疼痛之中,父亲没有半点急躁和忧虑,一直处于心平气和的心态之中,这或许是上帝给他的力量。
父亲在垂危之中坚信起上帝,在我的理解中,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已寻找到终极信抑与终极安慰。这是否也意味着父亲已追求到最高的真善美,最高的和协和自由。因为,死亡,对父亲而言已不再可怕,而是一种生命最终的解脱和涅槃,我想父亲已达到这样超脱凡尘的境界。
但我没想到,这竟然就是父亲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这一夜,我们父子俩双手紧握着,我真怕我父亲的手会突然松开,就此撒手离我而去。
昏迷中,父亲竟让我打电话给克林顿,要他马上签署最优国待遇……
昏迷中,父亲要我买束鲜花给申花队送去,今年得个亚军也不容易……
昏迷中,我和父亲的手越握越紧……
2000年8月29日晴
离开医院,我回家后又准备上班。昨夜,父亲似乎没有任何声响,他是较平静地度过的。
清晨,我告诉父亲我先回家,然后去上班。父亲是清醒的,他朝我摆摆手,示意快去吧!
我刚要出门,想不到医院的医生打来了呼机呼我,请我速到医院。我马不停蹄地地赶到医院,父亲在接氧气,呼吸已相当急促。我争忙握紧父亲的手,渐渐地父亲睁开了双眼,这时的父亲眼睛已有些走神,但他还能认出我,还知道是我的手在紧握着他的手。他泪眼汪汪沙哑地对我说:“我要走了,凡平你千万要照顾好妈妈……”
父亲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跟我交代,可怎么也吐不出声来。
父亲慢慢地闭上了双眼,他的手也渐渐地松开了我的手。8月29日10点30分,父亲终于离开了我们,他走向了另一个属于他的世界。
人生就像一场梦。父亲在瞬间离开人间,我却像失去了什么一样,人几乎失重,我从未体验过失去亲人的心痛,这种痛,让我一辈子难忘,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好怕,好痛。
我知道,我还有许多事要操办,这时我突然变得坚强起来。搀扶起母亲给父亲作最后一次深深的告别……
夜深了,家里所有的人都睡了,我却忍不住伤心想大哭一场,我在夜色中又一次来到黄浦江边,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终于释放出挤压在心底所有的悲伤……
在江水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影子,这影子就像一棵葱郁的大树,在江水中向我摇曳……
父亲,就是我心中的一棵大树,我知道他已深深扎在我心底,永远不会倒下……
明天,我即去种一棵树,为父亲,也为自己。
责任编辑 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