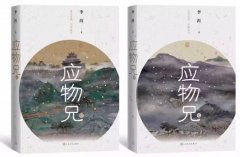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选摘②--他的目的地是上海
来源:文汇报 作者:何建明 时间:2020-07-04 点击: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李秋实、冯铿等五位左联进步作家和其他19位革命志士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他们就是“龙华二十四烈士”。 图为王少伦油画作品《左联等烈士走向刑场》 (现藏于龙华烈士纪念馆)
1
何建明
柔石的原名叫赵平福。16岁那年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18年的事。年少的柔石第一次走出大山,从宁波港乘船先到了上海,再奔杭州。第一次出远门,就见到了三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杭州,让柔石从此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灿烂”。他上浙一师时,正逢这所“浙江革命熔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后来受到被称为浙一师“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后在复旦大学执教,是复旦校歌词作者,1932年去世)、李次九和夏丏尊(因受日本侵略者迫害,于1946年去世)的影响,柔石在入学的第二年就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原本只想“好好念书”的他,看到自己尊敬的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四大金刚”被解聘,以及他十分欣赏的同学、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主编施存统被开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后,柔石有了“现今中国之富强,人民之幸福,非高呼人人读书不可”的全新认识。
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石,像绝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旧势力干扰,他们的追求仍受到束缚。柔石在省城上大学,他家人为了“锁住他的心”,在老家给他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媳妇,让身处新潮生活中的柔石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这与他革命战士的人生追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的许多作品和诗中都流露出这种挣扎又不能摆脱的痛苦。 “五四”时期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人生过程,包括鲁迅、茅盾、陈独秀等。
这种痛苦与挣扎,是那一个时代的青年所面临的一场人生搏杀——
活着要活的痛快,
死了便死个清确,
平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
你立身的价值!
柔石用自己的诗句来激励自己,并对自己说:“你应当知道你自身的宝贝之宝贵和爱情。你应当高飞你坚决的意志之艇,以达到环行地球的目的。……你应该去喜马拉雅山峰而俯视太平洋的宽阔呀!从今后,决愿你明白夜和月,明白生存和死亡,生存和死亡所拴系的切要意味!”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压抑者,也容易成为作家。柔石便是在这种心境下越来越爱好文学,并用文学释放内心的痛苦。
1925年,他带着短篇小说集《疯人》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让他人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就在此地,他结识了冯雪峰,认识了在这里上课的鲁迅,尤其是听鲁迅的课,使他感到是“平生之最大乐事,胜过了十年寒窗”。
这一年,上海的五卅运动给了柔石思想上巨大的冲击与影响,让他从一个进步青年,一跃成为革命者。也就是在这场反帝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战斗诗篇《战》,让他成了声名鹊起的革命诗人。95年过去了,让我们重新读一下这首战斗诗篇,感受一下那个峥嵘岁月里的战斗激情吧——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
尘沙埋没了人间的花草;
太阳呀,呜咽在灰黯的山头,
孩子呀,向着古洞森林中奔跑!
……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
炸弹!手枪!
匕首!毒箭!
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
也齐来助人类战,
战!
火花如流电,
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
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呵!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
还我锦绣的面!
呵,战!
努力冲锋,
战!
在北京的一年里,是柔石想得最多、写得最多的时候,他写小说,写诗歌,也写独幕剧,并且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散文写作。这个时候的柔石,有一种“拜伦式的英雄”追求,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外表少言少语,内心却异常丰富激昂,常常失眠于黑夜里,而黑夜里又是他最富激情的时刻。许多作品,都是他在彻夜不眠中完成的。“黑夜是他光明的追求时刻,也成就了他革命的烈焰熊熊燃烧的最美好的时光。”友人这样评价他。
1926年,柔石回到故乡宁海办校,后来还成了县教育局长。而由他主持工作的宁海中学也慢慢成了宁海革命大本营。可惜,后来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一场 “暴动”葬送了这个学校,也葬送了柔石在家乡的教育救国之路。
故乡的一场革命的失败,也粉碎了柔石内心曾经想过的开辟“宁地之文化”的梦想。残酷的现实,更让他明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推翻反动统治。
“门前拴着晨风中高嘶的白马,声音正激荡着壁上深思的宝剑呀!”柔石又一次离开故乡,而这一次他就再没能回来……
2
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他正式到了鲁迅麾下,成为一名巨人身边的战士。
这是1928年初秋的上海,桂花飘香的季节。鲁迅住在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第一次见面,柔石虔诚地捧上自己的《旧时代之死》书稿,并且向导师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与修改过程。鲁迅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位浙江小老乡,因为在北京他就多少听说过“宁海有位文学青年”。鲁迅接下书稿之后的一番鼓励,让柔石心潮激荡,夜不能眠,于是他把这喜讯告知了远方的家人: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蹇促矣!
可见,鲁迅的鼓励在柔石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说来也巧,不多时,鲁迅因所居的景云里23号靠近宝山路,行人嘈杂,加上邻居时有小孩吵闹,恰好同胡同的18号有房空出,于是决定租下。鲁迅请他在商务馆当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起搬到18号居住,又念柔石等几位青年无居所落脚,便把腾空的23号让他们住。柔石听后开心得快跳起来。更让柔石感动的是,鲁迅还让他们到自己家搭伙就餐。
这些都让柔石内心充满感激与感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自己的心底有异常的不舒服,”的时候,“在先生家中吃了饭,就平静多了”。先生“他的坚毅的精神,清晰的思想,博学的知识,有理智的讲话,都使我惭愧”,“先生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鲁迅还帮助柔石将他的《旧时代之死》发表在《奔流》杂志上。
鲁迅的提携无疑为柔石走上革命文艺道路拓出了条宽阔大道。不久,柔石得知自己的好友冯雪峰在老家浙江义乌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到上海,便把这位有才华、有见识的青年文学理论家介绍给鲁迅。
“请请,快请他过来认得认得!”鲁迅一听“冯雪峰”的名字,便兴奋起来,说,“看过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我们的《奔流》上刊登过,这是人才!”
当柔石把这个消息告诉冯雪峰后,这位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文艺领导者的浙江义乌青年激动得连声高呼。
冯雪峰和鲁迅的见面,形成了联结中国共产党人与鲁迅这位文化巨人之间的纽带,而且鲁迅特别欣赏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并视为又一个真正的“知己”。夫人许广平最了解鲁迅的内心,她称冯雪峰是“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1933年冬,冯雪峰调往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时,是他第一个向毛泽东准确、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从此也使毛泽东对鲁迅有了感情上的共鸣。所有这一切,柔石无疑是起着重要的 “桥梁”作用。同样,柔石也在冯雪峰的介绍下,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俩从此如双星拱月般地生活在鲁迅身边,既是鲁迅的学生,又是鲁迅与中国革命阵营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而他们三人本身又是并肩战斗在文化战线的亲密师生与战友。尤其是柔石与鲁迅之间的个人感情,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变得难舍难分。鲁迅自己承认,柔石是他在上海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采访过鲁迅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经这样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柔石的出现不仅让向来办事不求人的鲁迅日常生活中方便了许多,最主要的是,让他渐渐结识了许多革命文艺青年,包括胡也频等。而柔石在鲁迅身边,获得的则是更强大和彻底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信仰。柔石——完全成为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的笔和情随着革命理想燃烧,不再是单纯的借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来抒发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是真正的“革命”与“革命者”的胸怀了!
看一看他此时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纪实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柔石那满身涌动的革命烈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的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的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
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
“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
我们的关系都似兄弟,我们的组织有如家庭;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她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底购买和接洽,并在每晚睡觉之前,向我们作“晚安”。
“谁要仁丹么?”在会议的长时间之后,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
为了减少椅凳的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有一次,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这样说笑了:“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筷子是枪,米是子弹,用这个,我们吃了那些鱼肉;快些罢,革命,吃饭,可以使我们的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晚饭以后,没有会议的时候,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谈天,——互相找着同志,报告他自己的革命的经过的情形,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底目前的革命形势,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互相叙述着,讨论着。
“这位同志是代表哪里的?”
这句话是常被听到的。
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
“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对于革命怎么样?不切迫么?不了解么?”
“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对于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只是同情,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我回答。
“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他们感叹地。“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日益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来不可!”
有一位辽东的同志,身体高大,脸孔非常慈祥和蔼的人,他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谈话时,——我们是同睡在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的——他就告诉我他对于革命底最初的认识和行动:他说他之所以革命,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四字,他是大地主的孩子,钱是很多的,而他却想推翻“做官阶级”——这四字是他用的;他说他自己是“平民阶级”——底专制,就从家里拿了一支枪,空身逃出到土匪队里去,因为土匪是“做官阶级”的惟一的敌人。可是第一次受伤了,子弹从上臂底后部进,由背上出,——同时他脱了衣服,露出他底第一次的两处伤痕给我看。他是受过几次的伤的(以后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过颇深的伤痕),第二次是在面底后部,耳朵底下面,银圆那么大的云的一块。——同时,他觉到土匪是没有出息的,非进一步作推翻封建社会的行动不可,于是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
威武的,扬跃的,有力的口号,在会议的胜利的闭幕式里,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我们慢慢地摇动着,心是紧张的,情感是兴奋的,态度是坚颜而微笑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后,恍惚地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唤呼着,手舞足蹈地欢乐着。我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飘动地同着我们走,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各处深入,向全国的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的耳边,仿佛响彻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的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在描写上世纪初革命青年在一起谈论革命、加入组织、畅想爱情等等方面最直观和形象的、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节选。
3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个傍晚,他去了一趟鲁迅家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鲁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与北新书局签订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过鲁迅的抄件,就匆匆与鲁迅告别,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面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
他们走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都掉了,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年轻的女党员冯铿的脸颊浮肿得有些让人认不出。
“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
“现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由审判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通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决!” “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18斤重的“半步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样的“重犯”。
“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因为两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刑具惊醒。于是两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依然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人)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赵少雄”是柔石狱中的化名。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此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纸上 “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
“打倒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 “事出意外”,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端起枪,一阵猛烈扫射,惨无人道地将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
啊,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后来也有人说,龙华的桃花之所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浸了它……或许是吧。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则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鲁迅闻知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首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摘自何建明《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1
何建明
柔石的原名叫赵平福。16岁那年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18年的事。年少的柔石第一次走出大山,从宁波港乘船先到了上海,再奔杭州。第一次出远门,就见到了三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杭州,让柔石从此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更灿烂”。他上浙一师时,正逢这所“浙江革命熔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后来受到被称为浙一师“新文化运动”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后在复旦大学执教,是复旦校歌词作者,1932年去世)、李次九和夏丏尊(因受日本侵略者迫害,于1946年去世)的影响,柔石在入学的第二年就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原本只想“好好念书”的他,看到自己尊敬的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四大金刚”被解聘,以及他十分欣赏的同学、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主编施存统被开除等触目惊心的事件后,柔石有了“现今中国之富强,人民之幸福,非高呼人人读书不可”的全新认识。
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柔石,像绝大多数青年一样,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旧势力干扰,他们的追求仍受到束缚。柔石在省城上大学,他家人为了“锁住他的心”,在老家给他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媳妇,让身处新潮生活中的柔石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境地……这与他革命战士的人生追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的许多作品和诗中都流露出这种挣扎又不能摆脱的痛苦。 “五四”时期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人生过程,包括鲁迅、茅盾、陈独秀等。
这种痛苦与挣扎,是那一个时代的青年所面临的一场人生搏杀——
活着要活的痛快,
死了便死个清确,
平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
你立身的价值!
柔石用自己的诗句来激励自己,并对自己说:“你应当知道你自身的宝贝之宝贵和爱情。你应当高飞你坚决的意志之艇,以达到环行地球的目的。……你应该去喜马拉雅山峰而俯视太平洋的宽阔呀!从今后,决愿你明白夜和月,明白生存和死亡,生存和死亡所拴系的切要意味!”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压抑者,也容易成为作家。柔石便是在这种心境下越来越爱好文学,并用文学释放内心的痛苦。
1925年,他带着短篇小说集《疯人》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让他人生又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就在此地,他结识了冯雪峰,认识了在这里上课的鲁迅,尤其是听鲁迅的课,使他感到是“平生之最大乐事,胜过了十年寒窗”。
这一年,上海的五卅运动给了柔石思想上巨大的冲击与影响,让他从一个进步青年,一跃成为革命者。也就是在这场反帝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战斗诗篇《战》,让他成了声名鹊起的革命诗人。95年过去了,让我们重新读一下这首战斗诗篇,感受一下那个峥嵘岁月里的战斗激情吧——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
尘沙埋没了人间的花草;
太阳呀,呜咽在灰黯的山头,
孩子呀,向着古洞森林中奔跑!
……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
炸弹!手枪!
匕首!毒箭!
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
也齐来助人类战,
战!
火花如流电,
血泛如洪泉,
骨堆成了山,
肉腐成肥田,
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呵!战!
剜心也不变!
砍首也不变!
只愿锦绣的山河,
还我锦绣的面!
呵,战!
努力冲锋,
战!
在北京的一年里,是柔石想得最多、写得最多的时候,他写小说,写诗歌,也写独幕剧,并且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散文写作。这个时候的柔石,有一种“拜伦式的英雄”追求,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外表少言少语,内心却异常丰富激昂,常常失眠于黑夜里,而黑夜里又是他最富激情的时刻。许多作品,都是他在彻夜不眠中完成的。“黑夜是他光明的追求时刻,也成就了他革命的烈焰熊熊燃烧的最美好的时光。”友人这样评价他。
1926年,柔石回到故乡宁海办校,后来还成了县教育局长。而由他主持工作的宁海中学也慢慢成了宁海革命大本营。可惜,后来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一场 “暴动”葬送了这个学校,也葬送了柔石在家乡的教育救国之路。
故乡的一场革命的失败,也粉碎了柔石内心曾经想过的开辟“宁地之文化”的梦想。残酷的现实,更让他明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推翻反动统治。
“门前拴着晨风中高嘶的白马,声音正激荡着壁上深思的宝剑呀!”柔石又一次离开故乡,而这一次他就再没能回来……
2
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以革命者的战斗姿态,他正式到了鲁迅麾下,成为一名巨人身边的战士。
这是1928年初秋的上海,桂花飘香的季节。鲁迅住在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第一次见面,柔石虔诚地捧上自己的《旧时代之死》书稿,并且向导师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与修改过程。鲁迅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位浙江小老乡,因为在北京他就多少听说过“宁海有位文学青年”。鲁迅接下书稿之后的一番鼓励,让柔石心潮激荡,夜不能眠,于是他把这喜讯告知了远方的家人: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蹇促矣!
可见,鲁迅的鼓励在柔石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说来也巧,不多时,鲁迅因所居的景云里23号靠近宝山路,行人嘈杂,加上邻居时有小孩吵闹,恰好同胡同的18号有房空出,于是决定租下。鲁迅请他在商务馆当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起搬到18号居住,又念柔石等几位青年无居所落脚,便把腾空的23号让他们住。柔石听后开心得快跳起来。更让柔石感动的是,鲁迅还让他们到自己家搭伙就餐。
这些都让柔石内心充满感激与感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自己的心底有异常的不舒服,”的时候,“在先生家中吃了饭,就平静多了”。先生“他的坚毅的精神,清晰的思想,博学的知识,有理智的讲话,都使我惭愧”,“先生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知识”。鲁迅还帮助柔石将他的《旧时代之死》发表在《奔流》杂志上。
鲁迅的提携无疑为柔石走上革命文艺道路拓出了条宽阔大道。不久,柔石得知自己的好友冯雪峰在老家浙江义乌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到上海,便把这位有才华、有见识的青年文学理论家介绍给鲁迅。
“请请,快请他过来认得认得!”鲁迅一听“冯雪峰”的名字,便兴奋起来,说,“看过他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我们的《奔流》上刊登过,这是人才!”
当柔石把这个消息告诉冯雪峰后,这位后来成为共产党重要文艺领导者的浙江义乌青年激动得连声高呼。
冯雪峰和鲁迅的见面,形成了联结中国共产党人与鲁迅这位文化巨人之间的纽带,而且鲁迅特别欣赏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并视为又一个真正的“知己”。夫人许广平最了解鲁迅的内心,她称冯雪峰是“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人”。1933年冬,冯雪峰调往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时,是他第一个向毛泽东准确、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从此也使毛泽东对鲁迅有了感情上的共鸣。所有这一切,柔石无疑是起着重要的 “桥梁”作用。同样,柔石也在冯雪峰的介绍下,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们俩从此如双星拱月般地生活在鲁迅身边,既是鲁迅的学生,又是鲁迅与中国革命阵营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而他们三人本身又是并肩战斗在文化战线的亲密师生与战友。尤其是柔石与鲁迅之间的个人感情,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变得难舍难分。鲁迅自己承认,柔石是他在上海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采访过鲁迅的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经这样回忆说:“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叫柔石的,恐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最受他爱护的了。”
柔石的出现不仅让向来办事不求人的鲁迅日常生活中方便了许多,最主要的是,让他渐渐结识了许多革命文艺青年,包括胡也频等。而柔石在鲁迅身边,获得的则是更强大和彻底的革命精神与革命信仰。柔石——完全成为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的笔和情随着革命理想燃烧,不再是单纯的借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来抒发革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是真正的“革命”与“革命者”的胸怀了!
看一看他此时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纪实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柔石那满身涌动的革命烈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悠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的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的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
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字形的桌边,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
“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
我们的关系都似兄弟,我们的组织有如家庭;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她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底购买和接洽,并在每晚睡觉之前,向我们作“晚安”。
“谁要仁丹么?”在会议的长时间之后,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
为了减少椅凳的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有一次,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这样说笑了:“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筷子是枪,米是子弹,用这个,我们吃了那些鱼肉;快些罢,革命,吃饭,可以使我们的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晚饭以后,没有会议的时候,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谈天,——互相找着同志,报告他自己的革命的经过的情形,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底目前的革命形势,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互相叙述着,讨论着。
“这位同志是代表哪里的?”
这句话是常被听到的。
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
“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对于革命怎么样?不切迫么?不了解么?”
“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对于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只是同情,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我回答。
“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他们感叹地。“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日益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来不可!”
有一位辽东的同志,身体高大,脸孔非常慈祥和蔼的人,他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谈话时,——我们是同睡在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的——他就告诉我他对于革命底最初的认识和行动:他说他之所以革命,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四字,他是大地主的孩子,钱是很多的,而他却想推翻“做官阶级”——这四字是他用的;他说他自己是“平民阶级”——底专制,就从家里拿了一支枪,空身逃出到土匪队里去,因为土匪是“做官阶级”的惟一的敌人。可是第一次受伤了,子弹从上臂底后部进,由背上出,——同时他脱了衣服,露出他底第一次的两处伤痕给我看。他是受过几次的伤的(以后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过颇深的伤痕),第二次是在面底后部,耳朵底下面,银圆那么大的云的一块。——同时,他觉到土匪是没有出息的,非进一步作推翻封建社会的行动不可,于是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
威武的,扬跃的,有力的口号,在会议的胜利的闭幕式里,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我们慢慢地摇动着,心是紧张的,情感是兴奋的,态度是坚颜而微笑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后,恍惚地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唤呼着,手舞足蹈地欢乐着。我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飘动地同着我们走,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各处深入,向全国的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的耳边,仿佛响彻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的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在描写上世纪初革命青年在一起谈论革命、加入组织、畅想爱情等等方面最直观和形象的、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节选。
3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个傍晚,他去了一趟鲁迅家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鲁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与北新书局签订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过鲁迅的抄件,就匆匆与鲁迅告别,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面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
他们走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都掉了,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年轻的女党员冯铿的脸颊浮肿得有些让人认不出。
“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
“现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由审判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通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决!” “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18斤重的“半步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样的“重犯”。
“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因为两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刑具惊醒。于是两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依然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人)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赵少雄”是柔石狱中的化名。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此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纸上 “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
“打倒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 “事出意外”,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端起枪,一阵猛烈扫射,惨无人道地将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
啊,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后来也有人说,龙华的桃花之所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浸了它……或许是吧。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则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鲁迅闻知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首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摘自何建明《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因篇幅原因,刊发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