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三家巷〉——一个文二代的共和国记忆》第三章中三节
《走出〈三家巷〉——一个文二代的共和国记忆》第三章中三节
动员出身不好的同学上山下乡
1965年2月,初三的寒假还未结束,学校就已经召集毕业班的团支部委员回校了。当然,布置的工作跟初中毕业有关,那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说白了,就是有同学要下乡,离开城市去当知识青年,也就是下乡当“知青”。
当时,报纸给我们树立了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模范榜样,如董加耕,邢燕子。这些被报上称之为支援山区,把文化带到农村去的,是冠以光环的好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没有过于强调,说得更多的是支援农村建设。下乡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大家都接受把知识与劳动结合的正面意义。于是,青年学生中基本上以此为荣,更有甚者,大家都是主动准备的,批准谁去自然就由组织上决定了。
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是一个很年轻的教师,但在我印象中,他几乎很少任教上课,似乎是专职的政工干部。他来自潮汕地区,本来就不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思想激进,带头每天光着脚板,卷起裤腿上班。于是,毕业班的同学们,很多也开始光脚上学,先从磨练脚板开始,落实着自己的铿锵誓言。清晨,这批人提前回校,在学校大操场的跑道上,光着脚板,在煤渣铺垫的跑道上忍痛行走。当年没有塑料跑道,学校的跑道是混合煤渣的跑道。更积极的就挑起一副扁担,前后箩筐各放两块红砖,把肩膀也练起来。那个年代,可能学校资源不足,规定上学的年龄必须年满七周岁,少一个月也不行,所以,初中毕业的同学,年龄也都有十五岁了。十五岁其实也是绝对的孩子。不过,革命的年代,谁会过分宠爱孩子,又有哪个孩子会甘于撒娇。
我想,不会有哪家的父母会对自已的孩子说,农村很苦,你不要去。是的,革命的魅力,不在于是否真能改变你的灵魂,而在于煽动起群众,形成强大的压力。革命的伟大目标即便是空想,它往众人面前一放,天生它就是无比神圣,你只能自惭形秽。人们于是只能攀比谁更革命,这种竞赛不但在同伴中潜行,甚而跨越辈分,在家庭中萌生。私心被尘封在心里,顶多就是无语,无语就已经是最有力的不支持。智者还可能心有暗计,愚者总是相信鼓动,误以为自己认识了潮流,投身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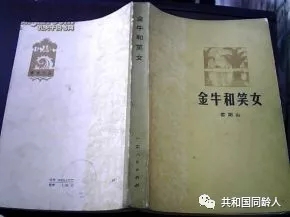
表面上,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学习表态,人人都必须有两种准备,党叫上学就上学,党叫下乡就下乡。但是,骨干的一两名学生干部实际已经获悉,特别要做好三个同学的思想工作。这三个同学分别是姓孙和姓韩的男生和一位姓廖的女生。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班初中毕业后就下乡去了农场的正是这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连入高中的考试都免了,他们的去向,在初三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其实,他们的命运,在初一入学填写家庭成分的时候就己经决定了,他们都是班上出身最不好的人。尽管他们中两个人的学习很好,表现也不错。
孙同学,我又要好好讲讲这个人了,因为他的情况太有代表性,实在是太典型了。我和他后来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大概两年前,我和他坐在香港佐敦道的一个咖啡厅里,谈起过他偷渡香港后的经历。当初同学时我就知道他出身反动军官,十几岁的他从来没见过父亲,也没和父亲有过通信联系,背着那不知底细的枷锁,一直在沉默的母亲身边长大。他说他也是到了香港之后,母亲才告诉他父亲就在香港。之后他才找到那位已经十分陌生的父亲。
原来,他父亲也还是一位文化人,大陆解放以后并没有去台湾,而是流落在香港。在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本小册子很流行,我们去沙头角中英街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偷偷夹带一两本回家偷看。这本小册子叫《姐妹》。这本小杂志厚厚的有六七十页,却还没有小学课本大,杂志算不上黄,但总有接近色情的几张图片。主要的是有大量的生活知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能接触到这样的图书,那跟听到徐小凤邓丽君的歌声是一样的,已经是让人的好奇心大为满足了。而孙同学的父亲,就是这本杂志的主编。
在班上,孙同学是英语课的科代表,各种成绩名列前几名。体育方面更尤为出色。我们班有个叫陶炜的,和他两人都是少年乒乓球的省级选手。陶炜得过省第二,孙也是参赛选手之一。陶炜英年早逝,文化大革m时已经参加省队的集训,武斗时期在越秀山体育馆练球,休息时跑出来乘凉,一辆红卫兵武装车辆经过,不知道什么人喊了一句口号,得罪了车辆上的红卫兵,车上扔出来一颗手榴弹却把陶炜炸死了。中国优秀的乒乓球国手中,就这样少了一个后备队员。孙同学的衣着简陋,人却非常亲近平和,尤其长了一双酷似河北女孩的吊眼,眼尾高高翘上,总是笑脸迎人。我是个好动之人,学校运动会上我得过的最好成绩是初中组跳远第一。自然,我和他既是玩伴又是各种球队队友。对他不能继续上高中,自然心有惋惜。当年三个同学都服从分配,慢慢地,也就默默地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他们去的是连山县的农场。孙同学一直表现很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他无聊回到广州的家。一次看什么球赛,他却因炒卖球票被押送回农场。回农场后,连长很贴心地对他说:你这样出身的人,表现再好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较脚”啦!这句是广东方言,当时特指偷渡出境的行为。
万念俱灰之后,他加入了广东特有的偷渡大军,他说从斗门下水游到澳门,再转到香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照田鸡”。农民晚上用手电照着抓青蛙,青蛙就不动了,以此作比,孙的这份工作是在电影院里做带位员。后来他做过很多份工作,他一直从工人做到老板的女婿,接班成为了坚持设厂在港的塑料厂长,直至现在。
令人惊讶的是,谈到过去,谈到那么多的不平,他作为一个勤奋好学的优秀生,却连上高中的考试资格都没有,他的脸上十分平静。我没有勇气问他,但猜测他的内心,也许觉得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他反而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对政府的不信任。他说,他自己即便是到了现在,一提到国家领导人什么的,心里都会非常激动,崇敬万分。我心里疑惑顿生,难道重负之下只会产生反抗?我怎么见到了压迫之下的忠诚?不过,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受的是五分加绵羊的教育,我们那一代基本上都是老实人。比我们年轻十年八年的下一拨,和我们相比可能聪明一些,但已经没有那么老实了。再往下的后来人,一批比一批更会为自己打算,就更有个性了。顺带再说一句,以我的人生经历,我认识的当年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中间,热爱祖国、老老实实、人品敦厚之辈,其比例和数量,绝对比怀恨共产党的人多得多。

1965年7月,初中考高中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初中的同学们己经纷纷准备分手告别。离开城市的去了下乡。即使升学,有部分也到职业学校去,就算升高中,也有转校的,并非都能留下来,留下来的,也不一定能还在一个班。不过,我的去向几无悬念,学校领导早早就做了工作,动员我留下。考试的成绩还未公布,校团委就通知我,暑假要到市团校集训,准备升高中之后担任重要的学生干部工作。
广州市团校在市郊的夏茅,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环境,到社会的学校里去,所以印象很深。当然,这次十五天的集训,认识了两位学艺拔尖的漂亮女孩,尤觉眼前一亮。和漂亮的女孩一起受到重视和培养,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幸福。认识的这两个女孩,是广州市第二中学的团干部,一个高个子,身高在一米七十左右,一个矮一些,但都长得美丽大方。她们不但能说会道,能歌善舞,而且都特别的有气质,眉宇中难掩自信和不凡。这也难怪,因为她们一个是广州市市长的女儿,另一个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市长的女儿一起给大家朗读一篇越战的报道,讲的是美国军队如何残忍地向平民扔汽油弹,抓住一群男女俘虏,为了防止他们逃跑,竟然用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一个一个串起来。读到悲愤之处,市长女儿声泪俱下,我也动情得声音嘶哑。我和这两位高贵的少女分在同一个组里学习讨论,到培训结束时真有点不想离去。市长女儿掏出一本精美的笔记本,请我写下一段临别赠言。记得,我好像写了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话,我感觉,自己也分不清面对她们是什么情感,有些许的倾慕,更多的是不敢仰视。结束的晚会上她们还有一段跳民族舞的节目表演,我在她们的意气风发面前,和在革命口号面前感觉是一样的,只能是自惭形秽。
与市长女儿的下一次见面,让人受宠若惊。与市长女儿文革中还有一次见面,她那时已经是英姿飒爽的红卫兵,但她绝对没看见我,我那时候在昏晚的街头惊魂未定地漫步,已经犹如丧家之犬了。当然,后来她父亲也被打倒了,她的名字本来在干部子弟中几乎无人不晓,慢慢也就不知所终,据说是到国外还是香港去了,永远地淡出了广州这座城市的舞台。回头再说说让我受宠若惊的那次见面,那是在广州东风中路上,时间己经去到我们都上高一了。大家都是骑自行车放学回家。东风路那时候不像今天这般宽敞,全广州的路都是一个方向只有一条车道。东风路已经算是最宽的,来回两条车道之间有大树作为分隔带,她隔着这些粗大的树干,居然看见了迎面而来的我,大声喊叫我名字之后,我们俩就在路的两边,单脚撑地坐在车子上,大声聊了几分钟。对于与我同行的同学,对于放学人潮的学生,仿佛我俩已经放浪形骸,我感觉得到旁人艳羡的目光,我仿佛骑在了童话中的白马之上。这种跨学校的交友,在一个保守的年代,肯定让人羡慕万分。也许这在她那方面并没什么特别,那个时代如果发展下去,她再稍微成熟一点,那毫无疑问,她一定是位地位高贵的红色公主,石榴裙下应该围满崇拜她的人。至少,那一次相遇,她在我的脑海之中,算得上是一次情感的骚动。

《一代风流》全书五卷,后三本文革后出版
重重复复的忆苦思甜教育
1965年10月,我已经上高中了,当然,上的学校还是广州市第十六中学。身份上除了初中与高中生的转变,我的职务也有了改变,我已经是学校团委的宣传委员。校团委的书记是校党支部书记兼任的专职老师。两千多学生之中只有三个团委委员,都是高中学生中的团干部,三个委员之下还有三个干事,分别是组织、宣传、文体干事,就连这三个干事,也都是高中的学生。
上高中以后,学校有了很大的改变,高中每个年级只有三两个班,初中每个年级却有七八个班,初一竟然有十五个班。在人的因素第一的口号下,当年人口的高度增长,使学校成了一个绝对的金字塔形。这也是后来中国为什么实行了世界闻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上高中的另一个变化,我们学校的干部子弟增多了起来,就广州市而言,广雅中学是干部子弟最多的学校,华南师范学院附中第二,我们学校就排第三了。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广州的西部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区,东山区则是传统的机关所在地。我们的学校周围,就正好有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空军司令部、管理中南五省的广州铁路局等等机关大院。这些干部子弟的父母多数来自北方,他们们之中不少人也是十来岁才到广州来。身材性格语言,与本地人的区别使他们个个自信满满,个性鲜明,趾高气扬。其中有些到南方后语言不适应,不乏留级的老油条,他们中有些人,全然不会介怀自己的学习成绩,他们甚至连学校老师都不放在眼里。加上越趋严峻的政治空气,他们几乎成了政治上特别早熟的学校贵族。事实上,经过初中上高中的一轮筛选,资源的配置趋向集中,既得利益者更为完整地占据了空间,在阶级成分上的优胜劣汰正悄然走到了前台。
校园里的变化日益增多,群情汹涌,万众齐心的争相进步,竞赛着光脚挑扁担的疯狂练习反倒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忆苦思甜,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政治压力日渐增大,出身不好的同学几乎光从脸上的表情就可以分辨出来。政治上没有出路的同学,埋头于专心学习,又受到白专道路的批判,批判的对象,已经发展到诸如“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普通常识。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的三好学生,已经远远赶不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吃香了。
同学中家庭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也纷纷站出来忆苦思甜,大概是每个人都要写写家史。比如我,当年父母北上去了延安,我的爷爷,就是父亲的养父,是在广州被日军占领时期,战乱中饿死在中山六路菜根香酒楼门前的。这当然也成了我血泪控诉旧社会的材料。只是当时我不可能知道,大半年之后,我会成为全校最为臭名远扬的黑七类。说起忆苦思甜,其实也有很多不伦不类的笑话。记得听过一个农民的控诉回忆,本来是应该讲旧社会所受的苦难,讲着讲着却成了他自己跟随国民党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军旅生涯,听得我们不知所以然。还有一次下乡农忙劳动,挖掘出来一个贫苦的下中农,勉强可以在大会上讲讲话。这个口吃的家伙讲了半天,最后突然口沫横飞,兴奋地讲到某某某万金油大王,早年是他同乡的远房亲戚。
为了让大家知道旧社会的苦,学校还组织大家吃“忆苦餐”去体验。所谓的忆苦餐,基本上是野菜不放油煮米糠,可能为了更逼真还放入少量木糠。那粗糙苦涩,难以入口,咽得下去的真是英雄好汉。可怜一群少男少女,平日农食足,不知饥饿为何物,怎受得了这般折磨,当时就呕吐的不在少数。我当时为做表率,强忍着,能把半呕出来的酸水和这些泥巴一样的东西,又强行咽了下去。说来也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天堂里了,但是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我们还要去解放全人类,这一点点的苦实在算不了什么。浮夸作假,极左的思潮在不断洗脑,我们这些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革命的思潮一天一天在发展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