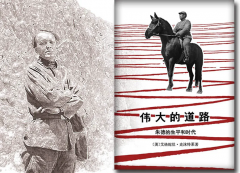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上)
来源:选自《联大八年》 作者: 晓舟 时间:2018-02-24 点击:

《联大八年》,是一本由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自己编写印刷的小书。印行于1946年的8、9月份,用的是土草纸,印刷和装订都很差,可以看出当时的条件非常之困难。封面是闻一多先生题的金文书名。为了这位纪念不久前为了民主运动而遭到特务暗杀的老师,学生们“谨以此书誌念闻师一多”,以表达对老师的哀悼。当时学校已经解散北归,同学们也在分批离开昆明。留下的学生不负众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将此书编成出版。在书的后记中编者说道:从五四开始编,中间经过了两次暗杀事件,到暑假同学们大批都已离开昆明,剩下的同学努力在完成这本书的出版。他们天天跑印刷厂,因为没钱,他们甚至想分册出版,拿第一本卖得的钱,作第二本的印刷费,然后再印第三本,但也未能如愿,最后只能压缩再压缩。而“印刷的丑陋和纸张的恶劣,使编者觉得深深地对不起读者和写稿的朋友”。

书中的文章大都出自学生之手,曾刊登在“联大生活特刊”的壁报上。书中还收入了冯友兰先生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费孝通先生的“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闻一多先生的“八年来的回顾与感想”,由此可看到当时的这些大教授们在授课之余,是如何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并关心和支持他们的。人们喜欢说“联大造运动”,运动虽然不都是联大造的,但确实联大往往走在运动的前面。书中记录了联大八年来的学习生活、团体活动、文艺活动、壁报活动等。应该说最精彩的部分当推“联大教授”。书中收入102位教授,据本书的统计,当时西南联大共有教授179名,其中97人是留学美国的,38人是留欧的,18人留英,3人留日,23人未曾留学。5个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中有21位是留美的。
联大的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他们个性鲜明,风采各异。本书对教授的介绍,一改某教授,毕业于某校,留学于某校,获某某学位,有何成就的程式。由学生写他们熟识的老师读来颇为风趣,寥寥数语,人物跃然于纸上。
梅贻琦先生
实际主持联大八年校务的是我们的梅先生。从前梅先生还常常说说说笑话,但在抗战后期,学校的困难一天加深一天,梅先生也就一天衰老消瘦一天。然而梅先生对同学还常常能自解。最近学校复校经费,叫教部指令,妥善支配,梅先生说:“假如我们用不够就好象我们支配没有妥善似的。”梅先生从不大和同学们接近,主要的大概是事务太忙。梅先生本身就代表清华的严格精神。他兼教务长时,一位四年级的同学选修十二个学分,却有六个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学,这位同学去找梅先生,梅先生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一除。”梅先生原是学电机的。
选自《联大八年》

傅斯年先生
近代学生运动史上及现代政治舞台上有名的人物。傅先生原来研究数学后来改学历史。我们的常委之一。身材的肥胖,在到学校里的人物中,除了孔祥熙就要算傅先生了。三十四年十一月联大末次校庆傅先生来昆,开宗明义,他说他是来管北大复校和联大搬家的,并婉言告诫同学要多花时间在学术上,不要太谈政治。“一二一”伊始,傅先生赶来昆明,首先对关鳞征说“从前我们都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你杀死我的学生比杀死我的儿女还痛心。”然而事隔数日景况全非,经过与党团方面同学多方接触之后,他似乎断定“一二,一”是有党派作背景,于是一方面对教授下功夫,一方面对同学施压力。当时他向教授们宣称以“头”来保证李宗黄撤职,于是教授敢以去留“保证”李宗黄行政处分,以后才有所谓接受保证复课。然而现在呢,李宗黄擢升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傅先生却毫无动静,似乎业己满意。又当今年学校有再留昆明的意思,同学纷纷要求学校迁移,其他学校校长也都在为搬家忙碌奔波,而我们专门搬家的傅常委却在重庆一声不响。偶尔发表一点“须假道中共区”的毫不着边际的谈话。傅先生曾是延安参观团团员,在昆明时,他曾表示延安有“开国气派”。
刘仙洲先生
中国机械学的老学者。著述甚丰。刘先生没有镀过金,然而讲课也很好,他在讲堂上从不用英文。他教热工、机动、热机诸课。私生活极有规律。忠厚温和同刘先生的年事很适合。正当有人想“出仕”或是希望出长某院某系的时候,刘先生却是请都请不动。
王竹溪先生,
清华教授,湖北公安人,抗战后自英国的剑桥归来,在联大从他回国后热力学似乎一直是由他讲授,当年王先生在清华就读时,听说是熊庆来先生的高足。他在国外的研究也偏重于理论方面,所以他的讲解数学用得较多,理论也比较高深。据我粗粗的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宽广的一位,比如三十三年(1944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很细心地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于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听说这本字典行将完工,快要付梓了。王先生平日很注意同学的言论,常见他站在壁报架旁细读。
潘光旦先生
这位名教授想来大家都不太陌生。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西洋社会思想史、优生学的学者,潘先生最崇拜儒家的“中庸之道”,遇事都没有“偏见”,无可无不可。潘先生是社会学家,同时是优生学家,常在优生学班上谈起自己站在国民的立场上也算尽了一己之责,因为潘先生此刻已膝下五女。在欢送同学会上常劝大家努力解决婚姻问题。潘先生是极端主张自由教育的,他在教务长任时,对于同学转系特别宽大优容,有时同学们读了半年,发觉与兴趣不合,下半年就把本系功课退掉,另选他系的课,系主任常不批准,最后总是潘先生签字。潘先生自己承认有演讲瘾,的确,潘先生的口才是少有的,演讲起来如黄河长江滔滔不绝,而所讲的又是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近年来潘先生对于抗战时期的教育颇有感触,最近将有文集问世。
吴大猷先生
假如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么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昊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
吴宓先生
吴先生是有名的西洋文学史学者。有一次吴先生开过“欧洲文学史”一课,事实上除了欧洲的小国外,亚洲的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文学史也附带讲到了。这门课程每周讲三点钟,一年完毕。吴先生平常讲课,常常一面敲黑板或桌子,一面有节奏的念讲词。每逢考试,吴先生总是半小时前就到讲堂,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同学进去时,他很谦和地递一份考卷给你,并且有点抱歉样的向你笑一笑,好象今天不得己要委屈你一下,到下课钟响时,吴先生不像别的先生催你交卷。相反的,他很紧张地向同学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吴先生的高足是李赋宁先生,吴先生离校时,英国文学史就由李先生教,他们师徒在一道谈话,常常是用法文,最近李先生即将到美国继续深造。吴先生常常向同学称赞他是“标准的学者”。
查良钊先生
我们有名的查菩萨(潘光旦先生也如此)。查先生主持联大的训导真是煞费苦心,查先生最了解同学的苦衷,公费第一次请不准,向他诉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也最热心快肠,有人说查先生讲演时不是兴奋、激动、悲哀得流泪,就是高兴得大笑,考诸查先生的平日言行,也确是如此。有一次东会堂住的新同学经查先生批准搬了一个地方,后来查先生查寝室时责备这位同学擅自移动,那位同学即回答是查先生批准了的,查先生立刻说:“我惭愧!我惭愧!’’联大教授对东北问题发出了一次宣言,有些同学以为教授们未得到正确消息之前,不应有所行动,在联大校门口贴了一张“呜呼!大学教授”的纸条,这样一来很多教授跑去找查先生请他制裁,对出布告的学生加以严重处罚,查先生只有笑对教授:“现在是讲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要说,让他说好了。”查先生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忙,从前吃公米的时候,他会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时跑遍昆明各公私机关,为同学借米。这一次,同学纷纷乘车至长沙或梧州,查先生无一天不在场照顾,有时出了麻烦。也总是查先生出面交涉。他是师范学院的教授,联大成立以前在南开,教授教育原理、青年心理卫生等课。
郑天挺先生
历史系教授,教书像说故事一样。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校内)。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北大复校时期他在北平办理复校工作,以前一直是联大的总务长。
华罗庚先生
知名的自学数学家,一腿失健,走起路来右腿总在画圆弧。研究代数,尤长于数论。先生对时事很关心,在卅四年五四前夕的科学晚会上他曾呼:“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有一次临大考,同学们都很紧张,华先生走上讲堂说了一句,不考了,今天却要上一堂课,结果皆大欢喜。华先生现在还很用功,不过也有人说华先生的论文材料太粗疏。
今年三月华先生应苏联文化界之请去苏访问,历时二月余,今已返昆。
费孝通先生
费先生比伍先生(伍启元)还年轻,或者正因为如此跟同学们很合得来,打球开会常跟同学们在一道。社会系教授,功利派学者。自从卅四年(1945年)自美讲学回来,费先生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在卅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关鳞征有“开枪自由”的时候,他曾高声疾呼“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呼吁和平。”费先生对于专讲A、B、C、D的教授们颇不感兴趣。他曾表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他也知道这种人在中国还有多深厚的势力。费先生写的论文有散文小说的笔调,看起来毫不使人厌倦,不过有时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的作风,不免显得冗长罗嗦。费先生有一位贤惠的师母,对费先生异常体贴,膝下儿女成群,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满大概也给费先生一个好的工作心情。
叶企孙先生
在吴有训(正之)先生长清华理学院之前,叶先生就是理学院长。五十余的高龄,早岁在芝加哥念物理,至今独身未娶,讲话时不太顺畅,心肠却极好。联大的学程一次考试不及格就得重修,不能补考,只有叶先生的课例外。他好清洁,在饭馆或是小店吃东西时,椅子至少要擦上五六分钟才坐下去。上课的时候,你每次总会看见叶先生带着一个个的小包很整齐地放在讲桌角上。叶先生有一位侄公子在联大念书,两人感情很好,常见他们一道看看电影,吃点华山西路的大虾粥。叶先生平时谈谈《东方杂志》之类。物理系的课程,从普通物理到近代物理他都教过。
汤用彤先生 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海内佛学大师,研究魏晋玄学。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一九四二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在有一次的哲学系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骂以学问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在学校附近,你常常可以看见汤先生和两位十岁左右读附小的小弟弟捉迷藏。
张奚若先生
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三十三年(1944年)冬,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政协会各方提出无党无派的名单时,中共及民盟都举荐张先生,国民党却说张先生是国民党员,他听到这话时,曾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查明告诉他党证号数,他说他还没有那种“光荣”做国民党员。在政协开会之前夕,他又再度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方案。在三十四年夏季,联大从军同学从印度回来时,在欢迎会上,他们说在印度时所受到的虐待和“新军”的腐败,张先生曾说:“这批人能做出好事来,才是怪事。”最近张先生批评这一批国民党腐败的官僚和特务曾有一句笑话:“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做事;以自己的腐败衬托出别人的前进。”他觉得前一次闹东北问题颇有义和团的作风。先生和钱瑞升先生一样,最近身体都坏,两位师母也一样坚持不许两位先生作公开讲演。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远在“一二,九”时候,他曾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为题而使《独立评论》封闭。
吴晗先生
历史系教授。开中国通史,宋元明经济史两课,对明史有深刻之研究。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靠工读维持生活的,不象其他教授摆架子。为人诚恳热情,尤其愿意与同学接触恳谈。
近年来鉴于国内反动势力猖撅,屡次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积极献身民主运动,对反动派攻击不遗余力。吴先生说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意帝王、皇室、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吴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镜子》内容是描写明末农民暴动事迹的。
曾昭抡先生
北大化学系主任,教有机化学等课。曾先生很用功,深夜还常常在研读比蝇头还小的字的化学书籍,他擅长分析时事,所写的时评,比之我国某些专家毫无愧色,近年来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的跟同学一道吃,玩,闹。他主张注意理论化学,今后北大化学系可能必修高等微积分和力学。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絪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高崇熙先生 清华化学系主任,清华化学系的长成与发展和他的努力是不可分的。教定量及工业分析,讲书的时候,声音大得整个院子都可以听到。高先生认为原子弹是世界上最高权威,很惋惜中国自己不能制造。什么人都不能使高先生满意,经常要讽刺别人几句。同学们刚开始选他的课时,没有人不怕他,在实验室里稍微犯了些错误,如果被他发现了,就会得到一连串的责难,比你所预料的还要厉害,但是同学慢慢的会了解到高先生的心肠很好。
钱端升先生 这位老北大政治系主任,想来是很多人熟知的了。关于钱先生渊博的学识,用不着我们多加介绍。他特有的刚直和正义感,倒值得我们年青人学习。自从“一二·一”复课以后,钱先生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的会议。有一次,联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迳赴重庆就任三民主义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钱先生曾经对同学说:“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钱先生对同学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联大政治系一九四八级(疑为“一九三八级”——编注)第一次“各国政府”的讲堂上,钱先生告诉同学们说英文程度太差,要好好努力。几年来的剥削,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来,据检查,钱先生的血球已经比正常状态差了一百万,就是平常走到教室时,都要休息几分钟才能开始讲课。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袁复礼先生 “在国内,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袁先生加上谭锡畴先生,整个中国就差不多了。字希渊,“希”是谦虚的意思,袁先生的“渊”在联大理学院,只有曾昭抡先生可以与他相比。但是袁先生对于政治向来不愿意在不大熟识的人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正因为太博的缘故,听他的课相当费力,真觉得他是“天马行空”有“犹龙”之感——见首不见尾,“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人说:袁先生最好教研究院。学生到系办公室里,一杯清茶,有时也许是咖啡,香烟满室,谈起来仿佛不能有个完。也许是太博的关系,袁先生很少动笔,在新疆和蒙古转了几年,集了几十箱标本,运来运去,遗失泰半。前两年听说又在什么地方搜回了一些,恐怕要回北平再慢慢整理了。
雷宗海先生
雷海宗先生 联大历史系主任,是成一家言的名史学家。教书有条不紊,同学认为雷先生写黑板都是有计划的。雷先生的脑筋是超级冷静的,只有在这次东北问题中是仅有例外,讲得来老泪横流。雷先生常为《中央日报》写点星期论文,以弥补日常费用。